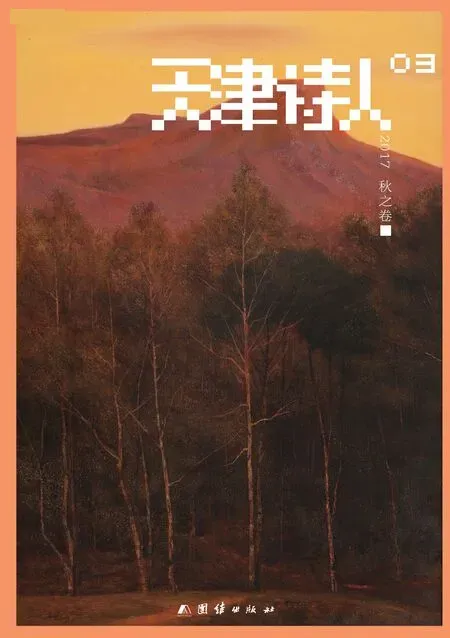钟(外一章)
2017-11-14 17:26胡有琪
天津诗人 2017年3期
胡有琪
那屋空了,空空荡荡,再无人迹。
那屋便成了风快活的风月场所。
人走屋空,泛黄的四壁不再生动。
挂在墙上的钟起先还挣扎了一下,过后也
闭上了嘴,不再多言。
蜘蛛却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地盘,开始织
网,开始在上面吃喝拉撒,开始生儿育
女。
没有钟表演讲的日子,时间便停止了下
来,蒙头大睡。
不知何时,有一首诗回忆起老屋,回来寻
根问底。
当它看到那块钟表时,往事便开始穿越时
空,又穿上旧时的外衣,记忆便嘀嗒嘀嗒
响了起来。
那块钟表复活。
它又拈着莲花指,逐字逐句讲解一部佛
经。
那些呆坐在往事里的笑声,瞬间解冻,开
出朵朵有鼻子有眼的莲花。
青山依旧。钟还是钟。
母亲就是我的三月
这个冬天很冷。
水证明过。风证明过。你也证明过。
水一说话就冻成了冰,真的是祸从口出。
风一说话就变成了刀,走到那里都是刀意
纵横。
你一出门就立马感冒,一连串的喷嚏到处
告状,喊冤。
我把一首诗放出来,它倏地一晃,就钻进
了母亲的眼里,死活都喊不出来。
怪,它一身的冰,却在母亲的眼里,一点一
点地消失,开始变得温暖起来。
诗,开始变得有模有样,甚至在母亲的眼
里有点得意忘形,说的话也不再结巴。
当母亲慢言细语把它读出来时,它的脸
上竟开出了一朵桃花、二朵桃花、三朵桃
花……
我笑了。
在母亲的眼里,我的诗也是她的孩子。再
冷,她也会把它读出一脸的春天。
我的诗不论长短,都是母亲的三月。就连
一个逗号,都变成了春天的蝌蚪,在快活
的摇摆。
猜你喜欢
中学课程辅导·高考版(2020年9期)2020-10-20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4期)2019-05-11
小溪流(画刊)(2018年9期)2018-03-18
中华家教(2017年12期)2017-12-15
小朋友·快乐手工(2015年10期)2015-11-02
小朋友·快乐手工(2015年10期)2015-11-02
少儿科学周刊·少年版(2015年1期)2015-07-07
中学数学杂志(高中版)(2015年3期)2015-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