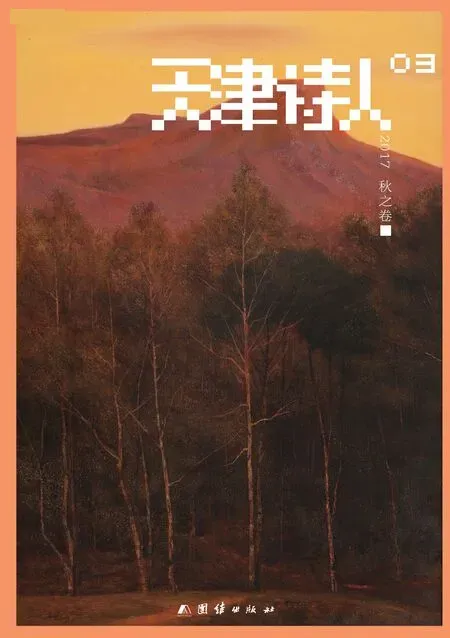忧患意识:关乎民族未来的思考
——读诗人肖黛《杂记黄河》中的《水流》《母亲河》《汜与沱》
道非
诗人,是有不安的灵魂需要安顿的。诗人的幸福和痛苦,缘于灵性的情感和思想,并把对历史或现实的审视,提升到具有忧患意识的理性高度。这种思维定势困扰,成了我阅读的方式,或许也是理解的障碍。
《杂记黄河》这组的《水流》《母亲河》和《汜与沱》,我体验到了作者内心的缠夹和自戕,心灵也跟着震颤了。黄河,不仅是民族的文化符号,更是易引发集体共鸣的精神源泉。面对母亲河,诗人写作前的责任和使命感,也许是朦胧的、隐性的,但构造成文的那刻,必是明朗的、显性的了。诗歌创作,是厘清思想使之成为体系的过程。这种明确的担当和反思意识,构成了诗歌的灵魂,使其变得更具力量。
黄河,奔腾不息百万年的河流。因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养育了我们的先祖“蓝田人”、“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也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祥地。它镌刻着沧桑和变幻的流动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的根基。
选择这一意象为切入点,不管是刻意而为,还是无意取之,其象征和涵盖意义,都已超越了文本本身。这条河流,毕竟是民族灵魂的居所。当诗人的生命之旅或思维游走,抵达黄河流域这一神性界面时,同频共振是必然要发生的。
“独尊世界。奔腾的不止/形如无形的蜿蜒/穿越大象之象/停在小船边你寒暄于相逢”。这样的诗句,我感觉写作是自觉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是交融的,词语的分寸拿捏适度,用文字消解了心灵喧嚣,达成了内外的平衡。
首句独立成句。用词突兀而险绝,稳妥地定义了母亲河的历史地位,凝练有高度。“独”与“尊”,把黄河特色和气概,恰当地凸显出来了。令人惊叹的是,这“独尊”,是世界无二的。仅四字,无限风光。
高处不胜寒,是有道理的。辉煌的高度,本身就是历经苦难波折,用生命血肉做基石的。作者对俯瞰众河流的黄河,并没有居高临下地继续形而上的赞美,而是宕回一笔,险中求稳,由“奔腾的不止”的动态写到“形如无形的蜿蜒”的形态特征,归结到写实中来。再到“穿越大象之象/停在小船边你寒暄于相逢”,已把大河穿越大河本身的视角,推到你的眼前。至于这个你,是作者、读者或河流本身,已不重要。纵或是物我之间的相互探访,也因了“小船”和“寒暄于相逢”,而变得朴素、亲切、温暖。在诗的带入作用下,读者与作者的心贴近了。
诗人,有时是矛盾的聚合体。诗人的自觉和成熟,会保留天真和理想的成分。这致命的率直,在洞察了客观存在的真实及因果后,导致内心产生纠葛,并影响其对事物的维度判断。
诗人的警觉,在于不会自恋地陷入赞美。给母亲河定位后,接下来是更深刻的苦难回顾:沿河而来的天灾人祸,生死记忆,哪怕今天再回首,疼痛仍是刻骨铭心的。这是藏在身体里的伤病,说出来,是敲响民族的警钟。诗人的情感与沉重的历史,已达成了相互认领,进入人河合一的境界了。于是,黄河有了诗人的灵与肉,诗人有了黄河的悲与怆,二者的共性特征是哀而不伤,骨子里保存着沧桑、厚重、不屈、坚定。至此,黄河已非一河,它经历了蜕变和转身,成为民族形象的化身了,并且诗意地“获得了俱足的延伸”。
读《水流》,我眼里也盈了水。面对奔突而来、啸叫而去的世界,当下是进行时的历史。当诗人站在这个节点,用灵魂追随母亲河,士子的情怀是血脉贲张的。随之而来的纠缠与疼痛是必然的,毕竟,我们曾是多灾多难而从不屈服的民族。在想象的耽溺里,诗人是强大的,但代替不了个体的卑微,低处不是姿态,是心态。面对与民族有关的凝重而庄严的情感,也许只有通过文字,把小我“观古今于须臾”而积淀的认识思考,用朴素实在的诗语形式,才能固化为有力度的表达。
在《母亲河》中,不仅因为河流的过去,再次看到了内在的郁结、角逐和觉醒,也看到了赤子之心,对未来的忧虑。这种浸润到骨髓的爱,使诗人怀着深重的不安和焦灼,是历史遗留下的戒备和警觉。“一条大河有无数个岸”,而在岸上聆听的人,“已把你昨天的流淌徐徐拢往身后”,这才是诗人最心疼的地方!母亲生养了我们,就欠着母亲一条命;母亲河哺育了一个民族,民族就要为她牵肠挂肚!我们的命运和这条河何其相似?“拥有无数生养的经历”,不能忘却的记忆,怎能漫不经心“徐徐”抛在脑后呢?忧患意识,是民族长治久安必备的基本素养和品质。诗人面对行旅匆匆的看客,艰难而痛心地发问,而这振聋发聩的质询,会使忘记耻辱而良心未泯者,在盲目自娱中羞愧难当!
在《汜与沱》中,“一时回来/行装们和我相依而发呆/便是创造哀伤音符时的苦思冥想?/看不到一滴水的颜色/听不见一把火的声音/如同被塞进深穴中/呵,这种可能性令我不得不死去活来”。行装们,指代的既是普通的看客,也包括有过家国情怀却麻木了的旅人。他们的来去,会不会因曾经的遇见,而驻足而思想而喟叹,并在短暂的深陷里,与母亲河的历史相遇和碰撞?这首诗的字里行间,似乎弥漫着到来或离散后的被抛弃感,这种丢失或落魄的邂逅,是母亲河悲怆命运,给民族留下的恐惧症。历史是不能更改的,危机感是与生俱来的,在惊悸和考量时,因“看不到一滴水的颜色/听不见一把火的声音”而处于“萍踪无定”感中的人,再次陷入黑暗、潮湿、逼仄的孤独无助中。来时的苦思冥想,去时的泪流满面,这些平实无饰的诗句,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患得患失,是内忧外患的重伤,浸入身体的冰冷,戳入灵魂的创痛。面对数千年未改模样的“汜与沱”,诗人有保存痛苦的权利,有诘问的必要。即使过客,也该扪心自问的!民族伤不起啊,要永久保留这种寒彻和痛楚感。
因为有了自觉,民族才能卧薪尝胆,不辱使命,迅速崛起。这种省悟,带着强烈的安危和归属迫切,不是一个人的,是整个民族的。即使国家强盛之时,血液里仍要流动着忧患意识。什么都可以丢,忧患意识不能丢,它是个人和民族都要有的精神品质。正是这种情结做先决条件,才有了后记的“不过以得心境的安逸而是”,诗人的安逸,是警觉的安逸,是枕戈待旦的安逸。
有人说:命运取决于我们对待命运的方式。但诗歌不一定取决于我们对待诗歌的态度。诗歌,除了作者的主观意识,还有读者和评论者参与的过程。诗歌的价值和影响,需要时间来衡量。然而,诗人的真挚情感,是奔走于字里行间的,不需要滞后的验证来定性。
人是随着时间和阅历而成长的。诗是诗人拓展和完善人生格局的自觉行为。诗人通过诗歌完成与外界或心灵的对白,把自身的经历、发现、感悟和创造,逐渐理出明确的思想轨迹,使潜在的、零散的、模糊的智慧碎片,形成独立的审美体系,这是对自我的文化构建。我从《杂记黄河》隐约看到了这个迹象。
这组诗,就我读懂的部分而言,是没有戾气的。诗,可以自我,或有点儿霸气,或许是特色或风格,但不能有戾气。戾气,对诗歌的发展和未来,无疑是蚀骨喋血式的伤害和扼杀。说没有戾气,是指相信读者的才华,留下必要的空白,多了想象发挥的余地。这种有意无意的缝隙,像钧瓷胎纹色泽一样,在造型和构图方面,做得灵动而鲜活,具有欣赏的可塑性。作品这样打磨,是创造艺术的高超处。在阅读鉴赏时,尽可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完成诗意的二度创作,不会囿于囚笼而窒息。
诗人的喜剧:是人生遇见了诗。诗人的悲剧也是。诗让诗人学会了坚强,并带着淡淡的忧伤。在《杂记黄河》这组大题材的文本里,诗人的刚毅中透散出沧桑的悲壮,是隐约可见的。我想起读萧红《呼兰河传》时,脑海蹦出的一句话:女性的坚定弥漫着时代和地域性的苍凉,她在对命运的反抗中走过命运本身。历史是现实必须正视的宿命,母亲河有太多坎坷和不幸,回眸和接纳这一切的同时,诗人用女性柔韧的勇敢,沉郁的呐喊,直抵这种宿命本身。教训必须吸取,经验需要总结,国盛民强不能忘掉这些记忆。诗人的良知在于怀着建设性的善意警醒。
诗人的发现力,是身上的理想因素决定的。在触碰过去和遥想未来时,看到了人性或意识方面存在或预见的缺陷和不足。毋庸置疑,诗人的写作目的是在唤醒,告诉我们不要再相信或经历这种宿命。所谓的宿命,并非一成不变的。是的,有些事物必须改变!
整组诗朴实的带着暗色的语感,让我读懂了蕴藉其中的不屈和坚决。灰暗不是沉沦,是为了唤醒和鞭策。诗人的坚强和热爱,在内敛和节制中蕴藏着。这是诗人的孤独,可养育丰厚的思想。她用刚正的文字,把看到想到的呈现到面前,我们才能面对、接纳、反思和改变。好像是昌耀先生诗句:“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从深远的角度和意义解读,悲歌是更有使命感的颂歌,是不可或缺的另一种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