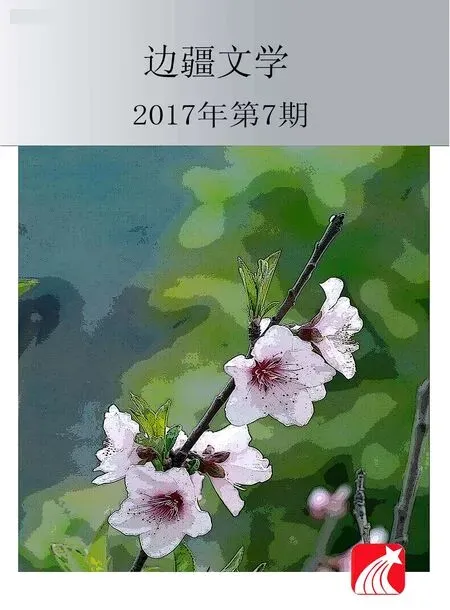贤者得闲(外一篇)
王雪飞
贤者得闲(外一篇)
王雪飞
一个多月前,怀瑾堂堂主李建江与我联系,嘱咐为杨连先生的新作《赋闲集》写点阅读心得。
诗词一道,所学甚少,素无研究,自然不敢应承。不几日,怀瑾堂小胡却已将连老诗稿邮件发来。五月正值我值守一份报纸夜班,长夜枯坐,痛读那些冠冕堂皇的大人之语,疲惫之时,点开《赋闲集》诗稿,陆续读来,颇有亲切之感,竟有一些话想说。
杨连先生是我尊重的长者。我在保山曾经驻留十四年,大抵由于记者这个身份的缘故,三教九流的朋友甚多,结识的官员也不在少数,与杨连先生虽无密切过往,却莫名形成一种独特印象。
形容一个人的气质,中国词汇非常丰富细致,比如朴实、清朗、孤傲、圆滑、猥琐、尖刻之类,等等不一。在交往过的官员中,杨连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刚正。刚强正直,刚毅正派,符合我对一位官员力所能及的想象。而这印象,来自我和杨连先生的直接交往,来自相熟朋友的口碑议论,也来自我从杨连先生诗文中得到的真切感受。
从《幽谷诗钞》到《赋闲集》,这个印象一直在延续,在加深,也在改变。连老的诗文,或讨论时事,或感怀故人,或表达心情,都从生活一事一人一时中来,因其刚正故显坦荡,以其坦荡而现率真。退居林下,其气不衰,其性弥坚,然而平添一分从容淡然,这正是《赋闲集》带来的变化。
我一直以为,对待时间的方式很能体现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尤其是真正的所谓"得闲"之后。闲适而非闲散,散淡并非散漫,闲极无聊的大有人在,品得闲之真味的却少之又少。“往事回首终无愧,退休从容度晚年”、“到老回眸终一笑,其实天地不亏我”、“活要活得有骨气,老要老得见精神”、“闲来慎独少受辱,心安理得乐坦然”、“闲来无为养天年,便是人生好境界”连老诗文中反复吟咏的“闲”字,已然真切传递着一种知闲、得闲的自在心境和从容心态。
有丰富的心灵才有悠闲的生活。如果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是一种经历,那么“老来识得闲滋味,不赋新词只说闲”何尝不是一种越发值得尊重的生命态度和生活方式?
我同样坚持认为:贤者心闲,贤者知闲,贤者得闲。闲之真味,唯贤者识之,唯有德者居之。《莫看人生多追求,幸福其实很简单》,连老这一句,直白、实在、真诚。
怀瑾堂主是相交二十年的老友,《赋闲集》由他制作必为精品。到时免不了要索取数册,或置案头,阅而有得;或赠识者,手亦留香。
几句感言 一份敬意
我太太供职于云南老年报,由于做办公室工作的缘故,和一些经常到报社送稿子的老人们有直接的交往。
老人们脾气个性不同、为人处事各有风格,朱兆亮先生则是让我太太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
朱先生是云南老年报20多年的老朋友,读书、写稿是他离休后安养晚年生活的一部分。他的文章体裁广泛,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二三百字一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文字平实,充满生命的睿智。
太太与朱先生相识四年,却俨然多年的老朋友一般。写好稿子,只要精神状态好,朱先生都要亲自送到老年报办公室。每次来到,会先浏览一遍新出的报纸,喝两盏茶,与放下手头工作的太太谈谈稿子,聊聊家常。每每提及他两个聪慧乖巧的孙女和调皮可爱的重孙小龙儿,这位快90岁的老人脸上便满是幸福与慈爱。朱先生听力不大好,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交流,太太会将要说的话写在纸上,朱先生看过后或会心一笑或侃侃而谈,久而久之,这种"纸上谈兵"反而添了种意趣。
前年朱先生因肺部肿瘤住院治疗,听说后和太太到云大医院探望,路上想好的宽慰之语,见了朱先生方觉都是多余的。倒是朱先生爽朗的笑声,谈病毫不色变的那份豁达与清醒,给予我们很多启示和教益。
朱先生今年89高寿,见报文章近500篇,获奖无数,这已是他的第五本作品集。读着这些印刻他一生所见所闻、真情实感、充满哲理的文字,深感幸运。
随着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在,传统的书写、出版、阅读方式正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我始终对那些坚持书写、坚持阅读,热爱写作、热爱生活的老人们怀有极深敬意。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与人为善的待人理念、真诚朴实的行事方式,一定能够得到人们认可,同样值得人们追求。在我看来,喜爱阅读和写作的老人们已然成就了这样几件事:让自己的生命不断充实;为亲人留下颇有意义的纪念;给这个世界标注出精神的方向和高度。
朱兆亮先生的为人为文,正是如此。
所以,当朱先生嘱咐为他即将结集出版的新书写几句话,我欣然从命。虽然不才,但以此聊表敬意,向朱先生这样的写作者表达一个后学晚辈的由衷尊敬。
(作者系云南日报评论部主任)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