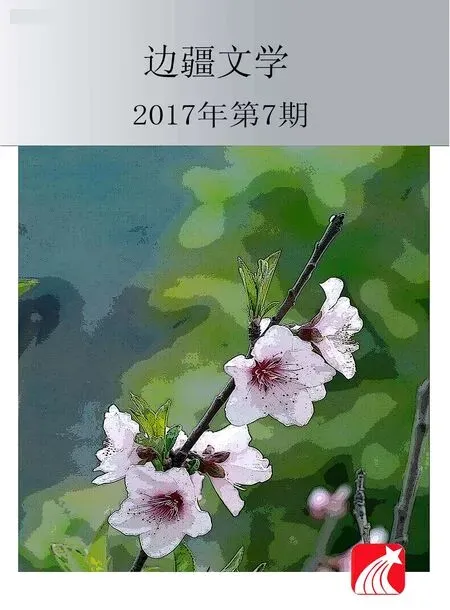诗歌的粉红色调(外一篇)
任芙康
争鸣广场
诗歌的粉红色调(外一篇)
任芙康
·主持人语·
本期发几篇短文。文短而意长,追求文字的凝练,文风的隽永,应该是批评写作题中之义。简单说批评文字的长短孰优孰劣,没有意义。还是看发在这里的几篇文章。比如:某作者说:“不会写情诗的人,终究是会和诗分手的。情是诗的源泉,诗情寡淡,温吞躲闪,写出的句子,必然如同缺水的干枝。”这就是经验之谈。都知道“修辞立其诚”,但是,如何立?这是答案之一。(冉隆中)
我昨天从天津来,明天回天津去,跟寒冷的北方,虽只有三两日分手,但来到青绿的深圳,置身于比天气更宜人的诗歌聚谈,令人喜悦。毕竟,短暂的暖和,也是幸福。写诗,被一些人认为是私人化、个体化的创作。似乎只有关在门窗紧闭的书斋里,才能写出让五百年之后的子孙顶礼膜拜的史诗。其实,可能大谬。诗歌诗歌,表明诗离不开歌;歌舞歌舞,表明歌离不开舞。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鲍勃·迪伦,一位民谣歌手,行吟诗人,却创造出崭新的文学表达。而下午的诗歌朗诵,听说除了配音,还有伴舞,将会同样告诉我们,诗歌写作,只有摒弃盲目高雅的幻觉,承受地气润泽,经受生活滋养,领受时代恩惠,接受民众鉴赏,方有望真实的兴旺。
1964年,我14岁,捧着梁上泉的《山泉集》,仿效涂鸦。第二年春天,发表第一首诗歌。稿费两元,买了100根棒棒糖,全班48位学生,加上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人手一根。尝过棒棒糖的甜头,同学中多了好几位诗友。到了二十来岁,有一天,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相貌呆板,跟诗人的模样,完全不配。从此,再不写诗。但依循曾经爱诗的惯性,就只是读。再后来,又参加一些诗歌的评奖,就还是读。读来读去,觉出自己的心里,比较接受声响小的诗,比较接受色彩淡的诗,比较接受含义浅的诗,或者说,比较接受家长里短的诗。譬如,你们深圳,有位黄姓朋友的诗作,便是我喜欢的类型之一。在他从容的表达里,不见大呼小叫,剑拔弩张。给你的感觉,只有举重若轻,平易近人,自尊自爱,甚至,欲言又止……此外,他的诗里,不乏对山泉、古树,祖母、草鞋等等人与物的缅怀,字字入眼,拨动心弦。今天的人们,七情六欲,而又丢三落四,尚有几多闲暇,能在脑子里腾块空地儿,保存关于祖母、关于童年、关于草鞋、关于故乡的记忆呢?
不由自主,想起我的中学语文老师。老师课上澎湃,课外少言,在50多年前的蜀国诗坛,不动声色地占有一席之地,写山山无狰狞,写水水无凶险,写人人无邪气。他的诗歌园子里,种着一点点老街古巷的幽暗,种着一点点山川原野的寂寥,种着一点点为人处事的良善,种着一点点花前月下的缠绵。总而言之,老师的诗,离叫卖声远,离开山放炮远,离心计远,离床榻远;既不像大跃进年代的民歌催人豪迈,亦不像流沙河的《草木篇》令人可疑。“文革”中的老师,成惊弓之鸟,受尽凌辱。在一场冬寒的批斗会上,脖领子里被人灌进一盆凉水,面对辱骂和耳光,他无奈地说:“我身上血少,只好做一个粉红色的诗人。”
而眼下,偶尔读到与老师相像的诗作,心里会生出莫名的亲近。当然,半个世纪的时空之隔,即或相像,但相互映照,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很难重合了。但玩味彼此的字里行间,除了近似的气息、近似的韵律,更有近似的色泽,那就是我老师从未舍弃的粉红。这种远离沉闷、也同时远离亢奋的颜色,会让你安静地去读,安静地去想。读是如鱼得水的读,想是怦然心动地想。有粉红作为基调,给人留出安详的余地,不同的看客,会以自我的境遇与感受,做各式的解读。粉红之色,不轻不重,不淡不浓,颇合中庸之道。如果有朝一日,粉红能修成正果,成为诗坛一种“正常”的色彩,肯定有助于写诗的人与读诗的人,淡忘于名利之诱惑,舒缓于现实之尴尬,润饰于人性之塑造。那就喜从天降,诗坛有福了。
容我再用一点时间,介绍一位历经坎坷的陈姓诗人,现居洛杉矶的四川老乡。72岁之前,老乡从未写过一首情诗。73岁的某一天,突生愿望,“要以情入诗,补爱恋之课”,随即坠入重重实有或虚拟的情网,而难以自拔。他的日常聊天里,绝无同龄者的健身、防病、养生之类,始终以独特的青春气息,去包裹每一位同他接触的人。至今七年过去,已写出情诗两千余首,成书四卷,被誉为诗坛一抹倩影。不知道,他的抒情之旅,还将跋涉多久。平均二百多首的年产量,意味着几乎每天,胸中怀爱,笔下流情。陈诗人积八十载人生阅历,以大半生情感蕴藏,蘸着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心性,写出的每首情诗,无不以翩翩风度,款款情思,让无数年轻男女,徐徐燃烧起来,成其心悦诚服的拥趸。
相形之下,许多杂以繁色,浓妆艳抹、怪相迭出的诗作,挖空心思,搜罗惊人之语,渴求惊鸿一瞥,追逐惊世骇俗,则往往事与愿违,耀眼于一时,炸响于一瞬,很快归于沉寂。所以,对那些色调可疑的诗,此刻不说也罢。
很多很多年前,那已是一段遥远的记忆,少年的我,靠着模仿,学着写诗。成年后则完全洗手。难以为继的原因是,情趣迟钝、枯涩。曾有一位师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会写情诗的人,终究是会和诗分手的。情是诗的源泉,诗情寡淡,温吞躲闪,写出的句子,必然如同缺水的干枝。我的经历,验证了师父的指教。活过一大把年纪,不曾给哪位异性,写过一首情诗。尤为悲惨的是,不曾有哪位异性,给我写过一首情诗。但相信在座的各位幸运的朋友,都不会遭遇如我一样的人生失败。诗歌的门外汉,此刻在行家面前语无伦次,并偏好于粉红的色调,一定惹人见笑。那就赶紧闭嘴。
言过其实的“冲突”
“东西方文化冲突”,已成一种概念,并在众人眼里,视作定律一条。中外交往之中,凡遇障碍,皆顺手牵羊,或以"文化"的钥匙释疑,或以"冲突"的利刃解惑。大而化之,固然省事,但远离贴切,多为隔靴搔痒。
托开放之便,自20多年前开始,我拖着行囊,多次域外云游。以丹麦为圆心,网罗周边诸国,曾有由秋到冬的勾留。之后有东南亚的云顶之高,亦有港澳台的湖海之远。数度赴美,与白人朋友结伴,为看太平洋与大西洋在洛基山脉的分水岭,登上美国国家公路海拔最高的地段;为看海明威的故居,抵达美国版图上最南端的小岛。国内的寒舍,我们留宿过法国、瑞士、美国、冰岛的亲戚。与家人同行,带他们去过延庆八达岭、重庆史迪威故居、长江三峡、卧龙熊猫保护区、成都三星堆遗址。我们用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成功矫正一位美国生、美国长的爱尔兰血统姑娘的形象思维,帮助其拨开爱情的迷雾。我们以东方式的待客之道,接纳一位除却往返机票、身无分文的法国女孩,兑现了她儿时向往的长城攀登。我们以华夏传统的忠孝伦理,说服一位冰岛小伙子,逢年过节去探望他定居瑞典的父母。交往之初,我们毫无回报的预期。但意外收获不少良性循环的硕果,使我们深感人生的丰富,亦倍觉人生的温暖。
悠久的大学,庭院深深,往往是一个地域的缩影。我酷爱校园里的行走,仅在美国,游览过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伯顿大学、布朗大学、纽约大学、纽约州立石溪大学、维斯理学院、克罗拉多大学、西方大学。看人家师生的风貌,图书馆的秩序,教舍的建筑,森林与草地的铺陈,在我"东方"的眼神儿里,毫无突兀之感,令人一见倾心。现在不少人聚饮聚餐,时兴AA制,本来无可厚非。但眼见一些青年,学得若干皮毛,将AA制夸张到西方文化的高度刻意仿效,就几乎成了他们吝啬的托辞。我多次有意做过试验,国内国外与洋人共赴饭局,要么由我一人付账,要么完全袖手旁观,结果无一“老外”跟我翻脸,更无一“老外”拒绝入席,回回酒足饭饱,尽欢而去。罗列这些,只为表达一个意思,我多年来西去东来,尚未眼花缭乱,而在琢磨体会,所谓东方西方的文化差异,其实往往只是生活的习惯、规矩不同而已,无须动辄凸显,更不必轻言"冲突"。抛开心理变态,抛开特异功能,从正面说,东方人西方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往往同心同德;从负面看,东方人西方人人性中的顽皮与卑劣互为难兄难弟。东西方借鉴、弥补、渗透、融合的事与理,可谓俯拾即是。
就我耳闻目睹,随手举例。早春鸟叫带来的愉悦是一样的,晚秋落叶带来的伤感是一样的;海水入嘴的咸与涩是一样的,刀尖进肉的疼与痛是一样的;相处一生的亲人不幸离世抱头痛哭是一样的,十月怀胎的婴儿顺利降生奔走相告是一样的;富豪拒绝死神的奢望是一样的,穷人追逐温饱的诚意是一样的;对投桃报李的认可是一样的,对过河拆桥的厌恶是一样的;富在深山有远亲是一样的,贫居闹市无人问是一样的;过节时注重吃喝是一样的,场面上讲究穿戴是一样的;父母康健的欣慰是一样的,儿女顽劣的痛惜是一样的;夫妻同床异梦的怨愤是一样的,同事尔虞我诈的郁闷是一样的;商人避税的心眼儿是一样的,文人版税的盘算是一样的;平民安居乐业的理想是一样的,政客巧舌如簧的做派是一样的;学者天马行空思路的庞杂是一样的,乞丐东张西望目标的单一是一样的;年轻气盛时容易愤青是一样的,渐入老境后变得宽容是一样的;对古道热肠的认可是一样的,对世态炎凉的感慨是一样的;有荣辱心的人做了错事会无地自容是一样的,无羞耻感的人干了坏事能泰然自若是一样的;不良的少年浪子回头金不换是一样的,有志的孩子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样的;坐上飞机希望正常降落是一样的,进入梦乡期待平安醒来是一样的……
写出这些语无伦次的句子,都是为了与人分享一个概念——文化范畴内"冲突"的概念,只是相对而言,大不必有人一说,你就点头称是。
(作者系资深文学评论刊物主编,多届茅奖、鲁奖评委)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