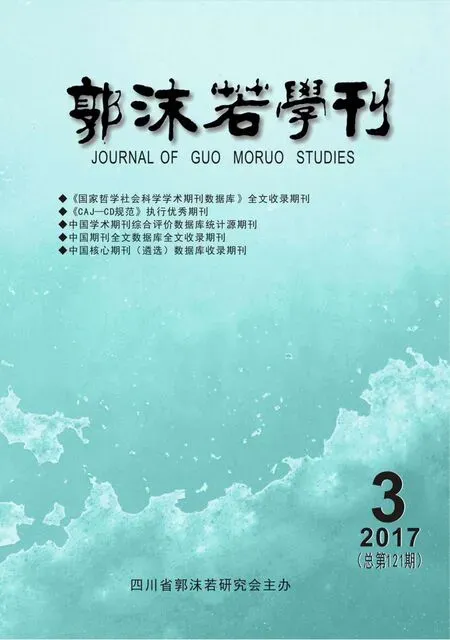跨越时空的对话、拯救与冒犯
——评《卷耳集》兼论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
曾 平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2)
跨越时空的对话、拯救与冒犯——评《卷耳集》兼论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
曾 平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2)
郭沫若1920年代的《诗经》今译之作汇编而成的《卷耳集》是沐浴于五四精神之中的郭沫若与古老的《诗经》之间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是郭沫若以现代精神和崭新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形式对《诗经》的重新诠释与改写。一部篇幅有限的《卷耳集》,却大胆挑战了或隐或显的各种偶象,这其中至少包括:自古以来将《诗经》神圣化的经学家;白话新诗的始作者胡适;由文学革命造就的一批新的文化思想权威等等。郭沫若以其《诗经》今译的文学实践,试图证明:文言与白话、新诗与旧诗之间并无绝对界限,完全可以相互诠释、相互沟通、相互融洽。郭氏的《诗经》今译以诗人自身的创作实践,表达了郭沫若对诗歌翻译问题的基本看法:反对笨伯式、注释式的诗歌直译,主张重在传达原作风神气韵的意译。郭沫若的《诗经》今译,是其诗歌翻译思想最初也是最成功的践行,并最终形成了《诗经》原作的艺术魅力与郭氏独特的艺术个性叠加之后的成果《卷耳集》。《卷耳集》不仅是郭沫若以时代精神对《诗经》作品充满个性的再诠释,也是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对旧诗经典的致意与挑战。
郭沫若;《卷耳集》;《诗经》;诗歌翻译
1923年,郭沫若怀着极大的热情,致力于《诗经》中被朱熹指斥为“淫奔之诗”的部分作品的古诗今译工作。现代新诗刚刚站稳脚跟,就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非凡勇气,撇下千年来的经学传统,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直接对《诗经》这部儒家经典里的诗作进行全新解读和大胆不羁的文学改写,力图以自由奔放、狂飙突进式的五四时代精神,洗去历代经学家们涂抹在《诗经》上的厚厚脂粉,还原《诗经》中“十五国风”尤其是其中的爱情诗的民间歌谣本色。
相比于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论调,郭沫若自登上文坛起,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更加温和亲切的感情,积极尝试对其进行改造,使之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服务。从大的方面看,郭沫若的《诗经》今译未尝不是由胡适等新文化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的组成部分。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一宏大目标作为新一代知识精英阶层的历史使命,“整理国故”运动算是正式拉开帷幕。受此影响,对《诗经》的研究也成为当时学界的热点。郭沫若对整理国故运动颇有微辞,倒并非他认为国故不值得整理,而是认为真正的国故整理,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传统学术的考证研究工作,而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整合进当下的文化之中,使之变成时代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基于这种认识,郭沫若于1920年代初对《诗经》部分作品进行白话今译,并陆续在许多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反响极其热烈。这些以《诗经》中部分“国风”作品改写而成的自由体白话新诗汇编成《卷耳集》,1923年由泰东书局出版。
一
《卷耳集》收录的作品,是沐浴于五四精神之中的郭沫若与古老的《诗经》之间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是郭沫若以现代精神和崭新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形式对《诗经》的重新诠释与改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郭氏的深刻影响,决定了《卷耳集》的整体思想风貌与艺术趣味,在选择所译作品时,郭沫若避开了与庙堂直接相关的雅、颂部分,单单选取了国风部分的爱情诗,这与五四新文化人将《诗经》这部儒家经典平民化、去经学化的努力完全一致。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周作人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倾向于将《诗经》看作是一部民歌总集,以此来消解《诗经》作为儒家经典的神圣色彩,将其从神坛上拉回到民间。郭沫若对所译《诗经》作品的选择,显然与这一“非圣无法”的时代思潮息息相关,注重的是《诗经》之于五四以来倡导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等现代观念的现实意义。经过郭沫若的翻译,脱胎于《诗经》的《卷耳集》变成了一部集缠绵悱恻、大胆热烈与天真烂漫为一炉的现代新诗集。
郭沫若曾经说,一个诗人不仅要做自然和时代的肖子,还应该更进一步,做自然和时代的老子。郭沫若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同样如此,他要做的是驾驭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而不是为它们所驾驭。这样一种富于挑战精神的个性,在郭沫若对《诗经》的白话翻译中也可见一斑。一部篇幅有限的《卷耳集》,却大胆挑战了或隐或显的各种权威与偶象,这其中至少包括:自古以来将《诗经》神圣化的经学家;胡适等人缺乏诗意的白话新诗;五四新文化人不成熟的现代新诗观念;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一批新的文化思想权威等等。《卷耳集》虽然是五四精神孕育出的果实,但同时也暗含着对文学革命发起者们新权威地位的挑战。几年以后,郭沫若撰写《文学革命之回顾》(最初收入1930年上海神州出版社《文艺讲座》第一册,署名麦克昂),其反抗五四文学革命所造就的文化新权威的立场更加鲜明:“时代不断的在创造它的文言,时代也不断的在创造它的白话,而两者也不断的在融洽,文学家便是促进这种文化、促进这种融洽的触媒。所以要认识文学革命的人第一须打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观念。兢兢于固执着文言文的人固是无聊,兢兢于固执着所谓白话文的人也是同样的浅薄。时代把这两种人同抛撇在了潮流的两岸。”《卷耳集》所做的工作,正是促进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不断融洽,致力于打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观念。郭沫若以其《诗经》今译的文学实践,也在试图证明:文言与白话、新诗与旧诗之间并无绝对界限,完全可以相互诠释、相互沟通、相互融洽。
在《卷耳集》的序与跋中,郭沫若阐述了自己翻译《诗经》的动机、原则与野心。如果把古诗今译分成两类:一类是“我注六经”,一类是“六经注我”,郭沫若的《诗经》今译显然更倾向于后者。他毫不讳言在《诗经》今译中秉持的古为今用、人为我用的大胆态度:“我对于各诗的解释,是很大胆的。所有一切古代的传统的解释,除略供参考之外,我是纯依我一人的直观,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它的生命。我不要摆渡的船,我仅凭我的力所能及,在这诗海中游泳;我在此戏逐波澜,我自己感受着无限的愉快。”与强调逐字逐句的直译硬译不同,郭沫若理解中的古诗翻译,应该是译者与被译者跨越时空的一场生命交融与灵魂对话,是穿过层层叠叠的时间迷雾后译者与被译者之间的一次深情凝视。把翻译变成一次充满激情的艺术再创造,也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影响的结果:“我译述的方法,不是纯粹逐字逐句的直译。我译得非常自由,我也不相信译诗定要限于直译。太戈儿把他自己的诗从本加儿语译成英文,在他《园丁集》的短序上说过:‘这些译品不必是字字直译——原文有时有被省略处,有时有被义释处。’他这种译法,我觉得是译诗的正宗。我这几十首译诗,我承认是受了些《园丁集》的暗示。”泰戈尔是在把自己的诗翻译成英文时采取意译的方式。既然是翻译自己的诗,最终解释权本来就在自己,不管直译还是意译,都算不上是对原作的冒犯。郭沫若将此原则移植到古诗今译之中,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首先,郭沫若翻译的是古人的诗作,对此,他当然不能如泰戈尔翻译自己的作品那样拥有天然的最终解释权;其次,郭沫若翻译的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作品,而是被视为神圣的儒家经典和中国诗歌至高无上典范的《诗经》,历代无数杰出的经学家和文人士大夫已经对它做了深入的解读,以这样一种自由的“纯依我一人的直观”态度去翻译《诗经》,背后隐藏着将“我”凌驾于一切解经家甚至凌驾于《诗经》之上的狂傲。而这样一种推倒一切传统思想束缚的态度,正是五四精神的突出表现。
郭沫若深知自己翻译《诗经》的尝试其实正包含着蔑视一切偶像与权威的叛逆精神,对此,他深感自豪:“我这个小小的跃试,在老师硕儒看来,或许会说我是‘离经叛道’;但是,我想,不怕就是孔子再生,他定也要说出‘启予者沫若也’的一句话。”在郭沫若看来,即便先圣孔子再生,也不得不对自己的《诗经》译作赞叹不已。如此自信骄傲的郭沫若,又岂能将新人名士放在眼里!故郭沫若在《卷耳集序》中接着说:“我这个小小的跃试,在新人名士看来,或许会说我是‘在旧纸堆中寻生活’;但是,我想,我果能在旧纸堆中寻得出资料来,使我这刹那的生命得以充实,那我也可以满足了。”一切今人古人都不放在眼里的郭沫若,在选择翻译哪些《诗经》中的作品时,却仍然深受时代风尚的影响,挑选了极受胡适等五四新文化人推崇的《诗经》中“十五国风”里的情诗进行翻译:“我选译的这四十首诗,大概是限于男女间相爱恋的情歌。《国风》中除了这几十首诗外,还尽有好诗;有些不能译,有些译不好的缘故,所以我便多所割爱了。”
不过,郭沫若作为诗人最大的狂傲还不在于秉承了“非圣无法”的五四精神,而是将自己对《诗经》进行重新诠释的白话新诗,视作对《诗经》真实面目和艺术生命的拯救者。《诗经》如同一位绝世佳人,被漫长时间里厚厚的灰尘与历代解经家们腐烂旧解的层层淤泥掩去真容甚至夺去生命,郭沫若自己则是那位拯救美人的盖世英雄,让她不仅死而复生,而且重新光彩照人:“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在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怜!可怜!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我要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我想把这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这也是我译这几十首诗的最终目的,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野心。”郭沫若对待《诗经》的这种态度,可以视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普遍态度。1919年12月《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发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文章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类似,五四精神也激发了个性解放和自我意识的充分觉醒,以致于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过程中,新一代中国知识人常常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眼光作为评判一切的尺度。对郭沫若这样才华横溢又天生好胜的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他完全相信今天的人们可以越过所有解经家的陈腐之说,凭借新鲜活泼的个体生命直觉,直接感受与还原《诗经》等文学作品的生命与真美:“《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这是既明的事实。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迷恋,也值不得我们去批评。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曾经以“天狗”自居的郭沫若,隐隐也将自己对《诗经》富有个性和激情的艺术诠释,视作可以一举驱散千百年来笼罩着《诗经》的烟瘴的“太阳的清光”:“朋友们哟,快从乌烟瘴气的暗室中出来,接受太阳的清光吧!太阳出现了,烟瘴自有消灭的时候。”
二
那么,我们要问,郭沫若的《诗经》翻译,对《诗经》原作而言,是否真的是一抹还原真相、驱散烟瘴的“太阳的清光”呢?对此,郭沫若自己是信心满满的。几年后,在《关于文艺的不朽性》一文(最初收入一九三○年上海天成书店出版的《孤鸿》)中,郭沫若说:“例如一部《国风》要算是中国存世的最古的抒情诗,它传世已继有三千年,但那艺术的价值丝毫没有更变——甚且在‘圣经’的漆灰之下久淹没了的它的本来的面目,到近代人的手中把那漆灰剥落了,又才显示了出来。”让《诗经》中的《国风》重新焕发生机、勇敢剥落了淹没真相的“漆灰”的近代人,自然包括郭沫若本人。
我们来看几首《卷耳集》中郭沫若的《诗经》今译之作。首先来看开卷之作《周南卷耳》(本篇曾发表于1923年9月5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一片碧绿的平原,/原中有卷耳蔓草开着白色的花。/有位青年妇人左边肘上挂着一只浅浅的提篮,/她时时弓下背去摘取卷耳,/又时时昂起头来凝视着远方的山丘。//她的爱人不久才出了远门,/是骑着一匹黑马,携着一个童仆去的。/她在家中思念着他坐立不安,/所以才提着篮儿走出郊外来摘取卷耳。/但是她在卷耳的青白色的叶上,/看见她爱人的英姿;/她在卷耳的银白色的花中,/也看见她爱人在向她微笑。/远方的山丘上也看见她的爱人在立马踌躇,/带着个愁惨的面容,/又好象在向她诉说别离羁旅的痛苦。/所以她终竟没有心肠采取卷耳了,/她终竟把她的提篮系在路旁,/尽在草茵之上思索。//她想,她的爱人/此刻怕走上了那座土山戴石的危岩了,/他骑的马儿怕也疲倦得不能上山了。/他不知道在怎样地思念她,/她没有法子可以安慰他。/假使能够走近他的身旁,/捧着一只金樽向他进酒,/那也可以免得他萦肠挂肚。/但是她不能够。//她想,她的爱人/此刻怕走上了那座高高的山顶了,/他骑的一匹黑马怕也生了病,毛都变黄了。/他不知道是在怎样地愁苦,/她没有法子可以安慰他。/假使能够走近他的身旁,/捧着一只牛角杯儿向他进酒,/那也可以使他忘却前途的劳顿。/但是她不能够。//她想,她的爱人/此刻怕又走上一座石山戴土的小丘上了,/他骑的马儿病了,/他跟随着的仆人也病了。/她又不能走近他的身旁去安慰他,/他后思着家乡,前悲着往路,/不知道在怎样地长吁短叹了。//妇人坐在草茵上尽管这么凝想,/旅途中的一山一谷/便是她心坎中的一波一澜/卷耳草开着白色的花,/她浅浅的篮儿永没有采满的时候。”《诗经》中《卷耳》的原文如下:“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两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试图还原原作气韵神色的努力。虽然是意译,采用的诗歌形式又是迥异于旧体诗的自由体白话新诗,但郭沫若的译作的确传达出了原作一唱三叹的民歌情调,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原作中女子思念远方爱人时的场景与内心的百转千回。多年以后,郭沫若在《简单地谈谈〈诗经〉》一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文艺报》第三卷第七期)中谈及《国风》的特点时说:“《国风》多是一些抒情小调,调子相当简单,喜欢用重复的辞句反复地咏叹,一章之中仅仅更换三两个字的例子是很多的。这正是一般民间歌谣的特征,尤其是带些原始性的民间歌谣。”对《诗经》中“十五国风”的这一认识,也代表了五四以来新文化人对《诗经》的共同判断。郭沫若的译诗,有意突出“国风”回环往复、再三咏叹的民间歌谣特征,试图还原《卷耳》一诗作为民间爱情诗的本色与真相,让其从经学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毛诗序》说:“《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毛诗序》的说法,代表了经学家们以儒家政治理念解读《诗经》的普遍倾向。正如郭沫若在《卷耳集序》中所说,他的《诗经》今译,完全跳出了历代解经家们陈见旧说的束缚,直接去体会《诗经》原作的生命与情感,大胆以译者自身极具个性的艺术直觉作为《诗经》翻译的凭据。这样的古诗今译,是译者与原作者跨越广袤漫长的时空所进行的一场热烈诚挚的灵魂对话,任何一方灵魂的抽离,都会使这场激动人心的对话夭折。郭沫若的《周南卷耳》很好地实现了这种平衡:无论是译者还是原作者的灵魂都全程在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在译作中也实现了一种相互推动、相互深化的动态融合。
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基础上,郭氏增添、补充了丰富的细节,使得自由体的白话译诗《周南卷耳》呈现出一种宛如油画般鲜明、清晰、触之可及的画面感。同时,生性浪漫多情的郭沫若又赋予了全诗更加灼热缠绵的情感。不得不说,沐浴了五四精神的郭沫若,凭借他天才般丰沛的创造力、敏锐细腻的艺术直觉、炽烈多情的天性,的确为古老的《诗经》原作注入了鲜活年青的生命,增强而不是削弱了原作的感染力,实现了他在《卷耳集序》中所说的小小的野心。虽然时代精神和译者的艺术个性均无可避免地对原作产生晕染加工效果,但郭沫若并未过多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侵扰甚至取代原作的艺术风味,而是保持了对原作的基本敬意与尊重。
我们再来看郭氏的另一首《诗经》译作《郑风狡童》:“他真是一个坏蛋呵,/他始终不和我说句话。/‘你怎晓得我正是为了你呀,/我连饭也不想吃了?’//他真是一个坏蛋呵,/他始终不跟我亲个嘴。/‘你怎晓得我正是为了你呀,/我连觉也不能睡?’”郭氏的译作,用活泼风趣的口吻活画出恋爱中的小女子娇嗔痴憨、大胆泼辣的情态,用的是当下的口语,却惟妙惟肖地还原出《郑风狡童》原作中犯了相思病的小儿女的口吻,成功剥去了蒙在《诗经》上的厚厚“漆灰”,让掩盖已久的天真烂漫的民歌情调倾泻而出。郭氏所译《郑风褰裳》同样是一首大胆奔放、爱恨交织的“淫奔之诗”,以自由体白话新诗的方式进行翻译,充分释放了原作的内在激情:“你是真心爱我的时候,/不怕就有溱水隔着呀,/我也可以褰着裙子走过。/你是不爱我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别人了吗?/你个浪子呀,浪子!//你是真心爱我的时候,/不怕就有洧水隔着呀,/我也可以褰着裙子走过。/你是不爱我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别的冤家吗?/你个浪子呀,浪子!”
郭沫若的《诗经》今译,甚至赋予了古老的《诗经》作品以幽默喜剧的效果,打开了《诗经》阅读的全新审美维度,最突出的例子是他的译作《齐风鸡鸣》:“一位国王和他的王妃/在深宫之中贪着春睡。/鸡已叫了,日已高了,/他们还在贪着春睡。//王妃焦急着叫道:/‘晨鸡已经叫了,/上朝的人怕已经到了?’/国王懒洋洋地答道:/‘不是晨鸡在叫,/是蝇子们在闹。’//语声一时息了,/他们又在贪着春睡。/鸡已叫了,日已高了,/他们还在贪着春睡。//王妃又焦急着说道:/‘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人怕已经旺了?’/国王又懒洋洋地答道:/‘不是东方发亮,/是月亮在放着光。’//语声一时又息了,/他们又在贪着春睡。/鸡已叫了,日已高了,/他们还在贪着春睡。//王妃最后又焦急着说道:/‘啊,我愿同你永远做梦,/这情趣真是轻松。/上朝的人怕已经都散了,/难道不会说我们放纵?’//蚊子们嗡嗡地飞着,/王妃已经披衣起了床。/鸡已叫了,日已高了,/国王的春睡还是很香。”这首译作,可以明显看到西方文学对郭沫若的影响,无论所表现的场景还是人物的对话都有浓重的欧化色彩。原作本来只是妻子催丈夫早起,不要耽误了营生。经过郭沫若的改写,仿佛成了中世纪某个欧洲王宫里国王与王妃之间甜蜜的日常生活片断。在这首译作中,郭沫若个人的艺术趣味和创作冲动完全压倒了对原作的敬意与尊重,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被打破。虽然赋予了《诗经》全新的审美维度,但也因此严重篡改了原作的精神,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间失去了应有的平衡。
以译者的意图取代、消解原作者的意图这一令人不安的倾向,在郭沫若的译作《陈风墓门》(本篇曾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中表现得更加充分:“我每天到这墓地里来打扫,/坟上的荆棘我用斧头斫掉。/我的良人过不惯奴隶的生活,/这在全国的人都是已经知道。/他们骂他,但我总不肯再嫁,/古时候有没有这样痴心的女娃?//我每天到这墓地里来打扫,/猫头鹰站在梅花树上嘲笑。/我的良人过不惯奴隶的生活,/我是时常地唱着歌向他劝告。/我劝告他,但他终竟丢了命,/思前想后,怎能叫我不伤心!”《陈风墓门》本来是一首讥刺不良之徒自取灭亡的讽喻诗,到郭沫若笔下却成了一首讴歌不甘做奴隶者的反抗精神及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正气歌。在郭氏的译诗中,原作的精神内涵完全被架空,译作成为译者抛开原作的自说自话。单从翻译的角度说,《陈风墓门》是彻底丢失了原作灵魂的失败之作。不过,对大体成功翻译了《诗经》原作的《卷耳集》而言,《陈风墓门》只是为数不多的例外。
三
郭氏的《诗经》今译以诗人自身的创作实践,表达了郭沫若对诗歌翻译问题的基本看法:郭沫若反对笨伯式、注释式的诗歌直译,主张重在传达原作风神气韵的意译。这样一来,诗歌翻译,无论是古诗今译还是翻译域外诗人的作品,就不仅要求翻译者能深入领会作品原意,同时也要求翻译者自己也是一位诗人,能够用新的书面语表达方式传达出原作的内在精神。按照郭沫若的翻译理论,古诗今译,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注释式翻译,而只能是今天的诗人与古代诗人之间跨越时空的一次深度对话与灵魂碰撞。1923年5月上海《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郭沫若《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谈及郭氏对翻译问题的思考:“但是逐字逐句的直译,终是呆笨的办法,并且在理是不可能。我们从一国文字之中通晓一个作家的思想,不是专靠认识他的字面便能成功的。一种文字有它的一种气势。这在英文是Mood。我们为这种气势所融洽,把我们的精神随着它抑扬张弛,才能与作者的思想之羽翼载沈载浮。逐字逐句的直译,把死的字面虽然照顾着了,把活的精神却是遗失了。……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以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
翻译其实是创作,这是郭沫若一以贯之的思想:“……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的贡献,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重第三个条件,因为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谈文学翻译工作》,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是郭沫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译文要成为一件艺术品,关键是译者要从整体上真正把握原作的精髓,绝不能仅仅充当呆笨的直译者、注释者,以白话新诗的方式译出原作的神韵,也是接受文学遗产的可行之路:“……本来凡是中国古代的好的作品或好的书能够用口语把它们翻译出来,我看也不失为是接受文学遗产的一个方法。关于屈原的《离骚》,我从前曾经翻译过,但关于其它的作品至今还没有人着手。这项工作在别的国家是做得相当彻底的,在我们中国注释的工作虽然为历代文人所好尚,但总嫌寻章摘句,伤于破碎,没有整个翻译得那样的直切了当。”(《关于“接受文学遗产”》,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一月重庆《抗战文艺》月刊第八卷第三期)
之所以反对在诗歌翻译中过分强调直译、硬译,是因为在郭沫若看来,如果连诗之为诗的艺术规定性都取消了,连诗的外在形式和内在韵味都丧失殆尽了,又如何能传达出原作的诗性之美!这样的诗歌翻译,等于取消了诗歌的文学性,变得毫无意义。郭沫若在《谈文学翻译工作》一文中说:“……外国诗译成中文,也得象诗才行。有些同志过分强调直译,硬译。可是诗是有一定的格调,一定的韵律,一定的诗的成分的。如果把以上这些一律取消,那么译出来就毫无味道,简直不象诗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郭沫若的《诗经》今译,是其翻译思想的最初也是最成功的践行。在郭氏的《诗经》今译之作中,译者与原作者以《诗经》中所谓“淫奔之诗”、“郑卫之音”为桥梁,实现了诗人之间跨越漫长时空的灵魂对话与精神碰撞,并最终形成了《诗经》原作的艺术魅力与郭氏独特的艺术个性叠加之后的成果《卷耳集》。《卷耳集》是年青的郭沫若以五四精神对《诗经》作品充满个性与诗意的再诠释,也是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的自由体白话新诗对旧诗经典的致意与挑战。
(责任编辑:魏红珊)
[1]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郭沫若.卷耳集序[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胡适.新思潮的意义[A].胡适全集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4]郭沫若.卷耳集自跋[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郭沫若.关于文艺的不朽性[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郭沫若.周南卷耳[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郭沫若.简单地谈谈《诗经》[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9]郭沫若.郑风狡童[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0]郭沫若.郑风褰裳[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1]郭沫若.齐风鸡鸣[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郭沫若.陈风墓门[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3]郭沫若.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4]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5]郭沫若.关于“接受文学遗产”[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符:
A1003-7225(2017)03-0052-07
2017-08-17
曾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