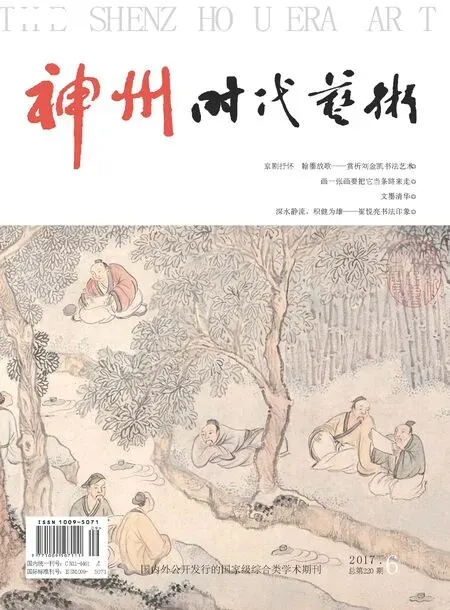故乡纪事
吴宝三
傻良子
回到呼兰河西的故乡小镇,已是月上中天的时候。如水的月光下,故乡的轮廓依稀可辨,记忆中的那条百米小街,两边的店铺还是旧时的模样,铁匠炉、棉花房、中药铺……门脸儿依旧,只是当年的风采已被雨打风吹去,显出无奈的疲惫。几乎让我辨认不出的是通往省城的那条柏油马路,路边一下子冒出春笋般的大红灯笼,来来往往的大车小辆,如同变戏法一般,一忽儿就不见了,无疑是被如织的酒帜饭幌笑纳进去。
我在一个远房亲戚家住了下来。问起五叔,每天早晨还有挑担卖菜的吗?街边儿的摊床该搬到大马路那边去了吧?五叔答曰,从形式到内容,如同桔枳、叶陡相似味道不同。你想找的“明朝深巷卖杏花”的人,怕难寻觅了。故乡是个有文化底蕴的老镇,五叔读过国高,不是村野之人,说起话来时有几句文言。他反过来问我,可曾记得道南出床子的那个傻良子吗?我说,当然记得,忘了谁也忘不了他。五叔沏上一壶茉莉花,爷俩一边喝茶,一边唠起这个当年二十刚挂零的青年,一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做生意的人。
傻良子,从小诚实、憨厚,良子前面加个傻字,是小镇上的人对他的昵称,我和小伙伴们都叫他良子大哥。他老家在陕北,西安事变那年同父母一起来到这个小镇上。在本地念完高小,先是跟父亲卖烧鸡,烧鸡做得绝好,远近出名。每天傍晚,傻良子背着一个小木箱,在小街没转上一圈就卖光了。我们小孩子给他编了两句嗑:傻良子卖烧鸡,不上东就上西。卖了两年烧鸡,攒了点钱,傻良子在我家对过摆了个摊床,卖点烟卷、散酒、糖果、瓜籽之类。我上小学的时候,每每路过摊床,良子大哥都给我抓把瓜籽或拿几块桔子瓣糖。吃惯的嘴儿跑惯的腿儿,家里要买东西,我就到这儿来买;做完功课,也愿意到这儿来玩。
我最喜欢看良子大哥簸葵花籽,一扇一扇的,扇去瘪子和灰尘,再拣出小石子和小块土坷垃,用湿毛巾反复搓揉干净,然后倒在大铁锅里急火翻炒。待炒好完全凉下来,良子大哥抓一把塞进我的衣兜里,一个个籽粒饱满,吃不出一个臭瓜籽来。有时,良子大哥像过家家一样,把酒罐子里的白酒,倒进另一只空罐子里,剩下一些全泼掉。长大后我才懂得,卖散装酒必须先用酒提搅动一番,盖因上面的是酒,沉下去的是水。我每回用锡壶给父亲来打酒,从没见过他在酒罐里搅动过,不管谁来打酒都一样。每当摊床进菜,良子大哥一捆捆打开,去掉“夹馅”,再一捆捆重新捆上。他总喃喃的自语道:“做买卖要讲诚信哪,不能靠这个赚钱!”
唠到这里,我忽地叉开话题问五叔,良子大哥和东街老葛家的三丫结婚没有?五叔叹道,棒打鸳鸯散了!葛老头出了名的抠门,整个一个葛朗台,嫌良子做生意心太实,没大出息。我说,三丫是良子下两届的同学,能歌善舞,不管在学校还是镇上演戏,一招一式都是良子教出来的呀!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男女,那么般配,海誓山盟,怎么说散就散了呢!五叔似猜透我的心思,接着说,惨啦!“葛朗台”要拆散这桩婚姻,先是不让两人见面,后来来个釜底抽薪,找个人家嫁到河东去了。从此,傻良子寡言少语,谁说媒也不打拢,一门心思做生意,公平买卖,童叟无欺,从摊床起步,竟成为全镇最大的土杂商店掌柜。良子傻就傻在太痴情了,孑身一人,终身未娶。
我和五叔久久无语,对“葛朗台”导演的悲剧几近愤怒。令人酸楚的是这出悲剧的结局:每年仲夏时节,人们常常见到傻良子一个人坐在河边,默默向远方眺望。夜深人静之时,镇上的人便能听到傻良子如泣如诉的二胡声,那是陕北民歌《泪蛋蛋落在沙蒿蒿林》——“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人们说,呼兰河是“葛朗台”仿效王母娘娘划出的一道天河,傻良子定是期盼着这一天,同三丫能在鹊桥上见上一面。
丫 头
丫头是个男孩,姓常,浓眉大眼,虎头虎脑,我儿时的光腚娃娃。他爷爷为何给他起这个乳名,怕是家里想要个女孩的缘故。我上学后方知,丫头的生日应该是夏天,要不怎么能有这么一套嗑:常老大家小大嫂/南下洼子摘豆角/一小筐没摘了/肚子疼往家跑/掀开炕席铺上草/老牛婆请来了/不是丫头就是小。这当是丫头呱呱落地降临人间的真实写照。
六、七岁的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长在老常家,特别喜欢他家那片大菜园子,一到春天,菠菜、毛葱、生菜、水萝卜下来了,又新鲜又水泠。到了盛夏,白里透绿的洋白菜正在包心,一片片菜叶子如同一个个扇面,搧动五颜六色的蝴蝶翩翩起舞,我俩把扑来的大蝴蝶小心翼翼夹在课本里,不是做标本而是当书签。天大热,我和丫头从麦地草丛里逮回几只蝈蝈儿,放进柳条儿架的黄瓜地里,然后再去逮,垄台踩平了,黄瓜架塌架了,我们才不管呢,还把刚刚坐胎儿的小黄瓜扭儿,硬往蝈蝈儿嘴里塞。这时,丫头的二姨从屋里跑出来,像轰小鸡似的,把我们从园子里往出赶,“死丫头,还不快上别场去玩,一会儿你二叔回来还得揪你的小鸡鸡!”二叔也是丫头的二姨夫,有时叫叔有时叫姨夫,我也弄不清楚辈份的事。年纪大点才明白,丫头的妈妈和二姨是一对孪生姐妹,爸爸和二叔是一对孪生兄弟,两家连亲,亲上加亲。丫头才不管揪不揪小鸡鸡,照样疯玩。疯累了,我们用镰刀割几根玉米杆,坐在地头大吃大嚼起来。听见大门口传来脚步声,猜想不是爸爸就是二叔回来了,他拽着我的手,猫着腰,顺着田塍夺路而逃。丫头家的菜园子,是淘气包子的天堂,那里盛下了孩提时代太多太多的乐趣。
上学了,我和丫头分在一个班,每天形影不离,依然常在一起嬉戏打闹。上南大泡子洗澡,下夹子打鸟,去大草甸子拣野鸭子蛋。我俩订立攻守同盟——谁也不许和家里人说。丫头胆子大,敢在学校的土围墙上翻筋斗、打把式,吓得我心惊胆战;他教我扶着墙头踩高跷、立大顶,我学到许多让同学们眼红的本领。有一样本领我学不来,那就是吃土垃坷,丫头像吃软糖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坐在墙根儿下一气儿吃个五六块不在话下。我以为他家比我家穷,吃不饱饭,大人说,这孩子肚里有蛔虫,因为穷,买不起药。
丫头绝顶聪明,特别喜欢看小人书。看过一遍,便能讲述下来。一日,把几个小伙伴约到他家后道闸,支起一个小木框贴张大白纸的影窗,自编自导,演起皮影戏来。演到哨兵在村头巡逻,丫头说,上自习时杨老师总管咱们,在教室走来走去,像不像这哨兵?咱们管他叫杨巡逻吧!小伙伴们齐声说好,一阵欢呼雀跃,丫头忙用手捂上嘴,示意大家小点声,别让前屋的爸妈听见。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这个外号居然在班里传开了。一日开班会,班主任杨老师把我叫到教导处,脸上堆满笑容,很和气地问我,老师的外号是谁起的呀?我低头不语。杨老师忽地站起来,怒发冲冠,拍着桌子吼道,你不说,去找你爸妈!我一下子被吓住了,去找家那还了得,只好从实招认,供出了丫头。回到教室,丫头被叫到讲台前罚站,在众多同学面前哭了,那一行行泪珠,流在他的脸上,重重地砸在我的心头。
班会开了一堂课,丫头一直在前面站着。终于放学了,丫头似啥事没有发生,和每天一样,招呼我一道回家。我惴惴不安,好像刚刚偷了人家的东西被发现了,蔫头耷脑,愧疚不已,几欲想说声对不起,终未能张口说出来。这件事在我心里打下很深的烙印。
小学毕业后,我和丫头天各一方,音信两茫茫。听家里人说,他进了皮影剧团,我看也算“专业”对口了,然而,后道闸演皮影戏引发的风波终难忘却。上中学、上大学,我每每在小说或电影中看到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总把自己同《红灯记》中的王连举相对照。多少年后回到故乡,同学们在母校聚会,我忍不住提起这档子事,丫头听罢哈哈大笑道,我早忘了。外号是我起的,你被老师闷了一顿,这是替人受过……一席话令我鼻子发酸两眼发热。尽管丫头如是说,为当年不能挺身而出,分而担之,岂能不省身思过?我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动情地说,让我再叫你一回吧——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