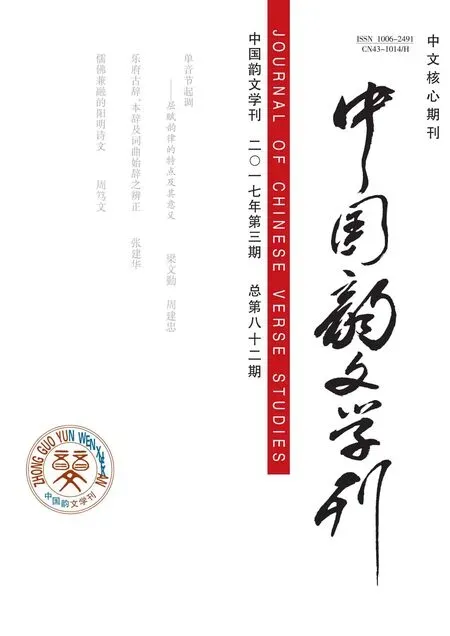清代词韵制作与词谱之学
胡宪丽 江合友
(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清代词韵制作与词谱之学
胡宪丽 江合友
(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清代词谱在文献和理论方面对词韵制作提供支持,词韵则使词谱的制订有更加明确的标准。词谱和词韵互为依存,词谱包含词的韵法,词韵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词韵的制订使得词谱趋于完整。词韵制作的理论和规范发展成熟之后,词谱制订者有详实系统的词韵作为参照,有意识地借鉴词韵研究的新成果,其词谱的编纂质量往往能够得到提高。
清代;词韵制作;词谱;关系
清代词学昌明,词韵制作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留下了为数不少的词韵专书,粗略估算,词韵专书的数量当不少于23种。清代词谱则为数更多,笔者知见的专书有近60种。作为词体声律之学探讨的重要方式,词韵与词谱相辅相成,互为取资,其间关系甚为密切。充分理解词韵与词谱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清代词学、词史甚为重要,但目前学界对此尚无专门探讨。本文不惮谫陋,拟对词韵与词谱之间既互相依存又彼此影响的关系予以揭示,以就正于方家。
一
词谱是词体声律的归纳和总结,使填词创作有格律形式的规范,所涵盖的内容包括词体的若干方面,其中词的押韵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词谱在文献和理论方面对词韵的制作提供支持,词韵则使词谱的制订有更加明确的标准。词谱和词韵互为依存,词谱包含词的韵法,词韵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两者的目的均在于为词体立法,词韵的制订使得词谱趋于完整。
在文献载体上,词韵多附刻于词谱之末,至清代中叶以后始渐独立成书。清初沈谦所编《词韵略》,开始是收录于毛先舒的《韵学通指》,这是音韵学的专书,后被收录于《倚声初集》《古今词汇二编》《瑶华集》等词选,再到被收录于《纪红集》等词谱,从未有独立的文献形态,这自然与其篇幅的短小有关。但后来的词谱制作,也满足于“吟啸之需”,服务于“取便携阅”,尽量控制篇幅和规模。吴绮《词韵简》先后附刊于《选声集》和《记红集》,《选声集》更倾向于选词,而《记红集》则近于订谱,《词韵简》不具备独立性。吴绮编词韵的目的很明确,即为押韵须严之词体设立规范。《记红集凡例》指摘唐词多遵诗韵,而宋名家押韵“亦多出入,往往真庚相混,甚有杂入东韵者”,这种带有随意性的作法是因“词韵无定本也”。对时人填词的押韵,吴绮虽赞为“备美”,但从其自称《词韵简》“似为妥确”的语气,可以感知其中的批评之意。仲恒编《词韵》原仅为自己创作的参考,因从王又华所请,刊行面世。仲恒为出版编订其书时充分考虑到独立成书的问题:“诗韵严,而古风每至百余韵,词律宽,而一韵不过数字。凡奇僻字面,诗韵不妨备载,词韵似无所用,且诗近古,押字不妨奇奥;词近今,倘字太生,则观者触目。然一概削去,恐不成书,今但稍为次第。”除收字较多之外,卷前还选录各家词韵之论,使之在体制上更加完善。虽具备独立成书的规模,仲恒《词韵》还是作为《词学全书》的一部分而存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与赖以邠《填词图谱》配套,这是视词韵为词谱之辅助的观念所致。李渔的《笠翁词韵》,发凡起例,一应俱全,并以“专刻”自期,仍然只是附于自撰《耐歌词》之后。郑元庆编订《三百词谱》,书末附己编《词韵》一卷;李文林编《诗余协律》,书末附《绿雪轩词韵》,郑、李所编以因袭为多,之所以校勘删补以前的词韵,是考虑到词谱有词韵附翼才能发挥好指导创作的功用。故嘉庆初年怡亲王讷斋重刻《白香词谱》时,也加上了《晚翠轩词韵》。叶申芗《天籁轩词韵小引》则说得比较明确:“余既编成词谱,不可无词韵。”与此类似的是钱裕的《有真意斋词韵》,均是先编成词谱,再制作词韵,形成配套。
词谱并不一定要附上词韵,但对于词韵的标准也须表明态度,多在凡例中加以说明。万树《词律发凡》:“词之用韵较宽于诗,而真、侵互施,先、盐并叶,虽古有然,终属不妥。沈氏去矜所辑,可为当行,近日俱尊用之,无烦更变。”明确申明以沈谦《词韵略》为准。秦巘《词系凡例》云:“国初沈去矜《词韵》,考据该洽,部分秩如,可为填词家指南。近时吴门戈顺卿《词林正韵》,较沈氏尤为精密。以视《学宋斋》、《绿漪亭》等书,则高出百倍矣。”对于词韵专书的取舍,是词谱编纂者必须关注的问题,万树、秦巘为词的格律设立规矩,同时也需要观察词韵并做出判断,词韵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词谱著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词韵制作需要以词谱为基础,尤其是当词谱的理论和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就会推动词韵走向成熟。在词韵轮廓始创之时,就没有脱离对于词谱的依赖。沈谦发现“博考旧词,裁成独断”的纂韵方法,就来自对词谱的体认。据毛先舒《与去矜书》“《词苑手镜》一书,必行必传”的记载,沈谦曾编过词谱《词苑手镜》,对于词的格律有过甄选归纳的经验,对于“名手雅篇”在格律上所谓“灼然无弊”是很重视的。沈谦抽样调查词的押韵情况,操作基础应该就来自于其制谱选词的实践经验。对于词韵的四声问题,明人虽有认识,至沈谦始明确下来,也当是得益于他对词谱的考订。《词韵略》的开创性和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以词谱编纂为前期准备。
在词韵制作史上,沈谦的成功经验具有普遍性,清代具有开拓意义的词韵均是如此。戈载编撰《词林正韵》之前,曾遍访词集,对《词律》一书下过很深的功夫,《词林正韵发凡》:“词谱则万氏最为精审,而犹多阙略,由其所见书少,且律吕不明也。”计划撰《词律订》来纠正万树书中的错误。因此,戈载对词中用字和韵脚的入派三声情况能看得更为全面和透彻,于是在词韵体例上予以改进。同时,戈载全面注重词的整体韵法,即不仅要为韵脚字立法,也要让词中的每一个字的平仄四声有规矩可循。《词林正韵》在词韵制作方面成就巨大,其根源在于戈载对词谱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予有订定《词律》之举,而尚未蒇事。凡在旧编,间多新得。即词之用韵,亦藉此参互考订,引申触类而知之耳。”谢元淮的《碎金词韵》探索词韵与音乐之间的联系,令人耳目一新。关键在于编者在词谱编纂方面有自己的思考。《碎金词韵》细辨韵字阴阳清浊,乃是配合《碎金词谱》以曲乐唱词的需要。谢元淮为实行其《碎金词谱自序》所谓“协律和声”,务使词的音节有“抑扬抗坠之妙”的词体主张,广泛征引各类韵书,每一韵字的字义、反切、五音、阴阳、入派三声的情况均有标注,使得《碎金词韵》的综合性大大增强。制韵主体和订谱主体的重合,说明谱、韵关系的紧密,更重要的是订谱本身可以成为制韵的工作依据,由对词体认识的深入推动词韵体例和内容的进一步完善。
二
独立成书的词韵,其制作者虽无订谱实践,但仍须对现有词谱进行研究并予以借鉴。为制作《学宋斋词韵》,吴烺、江昉等曾将沈谦《词韵略》与宋词韵脚相印证,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朱彝尊、汪森所辑《词综》和万树《词律》中所收词例,结果发现“沈去矜所辑,按以宋元人所押,未能尽合”。出于对姜夔、张炎词作格律的信任,吴烺等步趋姜、张词的韵法,以之作为制韵的宗旨。对于姜、张韵法的判断要对词体格律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知识储备,而考察其韵法的同时就是对其语言形式的把握。从《学宋斋词韵例言》以“订谱则有《词律》”作为词学“极盛”的标志,表明吴烺等人在全面考订张炎词的韵谱时,其分析的依据应当就是《词律》。
吴宁《榕园词韵》主张“上去分列,不统于平,入复更定”,其理由是“词体几千又二百,三声互叶才一十有奇,不得以少概多”,所以上去声不应被平声统领,而应另外分部。此即吴宁研究词谱之后获得的体会,《榕园词韵发凡》云:“北曲韵平上去三声互叶,入声分隶三声,南曲三声互叶,入声独叶,词则平仄各叶。其大较也,若[西江月]、[少年心]、[戚氏]、[换巢鸾凤]诸体,亦三声互叶,实曲学滥觞,非词家标准。[干荷叶]、[平湖乐]、[天净沙]、[凭栏人]之类,乃元人小曲,误援入词,编韵者据是定部,总合三声,殊无分晓,虽中诠平仄,昧厥大纲,骤观易惑。”三声互叶在词体中绝少,故不能据以分定韵部,这一判断是基于对不同词调押韵之法的观察,而对词调韵法的分析和归纳正是词谱用力之处。至于论元人小曲不可援入词体,则基本袭自万树的论断,《词律发凡》:“[西江月]等,宋词也;[玉交枝]等,元词也;[捣练子]等,曲因乎词者也,均非曲也。若元人之[后庭花]、[干荷叶]、[小桃红](即[平湖乐])、[天净沙]、[醉高歌]等俱为曲调,与词声响不侔,倘欲采取,则元人小令最多,收之无尽矣。”将万树这段话与上引吴宁《榕园词韵发凡》比较,不难看出两者有雷同之处。这表明吴宁曾认真读过《词律》一书,在制韵原则的拟定方面以之为参照。在《词律》《钦定词谱》较为通行的情况下,对于不同词调体式的韵法可以看得更加全面清楚,省去了繁冗的初级调查,而可直接援之为制韵依据。整体而言,词谱例词是填词格律的典范,在句式和韵法上均合乎规则,以之为据考察词韵具有相对的优越性。
词韵制作者既无订谱实践,又不参考借鉴词谱,就容易脱离词体韵法的实际,因而成绩不大,词学地位也不高。李渔《笠翁词韵》就是如此。他专门强调词与诗、曲之别,《窥词管见》说:“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在其《词韵例言》中又从韵的角度重申此论:“诗韵严,曲韵宽,词韵介乎宽严之间,此一定之理也。窃怪宋人作词,竟有全用十灰一韵,以梅、回、陪、催等字与开、来、栽、才等字同押者,此失于过严而不可取法者也。夫一词既有一词之名,如[小桃红]、[千秋岁]、[好事近]、[风入松]之类,明明是一曲体,作之原使人歌,非使人读也。曾见从来歌者,有以‘梅’字唱作‘埋’音,‘回’字唱作‘槐’音者乎?若无词韵一书作准绳,则泥古之士,必为前人所误,得词之名而失其实矣。今人作词,无所取法,又有以《中原音韵》为式者。至入声字与平上去同押,是又失于太宽。……词则始于唐宋,乃后世之文也。后世之文,其韵务谐后世之音。二语洞然,可息纷腾之议。是集操纵得宜,宽严有度,务使严不似诗,而宽不类曲。词之面目,已全现乎声韵中矣。”可以看出,李渔在编《笠翁词韵》时有一定的辨体意识,而且也对部分词例做了调查。然而其编辑之法,更多的是在现有韵书的基础上进行变通。《词韵例言》认为沈谦《词韵略》和毛先舒《词韵括略》因无专刻,见者寥寥;赵钥《词韵便遵》虽以沈、毛二人论议为准,却步趋诗韵,未能“变通作者之意”,故李渔自己动手编订《笠翁词韵》。但李渔对词的韵法态度不够严谨,因为所谓“宽严之间”界定的很是模糊。在他看来,词韵与诗韵之别在于打破诗韵规模,作者需要明白韵部之间通押的道理;词韵与曲韵之别则在于词乃入声独押,曲则入派三声。《笠翁词韵》的韵部编排遵循“词则全为吟诵而设,止求便读”的原则,大量参考今音。这或许与李渔的求异思维有关,《词韵例言》说:“才细如丝,胆大于斗,故敢纵意为之,知我罪我,悉听于人,有延颈待诛而已。”如此一来,《笠翁词韵》就与曲韵更为接近,总体来说,“与《中原》韵系相近”。李渔制作词韵时大量借鉴《中原音韵》,入声独立是符合词体入声独押的特性,同时他还想要用为南曲创作的指南,实际上在词韵与曲韵之间持骑墙态度。因此《笠翁词韵》撰成之后,词坛反应冷淡,很少遵用者,戈载在《词林正韵发凡》中大加挞伐,说李渔“以乡音妄自分析,尤为不经”。
许昂霄的《词韵考略》与《笠翁词韵》类似,不过在韵系方面与古诗韵更为接近,“词韵通转,当仿古韵之例”。而其“平声宜从古,上去可参用古今,入声不妨从今。平声宜严,上去较宽,入声则更宽”之论,则主张古今互参,在规范上不太严格。许昂霄虽无编订词谱的实践,但他精熟《词综》,其门生张载华辑其评点之语,成《词综偶评》一书。《词韵考略叙》云:“浏览旧词,考索同异。北宋则以六一、珠玉、小山、淮海、东堂、清真数公为主,而旁参东坡、山谷,南宋则以放翁、白石、梅溪、竹屋、竹山、玉田数公为主,而旁参稼轩、改之诸家。至于唐之温、韦,五代十国之和、毛、孙、冯,为倚声家初祖,押韵固无可议。”许氏确定韵部通用原则之时参考了唐宋时期重要的词家词作,但他没有参考已经刻行的《词律》《钦定词谱》等书,因而考察宋词的押韵不够细致,也不够系统。他所归纳的“通”“转”“叶”的词韵法则,自然难以被词坛认可。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曾予以评论:“许蒿庐《词韵考略》言古今通转及借叶法,说本楼敬思《洗砚斋集》,可取以补榕园所未备。但其所云古今通转,仍当标《广韵》部目,借叶则当注借叶某部某字,庶不至因一部而累及数部,因一字而滥及数字,为识者笑也。”此处指出《词韵考略》标106韵目的缺失,以及“借叶”注释的过简,是其体例上的漏洞;又认为此编可以与吴宁《榕园词韵》互补,实际上如何互补缺少可操作性。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许昂霄考察宋词押韵时,片面强调了其不规整的一面。杜文澜认为:“宋词用韵有三病:一则通转太宽,二则杂用方音,三则率意借协。故今之作词者,不可以宋词用韵为据。”这些毛病毛先舒曾称之为“宋人误处”,而许昂霄则据以认为词韵宜宽。所以戈载对《词韵考略》颇为不满,说:“不知所谓古今者,何古何今?而又何所谓借叶?痴人说梦,更不足道!”《词韵考略》影响甚微,虽被其门人张宗橚收入《词林纪事》,却未能成为后来讨论词韵的重要参照。
三
词韵制作的理论和规范发展成熟之后,词体韵法必将形成一系列共识,那么词谱的编纂就必须在这些共识的指导下进行。有系统明确的词韵为指导编订的词谱,其学术质量能够得到整体提升。
明代词谱编纂质量普遍不高,除去编者词学视野所限和态度不严谨之外,也和词体声律知识基础较为薄弱有关。张綖、徐师曾、程明善等没有提出自己的词韵主张,谢天瑞编《新镌补遗诗余图谱》时曾经试图创制词韵,其书已亡佚,但从毛先舒“谢天瑞暨胡文焕所录韵,虽稍取《正韵》附益之,而终乖古奏”的评语看来,与胡文焕《文会堂词韵》差不多,词曲界限尚不明确。
到康熙年间,万树纠驳明代及清初词谱的谬误,撰写《词律》一书时,词韵已有专书,沈谦《词韵略》已然流传开来。万树《词律发凡》表达了对《词韵略》的充分肯定,认为“无烦更变”,那么《词律》一书基本是以《词韵略》的韵系为音韵准则的。万树还表示:“今将嗣此有三韵合编之刻。”可惜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词律》刊行后的次年,万树便逝世了。此处“三韵合编”应该是诗韵、词韵、曲韵的合编,其中词韵部分一定会以《词韵略》为制韵依据,以其编《词律》所得的词体韵法经验,也将会为《词韵略》的修订提供独到的新见。万树分析词的韵法,因有《词韵略》的指导,使其更容易发现问题,如《词律》卷十六分析[渡江云]词调:“平仄互叶,往往有之。如[西江月]等显然者,人知之。其它人多未察,遂致失韵。如此‘更漂流何处’,正是以‘处’字去声叶上‘初’、‘鉏’等平韵。余初于片玉‘晴岚低楚甸’一首用‘指长安日下’,谓其以‘下’字叶‘沙’、‘家’等韵,人多不信。及观千里和词,亦用‘遏离情不下’已为明证。而玉田此词,亦以‘处’字为叶,及别作是‘纱’、‘佳’等韵,此句云:‘想萧娘声价。’吴草庐作是‘妆’、‘霜’等韵,此句云:‘似长江去浪。’草窗作是‘茵’、‘云’等韵,此句云:‘数幽期难准。’詹天游作是‘声’、‘情’等韵,此句云:‘掩重门夜永。’历观诸家如此,岂非此句皆以仄声叶平乎?若不细察,则少却一韵矣。”平、上、去三声互叶的原则在《词韵略》中被确立为韵部编排原则,平、上、去三声十四部的编排,使平声和仄声的对应十分清楚,因此押韵之处用了本部字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渡江云]通首押平声韵,仅有一处换成仄韵,如非仔细摸排,容易放过去,从而造成词谱失韵的情况。万树发现这一细节,找来其他词作进行对照,最终确定这一平仄互叶的规则,在“更漂流何处”之下注明:“换仄叶”。由此可见明确的词韵规范对词谱编纂有着明显的帮助。
当代表清代词韵制作最高水准的《词林正韵》刊行之后,同样对词谱编纂起到了推动作用。秦巘《词系发凡》说明其信从《词林正韵》之意,以为词韵专书中,《词林正韵》较之《学宋斋词韵》等“高出百倍”,并云:“各调已间论及,勿须另谱。”用以指导词谱的制定,其中许多论断见于各调的说明。秦巘订谱习惯于在例词后分析字的平仄,其中取资戈载《词林正韵》之处甚多,举[一寸金]词调即可明了。[一寸金]又一体选周邦彦词,下阕末句为“便入渔钓乐”,秦巘注曰:“‘便入’二字,吴、陈皆用平,是以入作平也。”此处即借鉴了戈载“入作三声在句中者”之论,戈载在举例时也提到了周邦彦[一寸金]“便入渔钓乐”这一句。秦巘为了分析的可靠性,还引证了吴文英二首词和陈允平的和词。其他戈载所举证之入作三声之例,在《词系》中大多得到了借用。如[凉州令]又一体用晏几道词首句“莫唱阳关曲”,秦巘注曰:“‘曲’字是以入作去押韵,各家首句俱用韵也。”在《词林正韵》中有这样一段话:“晏几道[凉州令]‘莫唱阳关曲’,‘曲’字作邱雨切,叶鱼虞韵。”这显然是将戈载所论应用于制订词谱的实践之中。这充分表明,词谱制订者有详实系统的词韵作为参照,有意识地借鉴词韵研究的新成果,其词谱的编纂质量往往能得到提高。
[1]江合友.《词韵略》与词韵流派传衍考论[J].汉学研究(台湾),2009,27(3).
[2]江合友.清代的词谱文献[M]//明清词谱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吴绮.记红集[M].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4]仲恒.词韵[M].康熙十八年刻《词学全书》本.
[5]叶申芗.天籁轩词韵[M].道光十一年刻天籁轩五种本.
[6]万树.词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秦巘.词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8]毛先舒.潠书[M].《四库存目丛书》影印康熙间刻思古堂十四种本.
[9]戈载.词林正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谢元淮.碎金词谱[M].道光二十八年朱墨套印本.
[11]吴烺,等.学宋斋词韵[M].乾隆三十年刻本.
[12]吴宁.榕园词韵[M].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13]李渔.笠翁词韵[M].康熙十七年刊《耐歌词》附刻本.
[14]麦耘.《笠翁词韵》音系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1).
[15]许昂霄.词韵考略叙[M]//张宗橚.词林纪事.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2.
[16]吴衡照.莲子居词话[Z]//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杜文澜.憩园词话[G]//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 雷 磊
2017-03-1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词体声律研究与词谱重修”(项目编号:15ZDB072)
胡宪丽(1980— ),女,河北石家庄人,在读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江合友(1978— ),男,博士后,教授。研究方向为词学。
I207.23
A
1006-2491(2017)03-008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