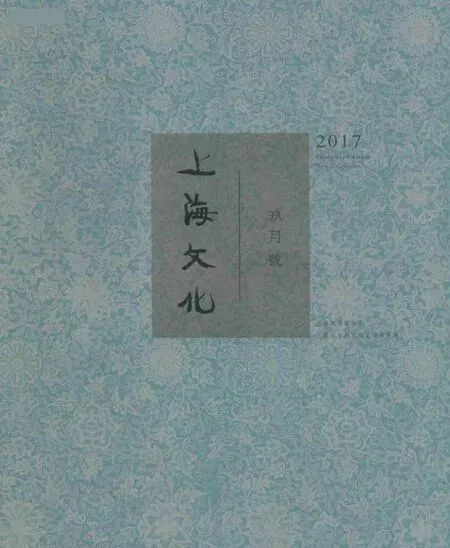奥威尔的名单①
蒂莫西·加顿·阿什
Violaine 译
奥威尔的名单
蒂莫西·加顿·阿什
Violaine 译
真的,我终于看到了那份1949年5月4日进入外交部半秘密部门的档案,那是乔治·奥威尔众所周知的“秘密共产党员”名单。它就在我面前,装在米色文件袋里,放在一名外交部高级档案员的办公桌上。尽管围绕着这份名单发生过许多争执,但自1949年5月2日,根据乔治·奥威尔从病床发送的原始名单的正式打印稿交给他的密友西莉亚·柯万(她刚刚开始进入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门IRD)之后,整整五十四年没有一名非官方人员被允许查阅它。这份名单中包括三十八名记者和作家的名字,这些人,据奥威尔4月6日写给西莉亚的信中说到,“在我看来,都是秘密共产党员,或是同路人、左倾分子,不能被信任作为宣传工作者。”
奥威尔的名单分为三栏内容:姓名、职业、备注,备注中有些带有模棱两可的说明。这个名单中有查理·卓别林、J·B·普利斯特利,还有演员迈克尔·雷德格雷夫,这些人的名字后面标着“?”或“??”表示吃不准他们是真正的秘密共产党员还是共产党同路人。国际关系历史学者E·H·卡尔的名字标注着“仅绥靖”而被划去。《新政治家》杂志编辑肯斯利·马丁是奥威尔讨厌的老家伙,所以就给了他一个醒目的挖苦评注——“??此人太不诚实,以至于很难直截了当地称他为‘秘密党员’或是‘同路人’,但他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倾向于苏俄的。”在《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沃尔夫·杜伦蒂和前托洛茨基派作家以撒·多伊彻(“仅同情”)名字下面是许多不太知名的作家和记者,第一个是《曼切斯特卫报》的企业报道记者,他被奥威尔形容为“可能仅是同情。好记者。愚蠢。”
在过去的十年里,“奥威尔名单”一直是许多骇人听闻的文章的主题,诸如“外交部的老大哥”、“社会主义偶像成了举报者”以及“奥威尔的黑名单帮助了秘密警察”之类。所有这些关于《1984》作者的猜臆性谴责,无不基于以下三个不完整的来源:许多出版物(并非全部)中奥威尔私密笔记(他在其中尝试标注的“秘密党员”和F·T·,这是同路人的缩写)条目,已出版的他与西莉亚·柯万的通信,以及甚至是几年前刚刚部分解密的外交部情报研究部门的相关文件。但是在外交部FO 1110 / 189文档中,奥威尔于1949年4月6日写给西莉亚·柯万的信旁边插入了一张卡片,标注着一份文件被扣留了。
由于女王陛下的政府对于保护奥威尔最后秘密的强烈关注,这件事被搁置起来,直到去年(2002年——译注)西莉亚·柯万去世后不久,她的女儿阿莉亚娜·班克斯,在她母亲的文件中找到了这份名单的拷贝,她于是就请我来写这件事。我们把名单发表在《卫报》上后,我去找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要求解密原件。他同意了,“反正所有这些信息现在都已经属于公众领域”,对此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在适当的地方看到。
一
就这样,文本就在眼前了。他当时为什么要写下这个名单呢?1949年2月,乔治·奥威尔躺在科茨沃尔德一家疗养院里,一年来,结核病几乎要了他的命,他已奄奄一息了。这年冬天,重新打印 《1984》(他对英国一旦屈从极权主义的后果的严厉警告)这项工作耗尽了他最后的体能。四十五岁的他非常孤独,对自己健康状况不抱希望,对前苏联前景深深悲观,因为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几乎以生命为代价,亲身经历了那种体制的残酷和背信弃义。捷克斯洛伐克被攻陷,他们现在又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边界,试图扼住那座城市来逼迫它屈服。
他感到一场战争已迫在眉睫,一场“冷战”,他很怕西方国家会输掉这场战争。他认为我们会输的一个原因,就是公共舆论的盲目。这种盲目,部分可以理解的态度是因为苏联抵抗纳粹所起的作用。但这也是那些多愁善感和天真的崇拜者们的毒性在发挥作用。
但他也知道,现在那些真正的信徒变得越来越令人厌恶了。有人成为《失败的上帝》(冷战时期一本著作,汇集了理想幻灭的六位作者的文章和谈话,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注)一书最尖刻的批评者,点名批判阿瑟·库斯勒和工党国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共同编辑的那本著名的书。《失败的上帝》于1950年1月出版,就是奥威尔逝世的那个月,克罗斯曼为此书写了导言,库斯勒、斯蒂芬·斯潘德和伊格纳齐奥·西隆也都为此书撰文。奥威尔确信,这些作者对于像他这样的左派尤为重要,就像他自己所写的,“如果我们想要重振社会主义运动,苏联神话的破灭是必须的。”1940年代中期的某一时刻,他开始秘密记下一些笔记,在那里边,他试图甄别谁谁谁是什么样的人:彻底的CP分子,代理人,“F·T·同路人”,多愁善感的同路人……
这本笔记(我现在可以在伦敦大学学院毫不受限地参看这本笔记)表明,他一直都在为这份名单操心。名单是用钢笔和铅笔写成,有些名字用红蓝色标注出来。一共有一百三十五个名字,其中有十个名字被划去了,八个是因为人已去世——如纽约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或许奥威尔认为他已不是同路人了,如历史学家艾伦·约翰·泰勒的名字就因此被划去,同样处理的还有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对他,奥威尔撤销了早先的判断,下了新的评注:“不。谴责了捷克政变和弗罗茨瓦会议。”斯蒂芬·斯潘德(“多愁善感的同路人……有同性恋倾向”)以及理查德·克罗斯曼(“太不诚实以至不能明确被算作同路人”)的名字还未被划去,因为那本《失败的上帝》尚未出版。对于这些评估,奥威尔显得极为纠结的人是J·B·普利斯特利。他的名字旁有一个红色星号,后来上面又打了个黑色的大叉,然后又用蓝笔加了一个问号。
对这个压抑而患有致命顽疾的天才政治作家个人来说,1949年2月倒是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西莉亚·柯万(中间名佩吉)从巴黎回到了伦敦。西莉亚是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年轻姑娘,热心,活泼,漂亮,她和双胞胎姐姐玛麦恩一样,加入了左翼文化圈,玛麦恩嫁给了奥威尔的朋友阿瑟·柯斯勒。1945年圣诞节,奥威尔与玛麦恩和柯斯勒夫妇以及西莉亚一起度过,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西莉亚。这一年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情感动荡,形单影只很孤独。西莉亚和他相处得很好,后来他们在伦敦又见过几次。在他们首次见面后五个星期的某天晚上,他给她写了一封激情洋溢的信,信中柔情脉脉但又笨拙不堪地向西莉亚求婚求爱。信的结尾是,“晚安,我最爱的爱人,乔治。”西莉亚委婉地拒绝了他,她后来把这封求爱信描述为一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信”,但他们维持了良好的亲密关系,成为密友。一年后,她去巴黎的情报分析部门工作。
“最亲爱的西莉亚”,他在2月13日从科茨沃尔德疗养院给她的信中写道,“真高兴你在来信中说你又回到了伦敦。”“我要给你寄一本我的新书(即《1984》),我想可能会在6月份出版,但我想你可能不会喜欢,因为这真的是一本可怕的书。”他说他希望“找个时间,也许是夏天,能见到她”。信后的签名“很多的爱,乔治”。
西莉亚来得比预期的更快,3月29日,西莉亚到格洛斯特郡来拜访他了,但她这次来还带有任务。她已经在外交部新的部门工作了,正在反击斯大林最近刚刚建立的工人党情报局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攻势。他能帮上忙吗?在她记录下来的他们会面的正式备忘录中,奥威尔“表达了全身心赞同我们的目标的热诚”。他自己不能为信息研究部写任何东西,因为他病得很重,而且也不喜欢“受委托”写作,但是他建议有些人可以写。4月6日,在一封笔迹纤细规整的信后面,他提出自己有一份名单,认为其中那些人,“不能被信任委派做宣传工作。那份名单记在一个笔记本里,笔记本在家里,我会寄给你,如果我向你提供了名单,那份名单必须是保密的,因为我觉得把某些人描述为共产主义同路人会被认为是一种诽谤。”
西莉亚把这封信转发给了她的上级,亚当·沃特森,后者写了一些评注,又加了几句话——
此外,柯万太太应该要求奥威尔先生提供那份秘密共产党员名单。她务必“以充分的信任来处理这份名单”,然后一两天后寄回去。我希望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都能给出可靠的理由。
柯万太太按照上级的要求做了,她于4月30日写了一封信,寄自“卡尔顿府街17号,外交部”——
亲爱的乔治,非常感谢你有益的建议。我的部门对那份名单很有兴趣……他们对我说,如果你能让我们看到你的那份同路人和秘密党员记者的名单,他们将会非常感激:我们会极为慎重地对待这份名单。
她的信是打印格式的,带有文件名FO 1110 / 189,信的结尾处落款比他的要冷淡些:“你永远的,西莉亚。”
与此同时,奥威尔要求他的老朋友理查德·里兹把那个笔记本从他遥远的苏格兰的吉拉岛家里(他曾在那里写作《1984》)寄来。关于此事,幸好他于4月17日为此写了一封信——
柯尔[即历史学家G·D·H·柯尔],我觉得也许不该搁在名单上,但我对他不如对加斯基那样有把握,假如来一场战争……整件事情非常蹊跷,而且,你永远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判断力,而且每件事都需要分别应对。
所以,我们必须想象奥威尔憔悴凄凉地躺在疗养院病床上,从头到尾查看笔记本,或许在普里斯特利名字下的红色星号后面又加上蓝色问号,然后又打上黑色的叉号,为柯尔或拉斯基,克罗斯曼或斯潘德,心里犯着嘀咕,一旦真要是跟苏联开战,他们会如何表现——终于把这份一百三十五个人的名单交给了西莉亚。
收到她的便条后,他马上就回信,附上一份三十八人的名单:“这个名单并不那么耸人听闻,我觉得也没有任何你的朋友们不知道的事(注意这里提到“你的朋友们”,奥威尔不会错以为这份名单只是到她那里为止)”。
同时,估计到这些人也许不那么可靠并不是个坏念头。如果能够提早一步,像彼得·斯沫莱特这样的人,就不可能钻进重要的宣传部门对我们造成很大危害了。即便如此,我这份名单也会被认为是极大的诽谤或是诋毁或别的什么说法,所以,可否请你事后能毫无闪失地归还给我。
这封信结尾处的落款是“爱你的,乔治”。
同一天,他再一次写信给理查德·里兹:
假设拉斯基拥有一份重要的军事秘密。他会背叛我们把它送给俄国情报机构吗?我想不会,因为他确实没有打定主意要成为叛国者,而且按他向来的本性,在这种事情上他应该头脑清醒。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会毫不犹豫且毫无内疚地把情报交出去,还有那种真正的秘密党员,如普利特[那个国会议员D·N·普利特]。整个事情的困难之处在于确定每一个人的立场,以及你必须分别确认每一个人。
二
令人懊恼的是,这段时间书面纪录文字少下来了。我们知道,西莉亚可能在接下来的周日去看望奥威尔,而他为表示感谢于5月13日寄给她了一瓶白兰地。如果她又去看望过奥威尔,那么是否将打印给部门的FO 1110 / 189文件原件归还他了呢?如果他们见了面,在那次会面中他们说了些什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份名单是否也交给了其他部门?
名单提交上去后,就文件本身来说没有进一步的事件发生。外交大臣给我的信中声称所有原件已经解密,他写道,“查看了我们的纪录后,我确信这份名单是奥威尔在信息研究部的联系人被扣留下来的唯一文件。”但有相当多的信息研究部门的文件被扣留下来了,其中有部分解密的文件被删除了——根据这些文件的相关情报含量,外交部的档案人员以他们称为“空白”的手法屏蔽了原件。不管怎么说,可以确定的部分事实是,这份文件曾被归档。
对这些问题的郑重答复,需要来自像信息研究部这样的神秘部门的判断。于是我让自己沉浸于有关此事的出版文献,阅读了向公共档案馆解密的部分文档。同时我还与一些部门前工作人员进行过交谈,其中也有亚当·沃特森,指示西莉亚向奥威尔要名单的官员;还有罗伯特·康奎斯特,苏联威胁时期老资格的年表编纂者,他曾与西莉亚·柯万合用一个办公室,并且“疯狂地”爱上了她,后改名约翰·克罗克。
一幅面目不甚清晰的机构图渐渐浮现,各个部门中大部分人参加过刚刚结束的反法西斯极权主义战争,他们在加入反对英国最新战时同盟的斗争中竭力摸索着自己的方式。IRD(信息研究部——译注)是一个半秘密部门。与那些秘密情报机构,如众所周知的MI6 (军情六处——译注)不同的是,他们是政府公开承认的机构,列于外交部机构名录,但并非所有官员都被承认其正式身份。这个机构的大部分资金来自“秘密表决”,某种不必经过议会公开表决程序的扯皮,政府可以适度支配的用于机密工作的资金。外交部内部1951年对它有过一个直白的形容,“应该指出的是,这个部门的名称是为了对其工作的真实性质进行伪装,这一点必须严格遵守。”
一开始,这个“真实性质”主要是收集和摘要总结有关苏联倒行逆施的可靠信息,并向友好的记者、政治家和工会传播这些信息,以各种方式支持(包括经济上)相关出版物。这个部门是由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设立的,它尤其关注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左翼作家如伯特兰·罗素,他的三本小册子就是由IRD资助出版的。据IRD资深工作人员称,有一些作者,像罗素,完全知道出版人(背景图书公司)接触他们要他们写作的背后是由这个外交部的半秘密部门给予资金支持的,还有些作者,如哲学家布赖恩·麦基,他的《民主的革命》出版后,听说出版商的资金来源后却勃然大怒。这种模式在文化冷战时期有过著名的轶事,如CIA资助的《文汇》(Encounter)。
更多为人所知的事实是这些作者的作品已经出版了,但在IRD助力下有了更大的发行量和知名度,尤其是在国外。以奥威尔为例,他的《动物农庄》有了缅甸文、中文和阿拉伯文版本,以及相当粗糙的 《动物农庄》连环漫画版(让老麦哲挂上列宁的胡子,给拿破仑猪添上斯大林式胡子,以防头脑简单的读者不得要领),并在英联邦国家那些“落后的”区域放映(CIA资助)加以政治曲解的影片《动物农庄》。
这个部门与海外BBC也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我在一份文件中读到,IRD的官员们试图迫使当时BBC欧洲地区主管伊恩·雅各布爵士,采用对苏联的描述用语(其中一个用语是:“警察国家,另一个有用的短语强调了这个体制有时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BBC却抵制了这种压力,而外交部官员也下令IRD告诉自己的下属撤回意见。
但是,似乎IRD的有些行动没有止步于这种欧内斯特·贝文相对温和的手段。他们把上一次战争中学到的方式用于为政治事务战争行政部(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简称PWE)或军情六处工作,他们显然试图打击那些在他们看来渗透到工会、BBC以及像他们想通过查明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成员,传播有关他们活动的暗黑传言——或许还有更坏的,来打击他们视为共产主义渗透的工会,英国广播公司,或是像国家公民自由委员会这样的组织。
所以我们必须想象罗伯特·康奎斯特坐在卡尔顿府联排的某个办公室里,小心谨慎地收集和筛分着有关东欧政治的信息。另一间办公室里,一名前二战政治战争行政部成员或军情六处的人也许在准备着某种不那么谨慎的行动。隔壁的办公室里,你也许会见到一位风度迷人的教授型外交官盖伊·伯吉斯,他为IRD工作了三个月——而且,作为苏联间谍,把他所有知道的机密都告诉莫斯科的控制者们。走廊尽头,尽管只是在1952年的年初那段时间,坐着一个名叫费伊的年轻女子。小说家费伊·威尔顿后来回忆起每当有来自军情六处的人,她和她的同事就会被告知“转过身去!”于是这位詹姆斯·邦德式人物就能在无人见到的情况下穿过走廊(“先生们经过时你们要看着墙壁,亲爱的,”)。但她们常常偷眼瞥视。
冷战强化后,早期的白色(真实)宣传似乎掺杂了越来越多的灰色和黑色调子。到了1950年后期,据当时供职于英国情报机构的人说,IRD素有外交部的“肮脏把戏部门”的名声,沉溺于暗杀、假电报、把痒痒粉倒在卫生间马桶坐垫上,以及种种诸如此类冷战恶作剧……这些事情大抵不会记载在那些即使与情报相关最终也需解密的文件档案中。
所有的幸存者都坚持说,奥威尔1949年提供的任何名单基本上都不可能转给任何其他人,尤其是转到负责国内安全的军情五处和负责国外情报的军情六处。“我可以完全诚实地告诉你,”亚当·沃特森对我说,“我不记得我们曾经(对军情五处或军情六处)谈起过任何这方面的情况,”“你是否意识到X说过某某人是秘密共产党员?”但是,亚当·沃特森自己也提醒我,“老人忘性大。”显然,没人确切知道,比方说,这个部门的头儿拉尔夫·默瑞,也许会在卡尔顿府联排附近街角的酒吧,跟一个军情六处的朋友喝着白兰地,嘀咕些什么。
西莉亚·柯万总是坚定地为奥威尔对IRD所做的工作辩护。1990年,奥威尔的名单事件被炒得火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弗·希尔说,“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个两面人。”工党国会议员杰拉德·考夫曼在《晚间标准》报上写文章说“奥威尔也是个老大哥”。西莉亚则坚持认为:
我觉得乔治做得对……还有,当然,大家都认为这些人会在黎明时被枪杀,但事实上他们只有一个后果,就是不会再要他们为信息研究部撰文写稿。
现在有些作家认为IRD当时的作为相当于英国的麦卡锡式的政治迫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会迷惑于英国式的温和,你可以比较,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提示阿瑟·米勒去写作《熔炉》,而查理·卓别林则逃回了奥威尔的英国。
来看看名单上的人是怎么回事吧。彼得·斯沫莱特被奥威尔单独挑选出来,在写给西莉亚写的附信中,奥威尔特别提醒对此人应予注意。在他的名字下的“评注”中,奥威尔写道:“给人以某种苏俄间谍的强烈印象。一个非常卑劣的人。”他在维也纳出生时的名字是彼得·斯莫尔卡,二战期间,斯沫莱特是英国情报部苏联处的主管——是他激发了奥威尔关于“真理部”的灵感。我们现在知道了关于他的另外两件事。第一,根据“密德罗辛档案馆”克格勃的文件,斯沫莱特-斯莫尔卡确实是苏联间谍,他被金·非尔比招募,他的代号是“ABO”。第二,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在他的授意下,出版人乔纳森·开普以不健康的反苏文本为由拒绝了《动物农庄》的出版。那么,英国政府是如何起诉或迫害这名苏俄间谍的?居然是授予他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接下来,他担任了伦敦《泰晤士报》驻中欧记者。在他身上发生的最糟糕事情,无非是他的几篇关于战后维也纳的短篇小说引起格雷厄姆·格林的浓厚兴趣,格林为此写了《第三个人》。在那部同名电影片,格林塑造了一个有着幽灵式外表的圈内人笑料形象,名叫“斯莫尔卡”,观众还以为那是酒吧或是夜总会的名称。
工党国会议员汤姆·德里伯格——据密德罗辛的克格勃文件透露,他于1956年被招募,是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卫生间里与克格勃第二号人物搞同性恋的妥协结果,他绝对是苏联间谍(代号为LEPAGE)。但他去世时的名头是著名作家和布拉德韦尔海边的布拉德韦尔勋爵。E·H·卡尔,以撒·多伊彻,小说家纳奥米·米奇森(一个“愚蠢的同情者”),以及J·B·普利斯特利后来都有着成功的职业生涯,据我们目前所知,并无受到来自英国政府的为难。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后来还在1956年拍摄的《1984》影片中出演一个主要角色,真是够讽刺的。
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份名单而受苦受难,即便像斯沫莱特这样应该得到惩罚的人也没有获罪。当然,我们不能下结论说,那份三十八个不太知名的作家和记者后来的结局也是如此。那需要有进一步的查证。就我所发现,可以说上了“黑名单”的仅有阿拉列·雅各布一例,一个不太知名的作家,他和奥威尔上过同一所私立学校,后来对此有诸多抱怨。据一份英国政治调查研究,阿拉列·雅各布于1948年8月在卡佛沙姆参加了BBC监听工作,却于1951年2月“突然没有了编制权,那就意味着他不能拿到养老金了。”他向自己的表亲伊恩·雅各布(他在处理IRD的事务,后来成为BBC总干事)抱怨此事。在他妻子艾丽斯·莫莉(她也在奥威尔的名单上)1953年去世后不久,阿拉列拿到了发还的养老金。
冷战时期的英国,BBC与IRD这样的半秘密组织的合作,在与情报机构秘密审核员们的合作也有过一个相当晦暗不明的阶段。但BBC两年“编制权”的失去几乎就是一段“正午的黑暗”(《正午的黑暗》是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柯斯勒描写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期的著名小说,国内有董乐山译本——译注)和101房间(《1984》中最恐怖的地方——译注)的现实版。可是,无论如何都没有证据表明奥威尔的名单对阿拉列延迟了两年的编制权问题发生过影响。
三
“圣徒总要被判定有罪,直到他们被证清白。”奥威尔在给甘地的信中这样写道。此事距他给西莉亚那份名单刚刚过去两三个月。奥威尔的原则现在必须反证于奥威尔自身——英国政治写作的圣徒乔治。但即便所有可能的档案都获解密,谨慎精细的历史学家梳理过IRD,BBC和所有其他部门可能的证据,他的“清白”最终也无法得到证明。也许奥威尔其实并不想为自己的“清白”证明什么,只是对“被控有罪”恼火,因为所有的一切取决于控告。
如果指控奥威尔是一个冷静的武士,答案是肯定的。奥威尔是一个冷静的武士,即使在冷战开始前,许多人还在庆祝我们英雄的同盟国苏联的胜利时,他就在《动物农庄》中警告苏联的危险。他是《牛津英语词典》中首先提出“冷战”这个词汇的作家。他在西班牙以自己手中的枪与法西斯主义开战时,子弹射穿了他的喉咙。他以自己的写作与极权主义作战时,这项工作加速了他的死亡。
如果指控他是秘密警察的线人,答案是否定的。IRD是一个奇怪的冷战机构,但它绝对不是“思想警察”。奥威尔与鬼才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不同,他从不相信以结果证明手段是否正义。我们一再发现,他坚持对理查德·里兹说,必须区别对待每一个案件。他反对在英国禁止共产党。他担任副主席的捍卫自由民主委员会认为,公务员的政治审查是必要之恶,但坚持认为相关人员应当有工会的代表,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并允许被告交叉审查对他不利的证据。这里面几乎没有冷战时期克格勃——或者军情五处,FBI所用的方式。他告诉西莉亚他赞同IRD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他们的手段。
这份名单让我们又一次反思我们对于苏、德不对称的态度。奥威尔喜欢制作名单。在1942年给 《党派评论》“伦敦信札”专栏中写道:“我认为我至少可以起草一份可能会转向(在德军可能攻占英国时投向纳粹)的人的初步名单”。假设他是写下了这份名单。假设他那份纳粹秘密党员的名单送交给政治战争执行委员会了。会有人反对吗?
时隔已久的这份IRD名单的披露,使这种至关重要的区别显得分外醒目:在奥威尔的私人笔记本与他交给外交部的西莉亚名单之间的差别,经常是含混不清的。据调查,读者一般会对他笔记本上记载的条目更感震惊,更感到不可思议。里面记下了几个老帝国警察,几个间谍,还有大量的漫画,粗鲁的黑色幽默(他笔记本的名单里还包括某些税务部门的人:那些所得税审查员们)。但是所有的作家都是间谍。他们瞥视,就像卡尔顿府联排里的费伊·威尔顿那样。他们秘密地记在笔记本里。笔记本里让当代敏感的读者深感震惊的是给人贴的种族主义标签,尤其是八个什么“犹太佬?”(查理·卓别林),“波兰犹太人,”“英国犹太人”,以及“犹太女”。奥威尔终其一生都在力图克服阶级和时代的偏见,此处表现为他最终也未能克服这种偏见。
现存最大的令人不快的问题是他确实递交了那份名单,而他的名字几乎就是政治独立与诚实的新闻报道的近义词,现在被拖进了与官僚宣传部门合作的丑闻里,但这只是边缘性的合作,出于良好的“净化”宣传部的理由。在IRD文档中,你可以看到类似官牍文本式的,我们现在习惯称之为“奥威尔式”或“卡夫卡式”的语言。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奥威尔手写书信(“亲爱的西莉亚……爱你的乔治”)在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变成了FO 1110 / 189打印文件:以“尊敬的某部”开头,结尾落款却是超现实的“你永远的,档案室”。
但我们也许不必太惊奇,因为奥威尔是从内部了解这类世界的,并把它们写进了那本《1984》,在书中,他对纳粹法西斯(即国家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两者结合可能性——Ingsoc(《1984》中称为“英社”)的警告——其中大部分真实的细节来自他在战时伦敦供职于BBC的经历,那是相当英式官僚的机构,与英国新闻部保持着密切联系,是101房间的原型。
奥威尔和西莉亚的关系,是所有对他的诠释中最敏感也最能引起人们猜测的部分。在他写给西莉亚的信中,有一种几乎是痛苦的激情。你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位非常漂亮、富有同情心的、很有教养的女士的强烈感情。但我们都知道他这段时间的情况,你还可以感受到某种更宽泛的情感:一般来说,这是一个罹患致命疾病的男人相当绝望的渴求,他渴求女性充满爱心的支持。有人回忆起他三年前曾有过的感情起伏,当时他曾急躁地向西莉亚之外的两三个年轻女性求过婚。孤独地躺在科茨沃尔德疗养院病床上,憎恨自己四十五岁年纪就要真的完蛋的事实,很难说他是否有过这样的念头,渴望以爱一个美丽女子来与渐行渐近的死亡抗争?
西莉亚这一方始终维持着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身份,不鼓励乔治任何生硬的冒进。在名单交上去后不久,另外一个年轻美貌的英国女子登场了,他之前在感情波动中也曾向她求过婚,和西莉亚一样,她也从巴黎回来,到疗养院来看望他。索妮亚·布隆奈尔刚刚结束与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的一段罗曼史,也许是受到了些许鼓励,奥威尔再次向她求婚。在他出版人弗莱德里克·沃伯格的强有力的怂恿下,索妮亚接受了求婚。
在《1984》中,温斯顿·史密斯对极权官僚的反抗就是和朱莉亚做爱——这个人物有一部分是以索妮亚为模特的。真实生活中,是否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对西莉亚充满爱的关切导致“奥威尔先生”进入了英国官僚体系的秘密文档?
这种个人传记式的推测,并非要将他把名单交给外交部某个部门这一自觉的政治选择琐碎化。但你不得不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假设1948年3月29日去拜访他的是那个戴顶圆礼帽穿着条纹外套的克罗克先生,他会把名单交给他吗?可是,那天去看他的并不是克罗克先生,而是他“最亲爱的西莉亚”。
奥威尔与自己最后的敌人——死亡做孤注一掷的斗争,但正是他的早亡保全了他的名节。很难让人不去猜测,根据他编制的那份名单,如果他活下去的话,他会以何种方式行动?——在《新政治家》杂志发出反偶像的左翼声音?在《文汇》表现一个脾气暴躁乖戾的冷静的老武士形象?——这是完全不合规则的。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会有明确而强烈的政治立场,因而疏离那些左派或是右派,或许两者都不选边。他可能会写下更多的书——也许吧,以他之前的小说和最后的草稿故事来看,可能比不上《动物农庄》和《1984》。最终,死亡让他成了冷战时期的詹姆斯·狄恩,成了英语文学中的J·F·肯尼迪。
在柏林墙耸立之时,在越战问题上,在1968年学生运动发起之时,我们大家将会多么高兴读到他的文字,我会多么高兴在中欧见到那年如果活着的话将是八十六岁高龄的他。今天我们还能听到他的声音真是太棒了——这声音在我们的想象中更显生动——对伊拉克战争宣传语言,对缅甸持续的悲惨境地,或是托尼·布莱尔的困境的评论。但那位已一百岁的奥威尔会透过他笔记本上的星号和叉号向我们咆哮,“别傻了。你得自己去解决问题。”
❶Orwell’s List,作者Timothy Garton Ash,原刊2003年9月25日《纽约书评》。
❷2003年6月21日《卫报评论》重印了全部名单。
❸具体而细微却不乏偏见的叙述来自保罗·拉什莫和詹姆斯·奥立佛的《英国的秘密宣传战,1948-1977》。休·威尔福德的《CIA、英国左翼和冷战:谁说了算?》对此有更简短但更微妙的叙述。还可参考W·斯考特·卢卡斯和C·J·莫里斯发表于《英国情报、战略与冷战》(由理查德·J·阿尔德里奇编辑)的文章《这正是英国的十字军东征:信息研究部门和冷战的开始》;菲利普·迪尔力发表在《劳工历史》第77页(1977年11月出版)的文章《面对共产主义:乔治·奥威尔与信息研究部的冷战攻势》;IRD:外交部信息研究部的建立与肇始,1946-48;CIA与文化冷战(《格兰塔》1999)。
❹1951年3月21日FO 1110 / 383。
❺见FO 1110 / 191。
❻马克·霍林斯沃斯和理查德·诺顿-泰勒,《黑名单:政治调查的内部故事》(贺加斯出版社,1988)。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