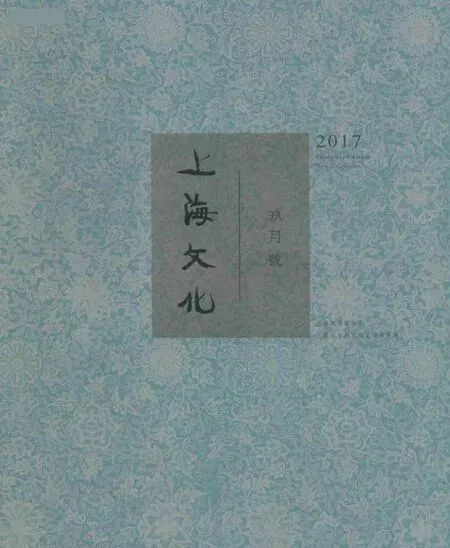“大师兄”王富仁
黄子平
“大师兄”王富仁
黄子平
因为是浩劫之后第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博士”,所以呀,广义地说,您是我们所有这些1980年代入这个行当的人的“大师兄”了。当面给他戴“纸糊高冠”,王富仁兄却不为所动,笑咪咪地吸烟,静静地瞅着这帮广义的“小师弟”有一搭没一搭鬼扯。忽然扯到他觉得有意思的话题了,好吧,一开口,一支接一支不抽完半包烟他停不下来。
有一种“正经八百”的学术研讨会,规定每人发言二十分钟,还剩三分钟打铃一次,还剩一分钟打铃两次。可想而知参加这种会富仁兄有多受罪,不许吸烟不说,刚开了个头,叮叮,打铃两次!有一回在港大开鲁迅研讨会,讲评的香港教授拿到富仁兄的论文,主旨深刻视野宏阔观点明晰逻辑严密,挑不出毛病,不知怎么讲评,只好从细节入手,说引鲁迅没注明出处。听会的学生们都笑说,鲁迅的全集都在王老师肚子里了,随手拈来注什么出处嘛。
1980年代初,我在《文学评论》上读到富仁兄博士论文的绪论,大为震撼。就好像在“正统鲁学”的铁屋子里,有个傻子搬了块砖头,咣咣地砸了个透亮的窗户。我们一伙“广义的师弟”都觉得,这篇论文宣示了几十年岿然不动的“正统鲁学”的终结。当然“镜子说”仍不脱反映论的思维窠臼,然而从“政治革命”转到“思想革命”,这就非同小可。他把《呐喊》、《彷徨》二十几篇小说,重构成一个“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系统,从立意到艺术,解析得那叫一个通透!——无懈可击。
后来“鲁学”又成为显学了,言说鲁迅的文章我就不太爱读。批鲁反鲁也好,捍鲁卫鲁也好,大都写得沉闷而无聊。富仁兄的长文也让人吃不消,但读到那些回忆他少时读鲁的文字,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是贴着生命的有温度的回忆。富仁兄说,在那谎言充斥的年代,唯有鲁迅的书是对我说真话的书,唯有鲁迅是跟我说真话的人。但少时读鲁也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富仁兄说,明明昨天你还是三好学生、学生干部、优秀少先队员,忽然你就看周围什么都不顺眼了,周围看你也什么都不顺眼了。用古人的话说,忽然你就有点“不可”一世,如是一世也就“不可”你。中了“摩罗诗力”的蛊,会活得很辛苦。凭着这一代人少时读鲁的经验教训,我对老钱钱理群去给中学生讲鲁迅,就颇有点腹诽——绝对误人子弟!高中毕业班的老师给学生们的忠告是对的:你的目标是考入北大去听钱老师讲鲁迅,而不是听了钱老师讲鲁迅去考北大。你这时候听得开心,然后别说考大学了,做人都很艰难。于是爆满的钱氏中学生鲁迅讲座,忽然冷冷清清,学生们真乖:这是好的。要知道,鲁迅的书有毒,说真话会害人。这一点鲁迅自己也说过很多次了,唯有“以说谎和遗忘为前导”,你方能依稀看见那条灰白的路从暗夜蜿蜒而来。
富仁兄对鲁迅作品的解读,那种细致绵密的条分缕析,我总是叹为观止。譬如他解说《故乡》的“悠长”,悠长的忧郁,以及忧郁之美。富仁兄说,直到结尾,这种忧郁的情绪仍然没有全部抒发罄尽。故乡的前途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个需要人自己去争取的未来。它把对故乡的关心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把对故乡现实的痛苦感受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人们没有在结尾时找到自己心灵的安慰,它继续在人们的心灵感受中延长着、延长着,它给人的感觉是悠长而又悠长的,是一种没有尽头的忧郁情绪,一种没有端点的历史的期望”。在“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心里,这无尽的乡愁一如悲凉之雾,笼罩四荒。
然而,对富仁兄那些大框架、大论述,譬如大气磅礴的“新国学”论纲,我就有点望而生畏。在这一点上,倒是老钱钱理群对他有“同情的理解”,说,富仁兄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将国学(民族学术)内部,长期被视为势不两立的各个派別,例如:古代文化(“旧文化”)与现当代文化(“新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学院文化与社会文化、革命文化,联系为一个更大的统一体,建立自我和自我对立面共享的价值与意义,构造一个有机融合、相互沟通互助的“学术共同体”,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同存共栖”的精神归宿。——好吧,这两位大师兄都有这种爱用大词、大概念的雄心/毛病,对我这已经习惯于碎片化思维的人来说,只能敬而远之。我总觉得,“国学”无论新旧,一旦姓了“国”,就难免有垄断,有霸权,有科层等级的区分和压榨,所谓“共同体”无非是一种乌托邦空想而已。可是转头一想,你又会为这两位兄长的拳拳之心、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感动不已,并开始反省自己的犬儒和迟暮疲懒的心态。
五年前我到老家的嘉应学院访问,讲点“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之类的专题。富仁兄说,路很近啦,还不顺便到汕头大学来讲一次。嘉应学院跟汕大有密切的战略合作,派车送,这就第二次到了汕大。记得上一次是来开一个很大的学术研讨会,叫“全球化视野中的现代文学研究”什么的,题目唬人,参加人数也吓人,主持者富仁兄忙得脚不沾地,根本说不上话。这回从从容容,讲完了课吃潮州菜,傍晚到水库大坝散步乘凉。那时他的身体状态已经不太好了,却还很自豪地宣布:我戒了——戒酒不戒烟!那年香港的岭南大学有一个会,讨论老钱的新书巨著,想请富仁兄作为“同时代人”去参加发言。我说起香港的校园全面禁烟,而香港海关免税烟是十九支(也就是说,一盒烟你得在关外吸完一支才能过关,否则整盒收税)。富仁兄大惊失色,一脸坚毅地说:这样子啊,那我就不去了。我本想以香港的苛政为契机令他戒烟,没想到反效果是失去了在岭南大学与他再聚的机会。
第二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富仁兄叫车带我去澄海塔山参观一个博物馆。偌大的馆(分布在几个小山头),孤零零只有我们两人绕山而行。“碑廊铭史”,“石笔书史”,经了“焚书坑儒”的年代,创办者想用坚硬的介质来抵抗历史虚无主义,他们没想到“焚坑事业”及其手段,其实一直在进化之中。参观这样的博物馆,令人心情如同那些石块一般沉重。下山的时候烈日当空,富仁兄沙哑着嗓音说,只怕这样的博物馆,也办不了多久了……
那就是我和富仁兄最后的一次相聚。我心忧伤,如此悠长。
编辑/木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