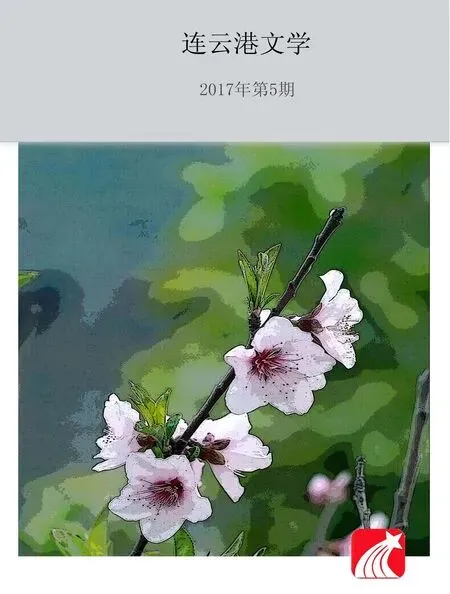竹马
汤景扬
竹马
汤景扬
儿时,总觉得生命很长很长,仿佛总有歌不完的曲子,走不完的路,撒不完的娇,遇不完的人……
可是,当我们这代人,渐渐成长起来,回首看去,人生路已经走掉了三分之一。如果是一块圆形大饼,那么我们已经囫囵吞完了近一半。时间太可怕,总是在没有来得及记忆,就留给我们苍茫的空白。
早先时候,我曾经去自己小时候成长的地方看过,那里还留着没有被推倒的断垣在苟延残喘,仿佛眯着眼睛在看着我,那种眼神就像当年我养过的一只老猫,临死的时候将对世间所有的哀怨情愁都照了一遍,让人终不忍触目。
日子往前费力推移,在二〇〇二年的时候,我升上了我们县这里最好的一所高中。我是那个最普通的学生,当我听说我升上了第一高中后,高兴得好几个夜里睡不着觉。那时,作为一名十五岁的少女,尤其又是读过很多三毛,张爱玲写的小说的青春期少女,对朦胧的青涩之爱,是充满了期待和幻想的。
那天,仿佛就是发生在昨日的一场电影剧情中,我在开学那一天,四下踮脚张望,在人来人往的同学当中,最希望遇到左源。
左源是我人生当中最开始记住的一个人名,他也是我今生唯一可以称之为竹马的男孩。
在我们的童年里,如果没有天空,没有蓝天,白云,没有五颜六色的玩具,和脏兮兮的手,通红的脸蛋,一定是不美好的。
然而,等了一天又一天,找过每间教室。高一足足有二十四个班级啊,找遍了整栋楼,我都没有找到想要看见的那个人。少女时代,在多少个午夜梦回处,我只能反复追思我的童年。
我三岁,因父母亲工作的缘故,我来到了一个叫作大圈的地方。大圈,大圈,圆又圆,圆住了我的一生,圆住了我绮丽梦想的开端。
那是一处栽满了松树,柏树,月季,郁金香,菊花的政府大院。
进大门之后,入眼的是棵硕大的,宛如亭子一般的大松树,绕松树一周,西拐脚是一个漂亮的拱门,走过拱门,偶尔会留意到拱门上的白石灰好多都脱落了。把目光移向右手边,即可看到一排平房,平房的前面是一根根朱红色的柱子,借由它们搭建出了宽约两米的走廊。走廊的前面是隽秀的花圃,围绕一周的是被修剪得很整齐的冬青,里面栽种着五彩缤纷的花朵,印象最深刻的是各色郁金香和绽放很大气的月季,翩翩佳人一般,摇曳身姿。穿过走廊,再往左拐,就会再次经过一道圆形的拱门,推开锈迹斑斑,却被磨得很亮的铁门,放眼看去,左手边一大片宽阔的土地,被住在这里的人们打点得井井有条,一块一块小洼地,各家种上了各种蔬菜。譬如春天的时候,是青绿色的小青菜;夏天的时候是长豆角、小占瓜,番茄;秋天的时候就更多了,以收获萝卜的数量居多。临近冬天,往往会在水泥路上铺上一层塑料大口袋,上面散落着被精心切成条形的萝卜。用以晒成干,然后可以装进坛子里,码上盐巴,耐心等待一段日子,就会变成可口的咸菜萝卜干。我在冬天的时候,小脸总容易冻伤,父亲就会去被大雪覆盖着的屋前田地里,捯饬一盆干净的雪回来,给我擦脸。擦得我嗷嗷叫唤,喊着疼。
在拱门的右手边,是一排刷得雪白的房子。往前经过的第一家是左源家,我家是第三户。
房子是典型的苏北民居布局,前屋是前后开的门,前门作为正门,屋子用做烧饭的,搁置八仙桌。后门就用来通偌大的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缸里的水通常是很满的,水面上漂着半只葫芦瓢。院子不是水泥的,而是泥土,只有围着墙角处,才有几大块水泥板,下雨的时候,用以防止鞋子被黄泥水陷住。踩踏过院子里的水泥板铺成的小路,就看到后屋了。后屋用作起居室,映入眼前的是两扇并排开着的木门。门被刷成了浅粉绿,也许是深绿色,经不住太阳光的摧残,晒得掉色了。门上挂着沉重的栓子,栓子的中间有个长条状的孔,正好吻合门框处的锁。锁平日里是挂在那里,人一走动,推开门,锁和栓就相撞下,咣当咣当作响。
我出入都是在西边那道门。家里的家具是那会做木匠的舅舅打制的。所有的家具都刷成了灿黄色。有一个写字台,中间带抽屉,两边带小箱柜。父母亲爱锁起来,使我总觉得里面装着好多宝贝。还有一面大衣柜,中间贴放了好大的一面长镜子,我母亲爱打扮,每次出门都会裙裾飞扬,在镜子面前好好照一番。我也学着臭美,依样画葫芦,偷戴母亲最美的那条大红色丝巾,想象长大后的模样。
当时,父母亲咬咬牙,购置了一台熊猫牌彩电。一台电视花费了1700多元,差不多他们大半年的工资收入。大舅就又给我们家打制了一米高的电视橱,电视橱的最底下是可以平掀开的储物格,里面塞满了父亲工作用的各种杂乱的文件,材料,夹杂很多牛皮纸袋。牛皮纸袋中间有个小圆片,打开的时候,必须顺着方向,绕出一条麻绳。我最喜欢拿牛皮纸袋玩,里面有好多盖着红章的文件。父亲找不到的时候,就会火急火燎的到处翻,然后我躲在一边,捂着嘴乐。最后就会发现父亲翻出了好多书出来,一时好奇,总忍不住翻一翻。其实,当时并不识得多少文字。
储物格的上面是我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推动的玻璃小门。我老是怕我的小手会被玻璃片给伤着。玻璃格的旁边又竖立着是可以锁上的两道门。母亲最爱把父亲和她的包,锁在里面。当然,偶尔也会有厚实的藏青色棉帽子,帽子上有红金色的徽章,我爱扣,却总是扣不掉。现在回忆起来,估计是父亲当初在张店镇做工商所所长时候的工作制服。
我记忆力算不得多好,但是总有那么几件印象很深刻的事。
譬如,在好多个午后,阳光刺目,明晃晃爬在大地上的时候,左源总是会在我的窗前探出一张笑脸,晶亮的眼睛带着狡黠。他先是轻轻敲一下前屋的玻璃,我竖着耳朵,捕捉听到的动静,待母亲不在意的时候,便悄悄从门缝里扣下了破旧的门锁,确保声音很小。通常,我的母亲不是正在专心烧饭,就是在打盹。而我则是关也关不住的那只小麻雀,总是想尽办法,翘出尾巴,尽情在天地间追逐打闹。
我们顺利会师之后,便躲在那棵很大很大的松树底下,因为个头小小的缘故,我清晰记得我可以微微弯下腰,在松树硕大的树丫处钻来钻去。我藏了好多宝贝,例如有我最宠爱的金色头发的洋娃娃,有带四个轮子的小电话机,有可以办家家酒用的好多餐具,特别是餐具,这些叮叮当当的宝贝们,看似破烂一般,却都是我好不容易在平日里收集来的,有的来自于花园的某一片叶子底下,有的来自于母亲遗弃的角落里。
左源他也有他的宝贝,那是一个底部烧得很黑的瓷杯。完整的,盛水后也不会漏下来。每次扮演家家酒的角色时候,他就会把瓷杯装来小米粒,然后倒上水。这个时候,有些大孩子也会凑过来,他们带来火柴,我们一起合力,码了个简易的,却像模像样的灶台。我要做些什么呢?看着怀里张着蓝色大眼睛的洋娃娃,我这个扮演“妈妈”的小女孩,可着急了,今天一定要加点好吃的菜呀!
于是,我便一边拖着我的彩色电话机,一边满院子里去寻找可以“食用”的食材。春秋天的季节里,还真是每次都可以满载而归呢!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转到一个圆形的小拱门里,忽然发现,眼前都是比我人还要高的黄花菜。密密匝匝挤在一起,仿佛里面藏有会吃人的怪兽,风从耳朵拂过,金黄色的花们,又美艳,又诱惑,使得小小的我,鼓起勇气,为了今天的“好吃”的,也为了能够在男孩子们面前炫耀一次,我握紧小手,冲进了黄花菜地里,慌慌张张摘了几朵就跑。
边跑边回头,两只冲天的小辫子,在阳光里,就像快乐的小燕子,随着小丫头的脚步,一起一伏。
左源他们的脸和手已经都黑了,脏乎乎的,好像小叫花子。他们见我回来,竟然表现得无比惊喜。一个高个子的大男孩,他捏下正在灶上被烧的乌漆麻黑的瓷杯,灶里的杂草已变成了碳屑,娓娓逸逸冒着青色的烟。小瓷杯被他扔掉了滚烫的盖子,他把瓷杯拿到我的面前,示意我闻一闻。
可我还没有凑过去,就被左源给推过去了,
"不要闻!"
然后,我才发现他们笑得特别得意,那种得意的笑容,让人却一点恨不起来。左源告诉我,他们几个男孩子无聊,把尿当成了水,煮在了米里……
左源和我都很喜欢扮演家家酒,他是“爸爸”,我是“妈妈”,怀里的娃娃是孩子。
我很难记得清一个人的长相。
左源的童年影像,却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并不明白,那时候的小伙伴不止他一人,可我为什么单单只记住了他呢?
至今是个难解的谜。
长大以后,得知他在海边工作,做一名英语口语翻译。整日里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客商们交流。我羡慕他的一口流利的英语。
那天,我特意放下长卷发,穿一件修身的,灰色,但是袖口是荷花样式的设计,胸前是一朵暗紫色大花的衬衣。我以为自己很妖娆靓丽,会很得男孩的喜欢。于是,自信的我便带了我一个女朋友去见他。女朋友长相普通,也没太招眼的气质,唯一吸引人的,就是那双大眼睛,落在了齐刘海的下面,扑闪着,很显嫩。
那次见面,离我们上次见面,隔了八年。
八年里,我们分别从少年,少女成长起来,各自变成了今日假装谦让有礼的世俗模样。当时,下着好大的雨,我在公交车站等他,一双腿裸露在外面,虽是夏天,雨水淋得久了,也觉得丝丝寒意。大概等了二十分钟,他终于开着他刚买的那辆黑色尼桑从前方护栏处绕过来了。我赶紧打开前车门,很自然坐进了副驾驶座。差点都忘了我身边同来的女朋友。
他偏过头来冲我笑,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浓密的卷睫毛,一张娃娃脸,仿佛时光的馈赠,使他竟然和八年前我见过的模样,丝毫未改。我心下微惊。
我要找回竹马,还是为了少女时代的青涩之梦?
左源,他还是那个记忆中很漂亮的男孩子。
在我们成长之后的岁月里,经历了些许风霜,他却依然形同男孩子,宛如稚嫩少年。
而我,却如牡丹绽放,发育极好,随时逸出沁香,周身萦绕淡淡女人味道。
——当初的童年仓皇结束时,那一地烧黑的痕迹,还时不时叹息着,叹息我们的单纯远离。
五岁,我们上学了。我每天都背着小书包,搭乘父亲的凤凰牌单杠自行车。
那个年代里,我们是骄傲的一群孩子。
我父亲是大圈的副乡长,母亲是当地学校的小学教师。而我,则是野性子的臭丫头,天不怕地不怕,世界里只有任性二字。
而左源,仿佛突然变成了谦谦少年。他待人接物,总是显得比我更加有礼一些。衣服也总是那么光鲜整洁。家里的桌上总是有那么一两盘是我咽着口水想吃的菜,也有些时候,是漂亮诱人的苹果。
而我则是因为小不点的弟弟刚刚出生不久的缘故,总是随便被强制性地套一件裙子就出门了。头发也随意散乱在鬓角,后来母亲嫌每天给我扎辫子,太费工夫事了,便给我咔嚓剪成了短发。
我很羡慕左源,他的爸爸妈妈对他总是温言软语,奶奶对他又是宠爱有加。而我,自从有了弟弟之后,便像是园中的一株小树,只有在有太阳的日子里,才能绽放出美丽却略显倔强孤单的绿色嫩芽。上学后,每天回家,总是被规定了时间,否则晚了一会,就一定要被严厉的母亲棍棒招呼的。我心里总是想着找左源玩耍,和他分享今天在学校里的事情。有一次,我捡到了一枚非常漂亮的水晶葫芦,很小却很精致,我想啊想啊,觉得好东西自己留着多没有意思啊,那我就送给左源吧,这样,我们在未来分开的时候,他一定还会记得有我这个小伙伴的!
于是,我每天都故意磨磨蹭蹭在路上走着,背着沉重的书包,默背着“a o e”,却依然等不来他。小小的手心里,因为攥着水晶葫芦的原因,总是沁着汗渍。
水晶葫芦到如今都没有送出去过。还在我母亲家的抽屉里收藏着,现在偶尔会翻出来,就想到了当时小小的一个丫头,简单透明,又焦急等待的心思。那是我第一次想着要去分享,并充分体会到了给人分享自己喜爱东西时候,那种雀跃期待的美好心情。
八岁那年,面临第一次离别。
左源和我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缘故,即将分别转去县里不同的小学。
临走前的那个夜晚。他又来我家找我出来玩。他领我来到大院里的那棵站在花园里的硕大松树处,扶我爬上了水泥花园台阶上。然后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他突然掉过头问我,
“你要去哪个学校念书了?”
“西安吧!”
“我去实验一小。西安?那不是很远很远吗?”
“咦?西安很远吗?我是听爸爸妈妈说,这所学校在县城里啊!”
“你确定是西安吗?我怎么只听说过新安小学?”
“新安……”八岁的我,就显露了遮盖不了的傻气。
那天,即将告别童年的我,还不知道我将永远见不到这所记忆最深处的大院,也将永远不能回来。仰头看了看那日的夜空,我发现月色如水,月亮很皎洁,雪白雪白,我也再没有在今生见过如那日的月光。
左源是先我一天搬家的。我贪睡,等我醒来的时候,他家已经人走房空。仅仅八岁的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伤感,我在他家空落落又无比杂乱的每个角落里,轻轻走过,努力想要记住些什么,却无从记起。
也许,是他曾经送给我,他亲手叠的一只白色千纸鹤;也许,是他曾经说要给我带漂亮的溜溜球;也许,是他的奶奶夹给我吃,和左源吃的一样的那块红烧肉;也许,我只是想要记住我的童年快乐。
我们家也终于搬走了,离开了大圈。生活了五年的大圈。承载了我最美好童年的大圈。
我果然入学在了新安小学。当时作为插班生,读三年级。我学会了写作文。渐渐发现自己的词语量增加了,我母亲又有意识锻炼我的文字。当时,我就觉察出我对这个世界的通感很强烈,比别的同年龄孩子更有情感的领悟力。所以,九岁那年,我竟然自己学会写信。洋洋洒洒用写作文的格子纸,写了三百来个字的信。人生的第一个收信人,就是左源。
信的内容忘记了,我用两只非常好看的蝴蝶结发夹,夹住了信的两端,藏在了我的枕头底下。
藏了多久,也忘了。约莫有半年吧,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寄信,只是觉得信纸用两只蝴蝶结夹着,显得自己很有爱心,很萌。所以一直到我母亲无意中掀开床席子,发现了信。她打开信之后,读了读,笑得一脸温柔。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柔的时刻,我母亲竟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严厉得苛责我,因为我没有按照大人的指示,第一次单独做想做的事。而是仅仅把信又折了起来,收进了那个有锁的抽屉里。
也是那次之后,我母亲就开始叫我写日记。
我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也一直坚持到现在。
现在我也有自己的家庭,偶尔和丈夫说起童年的故事,讲到左源,讲到他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无数次地偷看我。我年轻的丈夫,笑得比谁都欢,他一口咬定:“必然是你暗恋着你的竹马,其实你的竹马并不喜欢你。”
我气鼓鼓地回应他:“你是吃醋了!他一定喜欢过我。”
“如果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还用得着你暗恋他到高中吗?早就会想尽办法对你表白了,好吗?”
我怔住。原来,不管是男孩还是男人,喜欢一个人,还用得着女孩挖空心思去想要见他吗?
那年夏天,我们长大的那年夏天,我带我的女伴去见他,在大海边。我们在一起吃了个便饭,聊得很愉快,我扮演好一个旧时好友的角色,和他相谈甚欢。席间,他不时询问我女伴的信息。直至后来,两个人加了微信。
那天晚上,我笑得深藏不露,在女伴面前表现得很不在意,却听了一晚上他们之间的信息提醒的声音,声声刺耳。
女朋友惊喜地对我说:“左源说对我很有好感。”
“很好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相处看看。”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胸口闷滞,却要生生吞咽下,还要笑得很无害。
“真的吗?”
“嗯,是的,左源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如果你们在一起了,我会很替你高兴的。”
他们两个人,也就是那次,经过我的因缘,谈恋爱了。而我铩羽而归,也许,真的只是童年时代,一段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罢了。
我想起当我高三那年,听说他转学到我们的班级,我欣喜若狂,觉得记忆中那个好久不见的男孩,重新相遇,这是多么值得高兴地事。我又像当年得知他小升初的时候,转来我们班级那样,盼来了他。转学来的第二天,我从教室叫他出来,送了他一张亲手绘制的书签,他只是淡淡地收下,却让少女心的我,百转千回。如果不是因为学绘画,我一夜之间从那个班级离开,也许,我还会窃喜,变成我不停去在上课的时候偷看他。可是世事难料。所有的故事都不会那么轻易给你个了断。
直到今天,我才豁然明白,所有关于左源的记忆,不过是独角戏。
那棵硕大的松树,那座栽满鲜花的院子,那片被大雪覆盖住便如同仙境般的田地,那条人来人往的道路,那只带四个轮子的电话机,那个洋娃娃,那办家家酒的游戏,那个装满尿的茶杯,那个金黄色的旅游帽子,那个男孩的笑容,不过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青梅爱上了郎很多年,郎却骑着竹马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