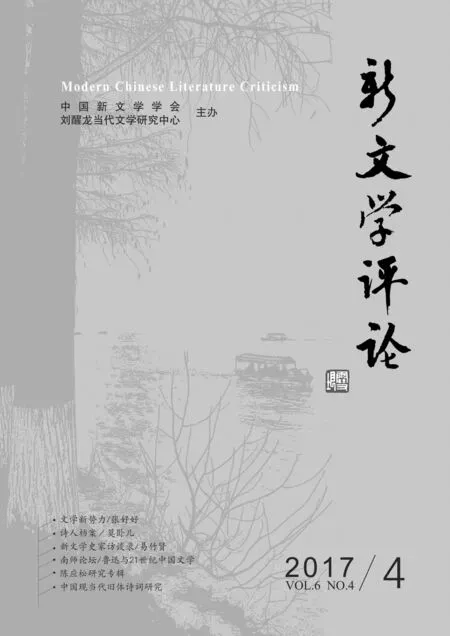风格、索德格朗及其他
◆ 莫卧儿
与一位画家聊天,这位画家也写诗,国内外得过不少奖项。谈及诗和画,他说他的画比他的诗好。我说何以见得呢。他说把诗作者名字省去,一定有人不认得是他的诗了;但把画的署名省去,几乎没人不知道那是他的画。意即他的画已经形成个人独有的风格了。
又有一次,几个人大冬天在餐馆涮过羊肉之后,觉得有些油腻,就钻到最近的一个人家里喝茶。那人是置了套茶道行头的。铁观音上来,捧着精致的瓷杯,雅物清心清肺,话匣子就在袅袅热气中打开来。
聊至风格,我顺便提及了和画家的对话,那个进门没急着吃茶穿着鞋爬上床找书看的不同意了。身子还在床上,直着脖子就朝我们这边大声道:不对不对,不探索不调整也就罢了,难道身心状态也永远一样?心下思忖:倘有一人二十岁即成风格,长此以往,三十,四十,五十……的确,是件可怕的事。
多扯了几句淡闲龙门阵,说回诗歌。记得那年早春的北京,“是消弭不去的残雪还在演奏安魂曲/冰面上尖脆的裂响——”“是柳枝深紫的芽苞哭喊着回来/声音被茫茫黑夜吞进胸腔” 那一分一秒失去的永不重生,而“亲爱的,我们都是活着的死者/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一切即将逝去,一切又即将开启的凛冽寒冷中,诗情恣意疯长。
一个朋友看到我的诗,笃定道:你看过索德格朗。我说从没看过,他不信,审视后又道:我十几岁时就看过了。丢不起这个脸,赶紧上当当网搜寻索氏芳踪。
《索德格朗全集》放在案头。读之,惊。比较读之,更惊。“而我站在黑暗中/听,一颗星星落地作响!”(索德格朗诗),“每个夜晚,都有流星欢笑着扑向死亡/冷冽的声响在空气中久久回荡”(我的诗);“我曾爱过一个男人/他什么也不知道”(索德格朗诗),“亲爱的,这多像我们的爱/撕心裂肺,却互不关联”(我的诗);“我必须在这里等待那给我的灵魂/带来自由的温和的死神”(索德格朗诗),“哦,不要停歇——/在春夜想到死亡的人是多么幸福!”(我的诗)……
曾经收到一条短信:冬天,在温暖中研究古典文本,在浪漫主义和现代派间寻找和解,获得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力量——绝望的力量或绝望的活力。发信人很熟,我回:“像你做的事。”对方道:“不是我,是罗兰·巴特说的,我深有同感。”此人不写诗。我想起,他是罗兰·巴特的拥趸。
静下心来,也没那么奇怪了。这种事岂止我一人碰上,同为艺术领域,气度作风相近相悦也属正常,哪来那么多罗兰、索德格朗?
说回索氏,一位身心病态、想象瑰丽的少女诗人。英年早逝,短短的一生仅三十一年。其实谁能确定三十一岁之后她诗风依旧?策兰的早期和晚期作品,差别也大了去:“一个灯一般的闪亮/在我心中,正好在那里/一个最痛苦的在说,永不”被多次解读,到了“而我谈论的多余/堆积出小小的/水晶,在你沉默的服饰里”,其创作的封闭特征立即令众人三缄其口了。
艺术终究是需要探索需要往前走的。画家们说:画到生时方是熟。而诗歌也永远是一项介于“熟”与“生”之间的探险。赞成先锋性的同时,我相信一点:不论如何多变,一个精神强大者,他(她)的精神线索是始终明晰的。也许一首诗只是偶然中注定的邂逅,若要这一生永远处在同一状态实属天方夜谭。
惊闻闺蜜与男友爆发争执,当时的场景——
他的手停留在她的第三颗纽扣上。
她用眼睛问:你爱我吗?永远?
他看懂了:亲爱的,我现在肯定是爱你的,但永远太可怕了。我能保证的是现在,你能把握的也是现在……
她问我:分不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