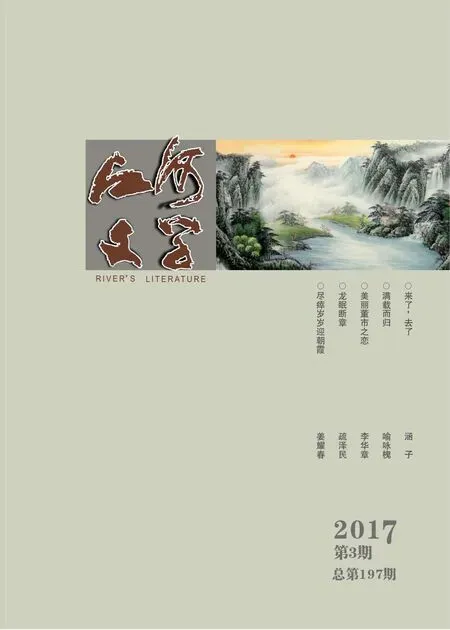布谷鸟的歌唱
■初守亮
布谷鸟的歌唱
■初守亮
黄河三角洲腹地,黄河岸滩最美丽的季节,莫过于五月的初夏了。鸟鸣啼啭着绿荫,绿荫涨满黄河岸畔。风光迤逦了华北的五月,这清新亮丽的季节,这景色怡人的初夏,给人多么丰富的联想,勾起多少往事的回忆。
黄河岸边那辽阔的大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麦浪,像浩瀚的海洋,澎湃着新一代的老农民的心潮,荡漾着老农民的欢笑。在这辽阔的麦浪里,摇曳着劳动人民的梦想,摇出了生活的希望。希望,带着夏日温暖的阳光,徐徐洒下,洒满了那鲁北平原“大粮仓”。
岸畔的绿荫可有着很浓的诱惑力呢。那些飘残的柳絮、杨绒,星星点点,如在寂寞地寻找着什么,却已失去了暮春时的那般排场与浪漫。过了小满,布谷鸟来了,带着婉转而悠长的啼鸣,如同极富韵律的歌唱,“布谷——”
此时,布谷的鸣叫声使整个大平原都活跃起来。它从朦胧的拂晓一直叫到暮色苍茫的黄昏,偶尔潜入夜的梦魂深处,使这个芳菲的五月沾染了一层淡淡的略带诗意的愁绪。
少年时,那夏日的阳光也算是毒辣,我总是不愿意睡午觉,也许是怕做白日梦吧。我总是喜欢在岸边的树荫下溜达,急切盼望早早听到布谷鸟婉转的啼鸣,轻盈而绵长,“布谷——”布谷来了,眼瞅着就要吃上那粗面的大白馍了。那时,同伴们常常唠叨:“布谷来,布谷来,下来麦子蒸白馍”。可是至今我却不解,同样的沃土,种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却还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半年粮中四月黄”,真正的大白馍只有刚打下麦子和过年时才能吃得到。其实,那年月,顿顿能吃到那拉破喉咙的玉米面窝窝头,就阿弥陀佛了。虽如此,我却对布谷鸟开始默默地喜欢起来。
或许是久居外地的缘故,我对脚下的路走得非常的熟悉,但对故乡的事物似乎是模糊了许多。“镇日叮咛千百遍,只将一句频频说: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那些诸如此类的伤春思归的诗句,一旦闪现脑际,也巧合季节小满,缘于布谷来了,开始鸣叫。对这种精魂化身的小精灵,不由产生一种期盼和喜爱的感觉,让我萦怀不已。而那种思乡心情,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淡去。记忆中,最清晰的灵信,也莫过于这布谷鸟的叫声,它那优美的韵律,发自肺腑,生生不息的歌唱,声声扣人心弦,使我如有蠢蠢欲动之感。
总也不会忘记那声声幽婉的布谷。当春天的颜色愈加葱绿、浓艳,而黄河岸边那辽阔的大平原,在夏日的阳光下渐渐褪色,褪成浅绿、淡黄、橙黄至金黄的麦浪,浩瀚无垠。看!人们走在岸畔的绿荫下,走在布谷的鸣声中,心情是多么的舒畅!凝望麦浪的眸子里,闪动着丰收的喜悦。
那片优美而绵长的布谷声中,蕴藏了许多过去的记忆。人们体悟着过去的贫穷,品味着今天的富足。那些时光的记忆中,压弯了多少擎天的脊梁,晒黑了多少俊俏的脸庞,展现了多少纯洁的灵魂,布谷声中倾诉着劳动人民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读着布谷美妙的歌声,吮吸着甘冽清醇的黄河水,在酸甜苦辣中挣扎着成长起来的人们,总是继承着先人留下的习俗,念着那片沃土的芬芳,知道布谷声中那份期盼、渴望和真实的情感,懂得生活的艰辛来之不易而万分珍惜,心中充满着对人生的美好和憧憬。
然而,如今的农村,已不再是那些灰蒙蒙的村落,亦非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泥泞小路,现在的农村人也不再是那些守旧、低调、庸俗的“老赶”,而是用着时尚的智能手机,电脑桌前获知天下信息的现代人。而那悠长的布谷声却像不朽的篇章,叙说着黄河岸滩一代代劳动人民生活的质朴与淳厚。
而今,小满已过,布谷鸟,这旷野的精灵,带着婉转而余韵悠长的歌唱,在阔别已久的黄河岸滩上,生生不息地鸣叫!“布谷——布谷——”天上飘来的绿荫,一直绿到天的那一边。滔滔的黄河水,浩浩荡荡,一路东逝,永不回头。那广袤无边的大平原,那麦浪……那祖祖辈辈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人们,生生死死,世世代代,都寄情于这绚丽丰富的黄河滩。当下,何以证明黄河岸滩的美丽富足呢?那林立的高楼,纵横的柏油路,雄伟的高架桥,以及人们心中流露出的喜悦,洋溢在脸上的笑容都足为见证时代变幻,沧海桑田。唯有布谷,每年春天,或高踞枝头,或自由飞翔,不断吟唱出美丽的赞歌。
“布谷——布谷——”
往事如书,布谷鸟的叫声如书,黄河岸滩的大平原亦如书,一页页从匆匆的时光和心灵的记忆中翻阅过去。它记述了时代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科技进步。不管如烟也好,如梦也罢,它驻在人们的心间,在人们心灵深处和记忆深处闪光。
责任编辑: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