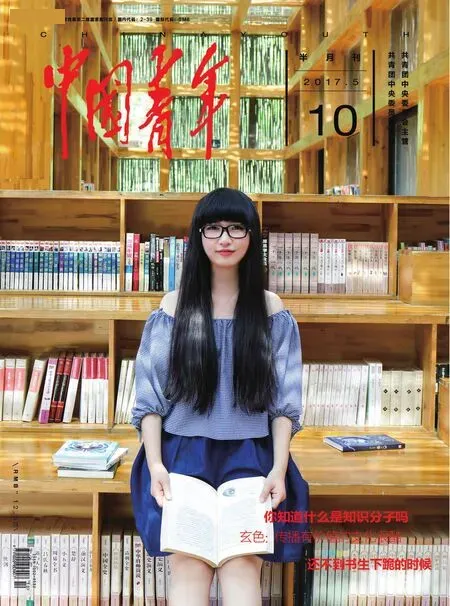李老七的瓜,老孟家的篓
文-马风
李老七的瓜,老孟家的篓
文-马风
我的老家,是北方一个偏远小镇,离家念初中前,我在那里整整住了十三年。那时候,没通铁路,也没有电,距离现代文明好遥远,好像生活在一幅色彩素淡、尺寸狭小的图画中。
十岁那年,小镇出现了一个多少年没见过的场面,差不多有上百人,参加了一个葬礼。要知道,整个小镇也就五六百人,而且全是自觉自愿来的。那个离开人间的人,无钱无势,地位甚至不如小镇的老百姓,是个最末等的草根。
小镇有座古塔,雕刻着六个观音菩萨佛像。那年代正反对封建迷信,可小镇是天高皇帝远,依旧敬神拜佛,古塔下一直是祈福、祭祀的最好场地。不只镇上的人,附近村屯也有人来,于是经常纸灰纷飞,香火缭绕,残留着各种各样的垃圾。塔旁边还有一片杨树林,天燥地干的时节,小镇人提心吊胆,担心烧香烧纸引发火灾。
可是这些,随着一个人的到来,烟消云散了。
这个人就是去世的李老七。他孤身闯关东,落脚到我们小镇,究竟叫什么名字,没人问,老的小的都叫他李老七。这个身材矮小,面色青黄,一天都难开口说上两句话的外地汉子,主动地揽了一份差事,当了古塔的义务守护人。从三十来岁开始,不分春夏秋冬,不管刮风雨雪,他单薄枯瘦的身影,总是围着古塔和那片杨树林,转来转去,一直转了二十多年。
他在塔旁边,钉了个一块板四条腿的木桌,上面摆着香炉烛台等物。其中多数是他动手做的,也有事主捐赠的。能吃的供品,比如糕点水果,他都给了来化缘的和尚道士。到了西瓜熟了的季节,他常抱来两个放在桌上,有人口渴,切开吃,给钱不给钱,都行。
李老七出殡那天,老天爷也挺难过,满天乌云,整个小镇变得阴阴沉沉的。我们家开了一间木铺,李老七睡的棺材,就是我老爸给他的,还让画匠特意在棺材头画上了古塔。小镇仅有的一家为红白喜事演奏的鼓乐班子,吹吹打打的四五个人,也免费为他送行。喇叭声悲伤凄凉,听得人都想哭。来送葬的年轻人,有的扎着白布腰带,像亲人那样,给他戴孝。还有人一面走,一面撒着纸钱。
就是这个平凡到底的李老七,教我懂得了什么是善心善行,默默奉献。老家乡亲则教我懂得了什么是感恩,什么是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那时候,小镇有好几家手工作坊,我一个姓孟的同学家,就是柳条编织专业户,他家店的祖传手艺,远近闻名,从直径一米多的笸罗,到拳头大小的小筐小篓,几十种,形形色色,质量过硬,精致精美,是小镇的一大名牌。
镇上没有自来水,用的是土井。长长的井绳底下拴着盛水斗,就是用柳条编的,叫柳罐。镇上的所有人家,包括镇外许多乡屯,打水用的柳罐,几乎都是出自老孟家。这东西,一定不能漏水,最好的也不往外渗水,还必须编得结实,经得住磕磕碰碰。外形像巨大的核桃,线条圆润匀称流畅,跟工艺品似的,无论哪个角度都耐看。老孟家出品的,就是行业标准。
当时,他们家主管编织制造的一把手,是我同学的爷爷。他已经七十多岁,将近六十年工龄,腰板弯曲得像个钩子。满头白发,连眉毛也白了,可两颊红扑扑的,鹤发童颜,浑身上下有一股用不完的精神头。
老孟家的大院子,到了不冷不热的时候,就成了露天编织场,对邻居包括镇里镇外的买主实行开放。十几个人坐在小凳上,闷头忙乎着。一根根柳条在他们手里变得十分温顺听话,变成这样那样的物件。来参观的人都睁大眼睛,感到无比新奇。
那个老爷子,手里拎着一根柳条,走来走去的,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发现什么情况,用柳条狠劲敲一下,什么都不用说,那个人马上意识到出了差错,连忙进行改正。有时候,老爷子会坐下来,像表演一样做示范性地操作,粗糙的手指,引来一道道惊叹的目光。
我常走进大院找同学玩,顺便看看热闹。那个老爷子虽然不怎么说话,可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编筐编篓,全在收口。”或许因为这些编织物最容易松散开裂的位置,就是边缘部分的“口”,所以要加倍花工夫对待。
编到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精神疲劳,也急着早点完活,就不怎么注重质量,因此老爷子才反复提醒,反复要求,声音很响很重,谁听见心里都会一震。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社会经历越来越丰富,“编筐编篓,全在收口”这句话,让我听出了远远超出柳条编织的范围。一句朴实无华的民间语言,闪耀着哲理的光芒,这么多年,一直警示着我。
责任编辑:宋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