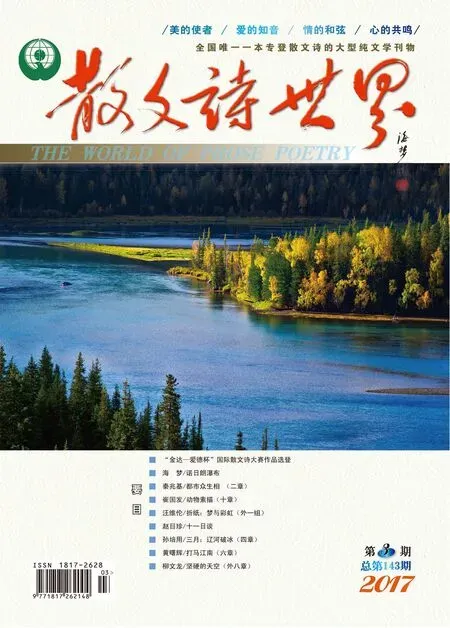动物素描(十章)
崔国发
动物素描(十章)
崔国发
猛犸塑像
遗世独立:依稀还能听到,猛犸的一声声狂叫。
寻归旷古的荒野。我穿越着时空连绵的混沌,于第四纪冰史里蓦然苏醒。
从象牙塔里走出来。
裸骨上莺飞草长。风中的木叶,野花,荒林,它们的脊椎似乎可以作证:不合时宜的巨兽,背负着一种原始、粗犷而健硕的思想与精神。
洪荒中的进化,生命与历史的遗传密码:引颈而作远古的呼告。棕色长毛飘飘。它的巨齿,大幅度地弯曲向上。时光在它蒙昧的脸上,铭刻着一道道深邃的皱纹。
可现在只剩下了,雪地上的雪。
已经见不到,猛犸的野性与魔法,有谁能够忍受,一尊冷石彻骨的寒意?
万物静默如谜。
梦回或招魂。亿万斯年的异类,于神秘主义的冻土和冰层里深埋:骸骨的冰冷。
苦寒的命,不硬。
我只有默默地祈祷,一种神话的复活,在史前的黄昏,隐藏着猛犸图腾巨大的宁静。
凤 凰
凤凰于飞:整个天空都是烈焰。
一直都不曾逃离。
衔香木而振翅,浴火,转世或重生,于动词的铿锵声律中,一次次地追问“我是谁”。
乾坤已定,一飞绝尘。
我不知道,还要在晚霭中飞出多远,才能抵达生命的神髓。
或许,它已忍受过了难以隐忍的疼,在黑暗中,火和空气在灵魂里燃烧,但骨子里的东西却不能取走,一种战栗的美。
凤凰在哪儿呢?
凤凰于飞但不是寻常的鸟类,五内俱焚却不受炼金术的专制,只是在它的背影转过之后,前世的拘囿,能否摇身一变为今生的自由?
既逝与重现,痛彻心腑的尖锐。
我真的没有想到,一个幽灵的塑造,原来是如此的在高飞中自足:
于地狱与天堂的两极斡旋,它没有节节败退。杜绝空难,我细致地体察着血的余温,透过时间的表象,越来越深入地感悟其内心的深邃。
凤凰于飞,与新的世界若即若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于云的波折中急起直追,电光石火一样呼啸的阵式。
蝼蚁颂
接触最多的是沙土。
命轻,得承认自己的渺小。
在夹缝中生存,仅一个小小的洞穴,便可以安身立命。
生而为蝼蚁,安于俗世的凡尘。清心寡欲,学会简单生活,视名利为粪土,不谈论高贵,无愧于卑微,它们怀揣的是一颗极其平常的心——
不攀高,是因为乐于脚踏实地,为天下的芸芸众生肩扛米粒,忍辱负重。
纵然,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而危机有时离它们也很近,却能淡然处之,从不惧怕无意之中被人踩死,也许它们,才是我要说的英雄的一种。
只是默默地、艰辛地赶路。
它们长途跋涉,总是缓慢、蹒跚而寂寞地前行,从未停下自己的步履,而能非常负责任地把搬运当作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永远保持沉默的声音。它们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不矫情,不折腾。
风吹浮云,山雨欲来——
蝼蚁一族,拥有足够的耐心,它们一再地告诫自己,在不起眼的边缘地带谋生,面对变幻不定的场景,必须时刻表现出真实、朴素与内心的宁静。
蜗牛演义
一生的苦役:或许爬之于蜗牛,就是它自己的命。
忍辱负重。
一直在前行,于道路的曲折中从未止息。
只要它还在走,我就没有什么理由苛责它慢条斯理。
欲速则不达。
即使是走不出自己重重的壳,却无论如何也不会陷入困境而坐以待毙。
跟不上风的节奏。
它的动作有些迟缓,下的只是一些笨功夫。
但我觉得这样也没有关系,接下来你自然还会看到,一只谦卑的蜗牛——
艰难地挪动着,被硬壳裹挟的柔软的身体:快与慢。硬与软。
它们永远在路上。
是一种演义,还是一种受苦的力量?
那时你是否已发现,它执著的足迹,是怎样弯弯曲曲地书写着一部生命的传奇?
驯狼令
应该给狼子一些驯令:可以有足够的勇气,但不能抱有一颗私欲膨胀的野心。
千万不要嗜血成性。
驯化与修行,我不允许它青面獠牙,也不允许它粗野凶狠,更不允许它深藏在草丛中,打埋伏,耍阴招,让许多动物在它恐怖的嗥叫里集体失声。
正大光明地走进,一片蛮荒的丛林。
如果可能,我会让它考虑放弃残酷的斗争,而学会与其他动物和平共处,并不是所有的攻击与追猎都能制胜。
让它不再有恨。爱绵羊的温顺,爱牛的敦厚与勤恳,爱狗的忠诚,爱鹿的轻盈与灵敏,甚至连野兔看见它,也不再心生畏惧,战战兢兢。
从相克到互生,从野蛮到文明,在这生机勃勃的大草原上,需要彻底地改掉,它的掠夺性。我努力地让它善待每一个生命,让动物在它们的理想国里,重新找到一片仁慈与安宁。
风在吹。
我相信受教育的狼,会潜移默化地参透道德的法则,但愿我严谨的驯令,也能刻骨铭心。
雁 群
它们肩并着肩——
我目送着它们有序地列队,就这样奔向诗和远方。
这样的事适合发生在秋天:天高。云淡。一群大雁,极像是黑色的闪电。
倾巢出动。
它们对于蓝天,有着又高又远的眷顾,并且真的知道,离开群众,会有多么危险。
早就相约着,一起遨游,追随,腾翅,旋转。
雁翎于气流中的艰苦磨炼。
推动秋风与秋风的对话与交流,穿越时空,筚路蓝缕,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雁群,
于曲折的天路中拓展,广阔无垠的生存空间。
内心已储备了足够的能量。
形而上的韵脚,轻盈地划过,它们无比亲爱的祖国。
当大雁的影子越来越远,我不再浮想联翩,听凭一股莫名的苍凉,从落日的瞳孔里升腾。
雁过留声。
试着练了几回粗门大嗓,还是当年的乡音。
一条瘦长的影子飘忽而过。那声音隐约传来,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的章回中,怎么听都是:双声,迭韵,连绵……
鹰之歌
面对鹰,我不想只说出仰慕。
当乡间的麻雀,更多地选择了低空飞行,唯有一飞冲天的鹰,在动词的奔突里大胆地挑战,一种翻动扶摇的高度。
这便是鹰所崇拜的自由:如果翅膀硬,好高骛远有何不可?
仿佛命中注定,它必须乐观向上,信念巍峨,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旺盛的精力与新锐的勇气,与那一片空悠悠的白云耳鬓厮磨。
补天浴日,异军突起,血脉中充满了冲动的激情。一种形而上的舞姿,已不再是他者审美赏心的匆匆过客。
不要说它一意孤行。一次次地涉过漫天席卷的风暴,又一次次地叱咤着疯狂咆哮的雷电,炼就了一身铮铮骨骼,鹰的辞典里没有怯弱。
飞起来,深入博大深沉、无限神秘而令人敬畏的灵魂圣地,
飞起来,梦想的空间越来越大,脚下的道路越伸越远,而自己的心灵,也蓦然变得幅员辽阔。
多年以前的蝉
很多年以前我就听到,它的絮絮叨叨。
话是不是说得太多?
杂音乱耳。直到现在,我仍没有摆脱它的纠缠,一种不厌其烦的聒噪。
夏日的热浪,一阵阵袭来……
虫声单调:是谁赋予它那么多的话语权?
我真的没有料到,它会深藏于法国梧桐的粗枝大叶里,着一身薄翼,衣袂飘飘,独享浓荫的清幽,却把酷暑的热辣抛向我们。
一次又一次地加重语气,唱着高调。世态炎凉,也不知道它是否知了?
——“既然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雁字回时
已经秋深。
雁子结伴而行,比翼齐飞,一点儿也不自由散漫,有势却不任性。
它们是高远的苍穹上健劲的移民。
扑棱着翅膀,到南方去。
谁寄锦书,出尘入云。闲云的影子,一朵挨着一朵,于井然有序的广延性上,把天空和我仰面而望的眼神,擦洗得干干净净。
不辞关隘远,也不问疲惫的身心。一群远征的游子,我所认识的天使,或许它们知道,意志如何使行为发生。
问世间情为何物?
它们集聚起周身的力量,向着一个温暖的地方飞,呼千里长风,渺万顷层云,衔着一片红叶追梦,执著地表达着内心无尽的忠贞。
西风紧。不作悲秋客,却可以于蹼的划动中翻山越岭,引颈长鸣。
似乎不需再打听,蒲公英飘散已久的消息。
还是排成一行行大写的人字——
我看好大雁众志成城的方阵,愿它们一路上的歌,留下一串串灵魂的和声。
鱼 群
连同它们自己也不知道,曾经的身世与来历。
随波逐流,让一片大海在体内汹涌。
精卵的繁殖与生息:
就这样,匍匐在水中,摆尾,嬉戏,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如何让我们这些站在岸边的人,渐渐地懂得,生命游动不止的意义。
穿过珊瑚与藻荇——
浮上来,让时间的鳞片在阳光下闪光;
沉下去,是为了在丰沛的血脉中,更好地飞翔或作舞蹈的练习。
无须探测。于无线的声呐中,我仿佛听到了,它们嘴边发出的唼喋之音。
鳍翅划过无边的蔚蓝。
不说孤独,它们沉潜在深深的海底,走的是群众路线。
无非是追赶、吹浪或呼吸,抑或是选择对钓饵的逃离。
不必瞒天过海,活着就有了存在。无非是让最优秀的自己,在浩淼的波涛中穿梭,并且祼身去接受:一次次灵魂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