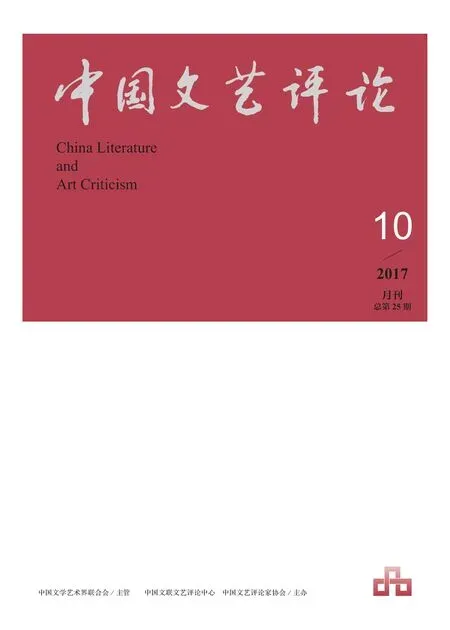媒介融合中“70后”诗人的历史焦虑
何光顺
媒介融合中“70后”诗人的历史焦虑
何光顺
“
70后”诗人的作品共同体现出一种植根于传统媒体与现代新媒体融合中的特殊历史境遇及渗透其中的深沉历史焦虑。首先,加速的生活节奏感、时间的破碎感和无意义感就构成了70后诗人独特的时间视野。其次,反英雄写作、去崇高化的大众视野表现出70后诗人对于外在世界无意义的清醒认识,他们更愿意退回到有尊严的自我和孤独之中。最后,时间视野与大众视野共同塑造着70后诗人的历史形象,他们或者创造着独属于自己的面对融媒介时代和未来的诗歌观念,或者在灵魂黏合剂中重新建筑出生命的宫殿。媒介融合 70后诗人 历史焦虑 时间视野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一切在衰老,一切也在新生。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诗歌的写作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是空前的。如果说,在古典时代,文学曾经写在甲骨上、羊皮上、竹简上、纸质上,这每一次的变革都为文学带来了崭新的命运和空前的机遇。那么,当文学开始出现在互联网上,在各种新媒体上,这次变革就不再仅仅是一种艺术承载介质的变化,而是其表现形式、思维方式和传播渠道的全新革命。当最新的互联网、移动网络和传统的印刷媒体、电视媒体等多种媒介处于深度交融之中,一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真实与虚拟的跨界融合,就在全方位地形塑和决定着文学创作和批评生态圈的变迁。这种由创作和传播媒介所带来的革命和变迁,相较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媒介变化,都将产生更为深远的裂变,这种裂变既意味着空前的机遇,也意味着深层的危机。
很多人在感叹,在这样一个媒介融合的时代,经典不再被重视,纯文学不再有市场,人心愈益浮躁,自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大众阶层开始获得了一种藐视知识精英和文化贵族的历史机遇。中国的“70”后诗人就恰好处于这种传统知识精英和文化贵族被迅速边缘化,而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愈益垄断社会的历史夹缝期,而这就造成了“70后”诗人深沉的历史焦虑,即那种源于传统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使命感无法实现的焦虑以及面对“80后”年轻大众文化读者追求快感阅读的无力感。文化的话语权多中心化,或者说从知识精英阶层不断向大众移动。于是,一种奇异的文学景象就在“70后”文学创作中诞生了,贯穿着历史忧思的等待焦虑和极具现代性碎裂感的时间维度,就成为其文学写作的内在性元素和精神因子。
一、媒介融合中的70后诗人的时间视野
这个时代没有伟人诞生
你望见的是谁的背影
——黄礼孩《背影》
没有经典,只有通俗;没有伟人,只有大众;没有智者,只有愚人。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没有了英雄辉煌闪耀的形象,只有在大地上忙碌迁徙的人群。亿万双盯着荧光屏和沉浸于虚拟网络世界的作者和读者,都早已失去了面对生活的自觉与勇气。诗人成为孤独者,成为了被大众抛弃的流浪者。于是,70后诗人黄礼孩笔下的“背影”,就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同题散文名篇《背影》里充满内在期待并在现实世界得以唤醒和实现这期待的奇遇,而是成了媒介融合时代的反召唤结构的大众文化的写照。不再同于朱自清笔下的“背影”,黄礼孩诗中的“背影”,就因为传统精英文化的流逝和现代大众文化的兴盛,而成为了中国典型的“现代性”的象征性意象,成为了70后诗人的真实的生存视野。
这一批诗人,不但早就远离了古典诗人和民国诗人因知识加冕的神圣角色,而且也没有50后、60后诗人如北岛、顾城等在经历文革的精神荒芜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纸质媒介获得最后辉煌的历史机遇。当然,70后诗人也没有80后诗人如韩寒、郭敬明等在进入21世纪并迅速适应网络新媒体突然成名的全新写作。这些年轻的文学新秀,不再具有传统知识人和文学人的道义情怀和神圣期许,在注重外在形象包装和当下文化热点炒作中,他们成为资本财富的新宠,那种古典的信仰和使命退居次要地位,只有在复杂的融媒介大众文化中迅速抓住大众读者的眼球才是制胜之道。
在媒介融合的当代文学生态中,新型媒介对于传统媒介的冲击,就可以置换成大众文化对于精英文化的摧毁。70后的一批优秀诗人如黄礼孩、黄金明、梦亦非、阿翔、翟文熙、陈会玲等,或许可能远比韩寒、郭敬明等在文学写作上更为纯粹,也更承传着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脉络,但在以眼球阅读和粉丝经济为核心的新媒体文化生态中,他们却也是被大众文化冷遇最久的诗人群体。在被当代历史冷遇中,70后诗人传达出了其追赶时代而又不沉沦于这个时代的时间焦虑与历史忧思。比如在黄礼孩的名作《谁跑得比闪电还快》:
丛林在飞
我的心在疲倦中晃动
人生像一次闪电一样短
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
生活又催促我去奔跑
谁能跑得比闪电还快?诗人并不是真的要写一位比闪电跑得还快的超人,而是表达出一切都在速朽、每个人都在奔跑、时空距离大大被压缩的媒介融合时代中的诗人的生存体验。当互联网、移动网络迅速取代传统的印刷媒体乃至电视媒体以后,一种远远超过闪电的速度,让每个普通平凡的作者或读者,都具有了书写或接受哪怕最遥远信息的可能。每一个封闭的圈子被打破,没有人可以做片刻的停留,没有人能让时间停下,“丛林在飞”,“人生像一次闪电一样短”,“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生活又催促我去奔跑”,空间的危机和被历史抛弃的焦虑感,灼烤着诗人,他必须去追赶这个加速度的时代。
在自然年龄和心理年龄与70后接近的1969年出生的诗人安琪的诗中也同样体现出这种让人沸腾甚至让人窒息的媒介融合时代的加速度生活节奏,比如在其重要作品《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中,安琪就写道:
脑再快些手再快些
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
快些快些再快些
快些,我的杜拉斯
亲爱的杜拉斯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诗人在前面说“亲爱的杜拉斯!/我要像你一样的生活”,这样的杜拉斯的生活,就是“快”的生活,就是这里说的“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急切地奔跑,这是一个速食的时代,是一个新的信息淹没旧信息的时代,是每一个人都疲于奔命的时代。然而,诗人却不甘于这样一个媒介融合时代到来中的让人窒息的快节奏的生活,当她发现这种快节奏就是扼杀精神、信仰和生命之时,她要让自己慢下来,于是,在诗篇结尾,诗人写道:“呼—哧—我累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这可以看作诗人从那种太过外在的耗费身体和生命的时间之压缩和心理之紧张中所渴望和找到的另一种返回,外在的生活无论如何追赶,都会疲累,不要去追赶一个大众文化时代的偶像的生活。
在对于这种外在时间的消解中,70后诗人将一种媒介融合时代到来中的时间的破碎感和无意义感推到了极致,比如梦亦非在他的长诗《儿女英雄传》中就写道:
带着不可剥夺的毒性,时间
一团2D脏雪越滚越大
在语言之光中自我压垮
散作日子,都是0与1
变作组合并散发倦意
——幻觉在持续
迷宫修建之前,特洛伊沦陷之后
梦亦非的诗可能是媒介融合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写作,梦亦非钟爱古希腊神话牛头怪迷宫的神话,该神话记述了英雄忒修斯(Theseus)刺杀牛头怪米诺陶洛斯(Minotaurus)并被米诺陶洛斯的女儿阿里阿德纳(Ariadne)用线团引导他走出迷宫。牛头怪迷宫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空间建筑,有许多暗道、叉路、曲折和迷障,这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空间化的物质世界对于生命所造成的陷阱,而引导忒修斯走出迷宫的线团,可以看作生命突破混乱空间的时间象征。“时间”就构成了生命的秘密,就是语词对于人之有限性的领悟与道说,认识这种有限性,人就能从恶的无限和空间的混乱中超越出来。
然而,在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到来的新时代乃至未来的时代,“时间”的秩序再次被粉碎,成为了完全挣脱物性、割断生命和世界关联的纯虚拟性生存空间,互联网的“时间”不再是有限生命的有限生长,而成为了数字和字母无意义的循环式组合,意义不再有效,生命沦为网络上的符码,“一团2D脏雪越滚越大”,“散作日子,都是0与1”,“它虚构这雪球,从木马滚落”,诗人无奈地道说:“所以,时间不过是一次虚构/它因无聊而摆弄的修辞”,于是,在梦亦非的诗中就大量出现数字、字母和乱码,在这篇长诗的末篇《回·尾声》中,就全是这样的字母、数字和乱码的组合:
@1010 0 10101010101010101010(
^010101010101玻0101010101010%
A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这样的乱码或字母与数字,是读者完全不能读懂的,也可能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种没有意义的语词或语言的产生,却是互联网或说媒介融合时代的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景象,无限的人们与无限的灵魂岂不都是游弋在这没有意义的虚拟网络生存之中。因此,当作者写完这首长诗以后,在结束的宣告中,他又指出这种乱码就是正文,就是媒介融合中的现代人的正式文本写照:“&本诗所有乱码均非乱码而是正文……”,这种庄严的宣告和全文的无意义的乱码之间就形成了相互的解构,这就像诗人在开篇对于“时间”所做的诠释:“但人们称之为创造,人类/后来被它假设出来的字节/做为雪在光中融化,做为/比喻中的睡鼠,所梦见的水滴”,人作为古老神话中的创造者的宠儿,却不过是这个世界无意和错乱中抛出或写出的乱码而已,就像睡鼠所梦见的水滴。
在我们从历史写作年龄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时间视野就构成了70后诗人承接传统印刷媒体叙事,又下启互联网新媒体叙事的交叉视角和生存境遇。他们固然有着如古典诗人或50后、60后诗人那样渴望进入文学史的等待焦虑和时间忧思,有着一种传承自古老经典与传统文人的自我先知式角色赋予中的使命感,却又有因应80后、90后的网络新媒体阅读和写作竞争中的焦虑感。在历史使命的传承和现代处境的焦虑中,他们做出了自己对于时间的独特诠释,并展现出了古典时间与现代时间乃至未来时间沟通的桥梁或断裂的鸿沟。于是,70后诗人,就成为在媒介融合视域中的跨界生存的独特的诗人群体。
二、媒介融合中的70后诗人的反英雄写作和大众主题
她敲下回车键,确信
他是这些词语之间的关系
——英俊、富有、历险、神力
——梦亦非《儿女英雄传·18 回.一些》
日常大众或小人物对于英雄的想象构成了这个融媒介时代的大众阅读趣味。好莱坞的大片曾经只是电影导演拍摄出来满足普通大众的商业影片,大众只是被动满足。而在融媒介时代,普罗大众得以借助网络新媒体主动出击,构建出自己被虚拟为传奇英雄的隐蔽欲望,这就是梦亦非诗中所写的“她敲下回车键,确信/他是这些词语之间的关系/——英俊、富有、历险、神力”,或许,梦亦非虚构的网络传媒时代的“她”对于“他”的想象的这样一个特定指向性叙述,是有深意的,那就是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的男权话语的一次颠倒。在传统媒体的古典男权和父权时代,性别想象主要是由男性作者完成的。在梦亦非的笔下,在新媒体的网络时代,性别想象却是由女性完成的。这里的“女性”并不真的是指向现实的女性的,而是表明一种感官想象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的男权文化的道德想象的颠覆,大众读者想象的人物是“英俊、富有、历险、神力”,这是小人物的想象,也是最日常化的欲望想象,没有了古典时代的理想和信仰,而更多一种欲望投射。
对于这种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时代转型中所带来的大众作者和读者的变迁,梦亦非在其《〈儿女英雄传〉小词典》中谈到了自己对于该问题的思考:“某一天福至心灵,突然想起烂俗的《儿女英雄传》这个名字,细一想,它对此诗内容极为妥贴,诗中有男有女,都是史诗、神话、电影、童话中的英雄,所以叫《儿女英雄传》再合适不过了。但诗中所写的并非英雄,他们都是些平庸的、平面的日常小人物,并非真的英雄,所以称之为‘英雄’,便带来淡淡的冷静的嘲讽之效果。”这些失去了内在精神指向的平面化的大众作者或读者,被梦亦非完全符码化地设计成“他”“她”“它”这样三个人物:
他是一条圆弧向下的线弧,她是一条圆弧向上的弧线,他们在切点处相交,它是一条直线,在中间均分二人并穿过切分点,而三条线都有箭头朝向开放性的未来。
历史和人物都完全被简化,一切都朝向新媒体时代的开放和明晰,没有人可以隐藏,虽然融媒介时代的作者和读者们仍旧在制造着迷宫,但这个迷宫再也不是古典时代的牛头怪迷宫,而是新媒体时代的“玻璃迷宫”,作者在这玻璃迷宫中插入了一个小小的字眼:小。“它变成了可爱的、卡通的、透明的、随时毁灭而又涵纳了这个历史时段的:玻璃小迷宫。”
梦亦非的这种反英雄去崇高化的写作指向,在另一位70后诗人余秀华那里同样得到了呼应。余秀华在主题和语言的指向上没有梦亦非这样的现代,但其对于这个时代的大众文化的欲望化和反英雄化却有着自己的体验: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这首诗是借助媒介融合时代的网络爆红进而一夜成名的作品,这首诗开篇就切入了“欲望”对于“极权”的无力反抗中的“空无”或“虚无”主题,就是作者在诗中所描述的大半个中国的灾难,那枪林弹雨的威胁,当一切的反抗都无力和苍白之时,作品中的主人公选择了在欲望中沉睡,选择了无意义指向的肉体书写。而这和梦亦非所谈到的其长诗《儿女英雄传》所针对的“空无”“物欲”“极权”形成了应合。新型媒介带来的可能并不是人们曾经期待的解放,而是更无处不在的严密监控与物欲勾引。
于是,我们就看到,70后诗人就身处这样一个历史的夹缝地带,这让他们既未如80后作者郭敬明等青春偶像式的物质欲望写作,也不抱有50后、60后诗人如顾城诗中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先知式执着或北岛式的“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的古典英雄式坚持。70后诗人的诗有着对于外在世界无意义的清醒认识,不去追求成为先知引领人们走出黑暗,不去追求成为英雄以作殉道式牺牲,他们更愿意退回到个体生命的小,退回到有尊严的自我和孤独之中。
这种70后诗人对于“小”的坚持与80后作者可能更看重大众趣味的写作方向不同,如梦亦非就将大众虚化为互联网上的符码化的数字和乱码式存在,这是对于大众文化取消意义的反讽和冷静旁观。余秀华将大众文化对于理想与信仰的吞噬转化为欲望的虚拟满足。而更具代表性的写作是黄礼孩、陈会玲等诗人的作品,体现出70后诗人对于互联网侵袭中的大众读者的柔和却又坚韧的抵抗,他们没有如梦亦非或余秀华的诗那样去反讽大众或欲望化大众,他们更在意的是自我的灵性坚守、在喧嚣世界里的孤独沉思与柔软之爱。
黄礼孩《独自一个人》写自己早上去赶地铁:“一路上,没有人与我谈起天气/在一滴水里,我独自一个人被天空照见。”描述了生命如“一滴水”的渺小却又澄澈的存在,在这种渺小和澄澈里,自有“天空”的广阔。陈会玲《拾碎》:“一个人老了/馒头一样松软的心/成了山岗上的石头/一半深埋,一半裸露。”描述了诗人面对生命苍老中的无力,诗人是孤独的并甘于这孤独,就如“山岗上的石头”一半隐藏于泥土,一半裸露于世人,她并不因为大众不能看见她深藏的精神而自怜,她甘于自己如山石一样的孤独者的生存。可以说,反英雄的崇高化,或者是反对大众的庸俗化,走向自我生命的内心,在其他70后诗人如阿翔、翟文熙、黄金明等的写作中,都成为了一种共通的指向。
三、时间视野与大众视野共同塑造着70后诗人的历史想象
在媒介融合的视野下,文学的读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致力于经典书写和使命承担的知音阅读迅速让位于现代的追求感官刺激和欲望满足的眼球阅读。这种变化同时也带来极其新颖的元素,那就是传统的士君子阶层高度依赖一种政治权力的担保,当这种政治权力发生变异之时,便无可挽回地造成士君子阶层的整体失落与政治权力对于知识精英的压制,一种一元化的权力知识结构便极容易形成。而在当代媒介融合的去精英化和非贵族化的新型文学生态语境中,就生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写作和批评现象,那就是现场写作和当下批评的盛行,作者的作品不是在完成之后,才接受读者的阅读和传播,而是在其写作过程中,就可以与很多专业读者或匿名读者进行多维度交流。这种写作、接受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不仅让文学从书斋走向社会,也是古典知识型到现代知识型转变中的文学的重大变革。
70后诗人对于这种知识结构的转型有较为清醒的认知,并借用自己的写作来回应这种转型。如诗人梦亦非从古希腊牛头怪迷宫的隐喻讲述了从混沌到秩序的文明创造期的古典知识结构的转型,又以自己创造的玻璃迷宫的隐喻来讲述从传统媒体时代到网络媒体时代的现代知识结构的转型。在“牛头怪迷宫”中,英雄是重要的,他们具有先知式的开辟秩序和文明的睿智与勇气。在“玻璃迷宫”中,没有人是重要的,只在作为符号和人称代词的“他”“她”“它”的出场,羽扇豆、雪球、乱码都指向了开端的虚无、过程的虚无和结局的虚无。爱是虚无的,生是虚无的,一切都成为程序设计中的数字和密码。基于对这种融媒介和未来媒介写作与传播中的大众视野的清醒认知,梦亦非认为,在现代知识结构的转型中,诗不再是古典的个性才情和灵感创作,而是转向了符合计算机网络语言的程序设计写作,这既是诗的新生,也是诗之死亡。诗不得不去展现人之未来的可能图景。
显然,在梦亦非的写作中,就具有了非常自觉的历史想象与历史焦虑,这正如他在看到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机器人写的诗集之后所感叹的:“再假十年时间,机器人写得比80%以上的诗人好。诗人没有危机感,反而嘲笑,这才可怕。”在这样一个精密的程序设计取代人的个体创造力的爆发性和偶然性的时代,梦亦非不愿意谈论诗歌中的生命、个体、灵魂、灵感、信仰和意义,他认为诗人的写作,就是要在历史的维度上贡献出新的知识。在技法上、修辞上、语言上、观念上,都不能再苟同于古典时代的诗人的情性化或叙事化写作。在一个现代知识型到来的时代,诗人要如建筑师和网络程序设计员那样去构筑诗的宏伟的大厦,从这种写作的历史自觉也是历史想象中,梦亦非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面对融媒介时代和未来时代的诗歌观念,开启了一种从未来出发进行诗歌设计的写作道路。
在做客广外的一次讲座《知识结构转型中的诗歌写作》中,梦亦非就以朗诵他的《儿女英雄传》的片断来结束了他的讲座:
“可怕的不是世界崩溃,而是不崩溃
你我被删除,世界仍然是一张网络”
他在3D地图上感叹,程序结尾
晚霞现出,她与他在海边对话
“如果一切都是虚无,那将是安慰
但虚无者,却只是自己的肉身
这彻底的失败属于每一个角色……”
那时他没有眼泪,对白被系统所设定
“我们的不存在也即世界的不存在”
她却反对,“但世界因不实有而永远存在”
它操纵他与她的对话速度
但不知道,它也只是她的假设
关联的世界中TA们都被卸载、删除
不在实有、虚无,而是在两者之间关系过程
TA们没有恐惧,也没有孤独
散入……0与1幻化的晚霞与海浪
这首诗无疑会对习惯了古典阅读的普通读者造成强烈的冲击,这种冲击是历史性的,而其关键就是以大众所置身的现代传媒语境和时间视野来挑战和刺激大众。大众既是敏感的,又是迟钝的,大众的敏感在于他们能迅速运用诸多现代技术手段和工具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大众的迟钝在于他们的观念和想象却是停留于过去时代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讽,大众坐在互联网之前,大众看着3D电影或地图,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散入……0与1的幻化的晚霞与海浪”,当自己被数字和符码化时,“TA们没有恐惧,也没有孤独”,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传统的世界已经崩溃。这就是诗人在这节诗篇开端处所写的“可怕的不是世界崩溃,而是不崩溃”,不崩溃的是大众永远滞后的观念世界,他们永远不能跟上这早已完成的现代型知识结构的转变,他们以虚拟的图景存在于古典没落的黄昏之中。
梦亦非关于诗歌是程序设计的写作观念,或许在70后诗人翟文熙这里得到了回应。翟文熙的《时间软壳》就可以看作一首结构精巧的长诗,这部诗集有首尾呼应的精密结构,首先是《自序》中的《论时间、存在物及诗歌》,随后是全诗的五个部分“第一辑 神的天空”“第二辑 死亡与石头”“第三辑 帝国”“第四辑 自由与虚无”“第五辑 意欲的表达”“第六辑 新年,旧年”“第七辑 山居笔记”“第八辑歌莉娅,歌莉娅”“第九辑 论艺术的诗性”,这全篇的结构布置实际是从神的世界降到人的世界再回归神的世界这样一个时间隐线来展开的。
在这部诗集中,诗人翟文熙表达了其不同于梦亦非的另一种可以包容信仰和意义的新的程序和结构观念:
一首诗不仅是一座建筑,也是完整的宇宙。
星空、河流、飞鸟和无形的气体。
一切物体活着,围绕诗人的心脏。
翟文熙的诗歌观念没有梦亦非作品的完全激进的新媒体式的写作方式,而是在面对现代知识结构转型中的精密建筑和程序设计观念中保留了神性、自然、信仰和意义等传统的维度,在翟文熙的诗里,传统和现代并不是断裂的,而是可以有机组合的。翟文熙虽然消解了人们对于实体的执着,却仍旧坚持着价值和意义,“没有可以依赖的实体/诗的价值在言词背后。”这样,传统媒介的信仰承载和互联网媒介的程序设计就实现了一个完美的融合,程序并不消解意义,意义可以融入程序。我们可以将翟文熙的诗看作是对于未来时代的互联网和移动网络信息的符码化和空无化的拯救。
于是,在梦亦非的笔下,大众是互联网上飘移的虚拟的数字、字母和乱码,是玻璃小迷宫中的透明化没有深度的存在,传统媒介所代表的古典知识型和网络媒介所代表的现代知识型是严重断裂的,而诗人的使命就是要去追踪这未来时代人的真实生存状态,要看到互联网信息化的主宰和控制,抵抗可能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去展现。在翟文熙的笔下,互联网上的大众仍旧是抹平意义的,然而,诗人却不能屈从于这种意义和信仰的虚无化时代的到来,诗人要将飘游于互联网中的没有灵魂的“他”“她”“它”唤回到“星空、河流、飞鸟和无形的气体”,未来时代的程序设计必须服从“心灵的组合方式”:
他在岩石上刻下太阳的图案,月亮:
请投下你的阴影。
传统媒介所代表的古典知识型和网络媒介所代表的现代知识型在翟文熙给出的灵魂黏合剂中重新建筑出了生命的宫殿。太阳和月亮都有了“你”的生命的投射。“你”其实也就是“我”,翟文熙诗中的人物是面对面的,是相互沟通和交流的。于是,梦亦非笔下的无所指的“TA”就进入了翟文熙笔下的具体的“你”和“我”的呼唤、应答和对话,未来写作的意义重新被唤醒,诗歌的灵魂在人的灵魂朝向生活和自然的指向中得到救赎。
何光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吴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