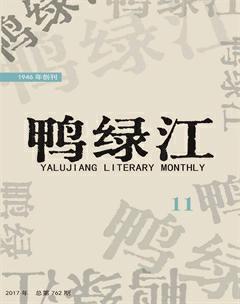花园尽处的风光
王雪茜
读克莱尔·吉根的小说会让人废寝忘食几乎是读者的共识,若说每个人都需要一本书来拯救千疮百孔的灵魂,吉根的书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她不是“文学药剂师”,她的小说也非治愈系作品。但如果你还相信文学有改变人类生活的力量,不妨读读吉根。
国内一些售书网站上介绍吉根的作品时,推荐语几乎雷同:每个故事都充满着希区柯克式的悬念和欧·亨利式的意外结局,她的小说集是当代最精致写作的短篇集之一。我当然同意——后一句。读完吉根的所有作品,我愈加相信,一个粗糙蹩脚的推荐语对于一部作品的伤害是多么致命,它太容易让我们与好作品擦肩而过!
我曾一度迷恋希区柯克的电影,情节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很难猜到最后的结局。众所周知,希区柯克在解释“什么是悬念”时,曾举过一个描述性例子:“假如我们在火车上聊天,桌子下面可能有枚炸弹,我们的谈话很平常,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突然‘嘣!爆炸了,观众们大为震惊,但爆炸之前,观众们并无紧张感,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毫无兴趣的极为平常的场面。如果是悬念,应该是,桌子下面确实有炸弹而且观众也知道,可能是观众在前面已经看到有个无政府主义者把炸弹放在了桌子下面,观众知道炸弹在一点整将要爆炸,而现在只剩15分钟了——布景内有个时钟。那么,原先无关紧要的谈话突然一下子变得饶有兴趣,因为观众参与了这场戏。观众急于想告诉银幕上的谈话者,‘别净聊天了,桌下有炸弹,很快就要爆炸。这样就让观众也开始动脑筋,他们也在为谈话者的生命安全着急和担心。”如果我们试图从概念上解释,悬念本质上是一种期待和关切的紧张心情,它要求接受客体的参与和想象。一旦悬念解除,故事也就完美落幕。
希区柯克的代表作《蝴蝶梦》,开篇即设悬念,被焚毁后的曼陀丽庄园阴森萧瑟,它经历了怎样的变故?故事以女主的回忆缓缓切入:在法国南部海滨,一名富婆的年轻侍女爱上了古怪忧郁的富豪庄园主德温特,对德温特并无了解的女主随男主来到位于英国的曼陀丽庄园生活,严厉的管家丹弗斯夫人毫不掩饰对新夫人的厌恶以及对旧夫人的崇拜,偌大的庄园到处是已故女主人丽蓓卡的影子,新夫人尝试适应新环境的努力一次次碰壁。紧闭的西边厢房,神秘的顶楼人像,奇怪的海滨小屋与小屋中的怪人,突如其来的丽蓓卡表哥,庄园里似乎藏着无尽的秘密。而更令她痛苦的是丈夫似乎永远只爱丽蓓卡一人,直到装有丽蓓卡尸体的沉船被发现,情节急速逆转,一环扣一环,凶手似乎已成定论,但其实真相悬而未决。
希区柯克就是有办法吊着观众的胃口,情节始终在走钢丝,观众始终捏着一把汗。《眩晕》是希区柯克最成功地运用悬念的又一部典型实例,在原著中,故事的谜团直到最后才解开,而希区柯克有着把原著中的神秘部分轻易转化为悬念的惊人能力,在这部影片里,希区柯克又一次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作悬念。男主受朋友之托,跟踪朋友有自杀倾向的妻子玛德琳,并在她跳水自杀时及时相救,二人在跟踪与被跟踪的过程中互生爱慕,但玛德琳还是在男主的眼皮底下爬上钟楼坠落而“死”。男主痛苦难挨,直到“遇见”了酷似玛德琳的朱莉,并尽力让朱莉模仿玛德琳以获得思念心理的满足,而在希区柯克暗示下提前知晓朱莉就是玛德琳的观众却一直在焦虑揣测:朱莉伪装成玛德琳目的何在?男主何时才会发现真相?知道了真相会如何?故事最终会怎样结束?
悬念的重要特征,用美国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的话说,就是“预示出一种十分吸引人的事态,却不把它预叙出来”。吉根的小说总体上并不刻意设置悬念,通常在故事开始前,冲突就已经存在。吉根只是按部就班地把它写出来,她不故弄玄虚,更不设置阅读障碍,她甚至极少采用除了顺叙之外的其他叙述手法。读她小说的读者也并不会因揣测情节焦灼起来,如同走在曲折幽暗的小巷,虽陌生迷惑但不会慌张恐惧。而看希区柯克的电影,观众如同走入万木丛生的密林,看似驿路千条,实则迷途而难返。吉根曾在访谈中说:“我把故事设置在一个自己很感兴趣的情景里,然后用语言探索它的可能性。我写一个故事的开场通常是一个意向或者一段对话,我知道这之后隐藏着更深的含义。我会写很多段落,直到我找到一段配得上这个场景的。” 她更在意的是人们如何对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心理的微妙变化,“探索人与人之间的沉默、孤独以及爱”。虽然生活有热烈如火的蓬勃,但她只写灰烬中的那一点余光。吉根擅长从生活打碎的镜子中寻找到那映照出人心的一面,并借助它锐利的碎片直刺进生活和人心的内核。
吉根不是一个写作快手,自1999年出版第一本短篇集《南极》,直到2007年才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立获边山短篇小说奖。2010年终于出了第三部小说作品《寄养》。她偏爱写人生中的残酷与苦难。她告诉记者:“我不会说我对生命悲观,我描述的只是现实。几乎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受苦,无处可逃。生活是艰辛的。” 美国作家理查德·福特将《走在蓝色的田野上》选为他个人的年度好书。尽管吉根喜欢契诃夫、狄更斯的短篇,甚至深受契诃夫的影响,也喜欢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菲茨杰拉德、哈代、简·奥斯汀、托尼·莫里森的早期作品……但她说:“我不想跟谁的名字放在一起,我只想成为自己。一些作家我很欣赏,但我不想模仿,如果什么东西是好的,它应该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獨特的。关于写作的一件事是,别人并不能写你想写的故事。”她是一个叙述上的极简主义者,不同的只是她的语言具有无限的延拓性,包含无尽的未言之意。生拉她的作品与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或阿加莎·克里斯蒂安硬扯在一起显然是对吉根作品不负责任的解读。
现在我想说的是“想象”。希区柯克电影中的“想象”无处不在,如《蝴蝶梦》中丽蓓卡是否真的是集教养、才识、美貌于一身的完美女人?德温特是否真的爱丽蓓卡?丽蓓卡到底有没有怀孕,怀的是谁的孩子?丽蓓卡是自杀还是他杀?是误杀还是谋杀?观众始终置身于雾里云里,在刺激、跌宕、惊险的情节中发挥最大可能的想象,揣测故事下一步的走向,转折或明朗,及至结尾真相浮现,观众如释重负,想象力也戛然而止。担任时代天线的电影大师控制着引人入胜的环节,在观众的叹息、犹疑、不满或痛快、舒畅、豁然开朗中像一个辩论赛中把对手驳倒的辩手那样获得了智性上的满足。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安是个同样娴熟运用悬念艺术的小说家。《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开篇即是一个美国人死在了豪华的东方快车包厢里,他被刺了十二刀,可他包厢的门却是反锁着的。侦探波洛无意中听到了两位旅客阿布斯诺上校与玛丽·德本汉小姐之间的三次对话,对话产生的有悖常理的信息立即凝聚了读者的强烈质疑,故事开端即笼罩扑朔迷离的悬念。之后波洛在质询快车上的“嫌疑人”时悬念层层叠加,隐含的信息牢牢抓住读者的思维,强化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期待,只要未到终局,无论好的坏的,都是过程中的偶然事件。犹如剥茧抽丝的悬念设置,它的目的在于凝聚吸引力,让受众被悬念俘虏,急切想获知真相,故而,悬念大师希区柯克不吝惜胶片,悬念小说家克里斯蒂安不吝惜笔墨。环境的渲染烘托,人物神态尤其是眼神的细腻刻画,模糊而异常的语言陷阱,共同达到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人物形象在精心的情节设计和观众的揣测里显得更加生动完美。毫无疑问,悬念使得情节更复杂多维,人物更饱满立体,并且,悬念要达到的最重要的效果之一就是让你“想不到”。
吉根的故事恰恰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无限拉长的长篇的瘦身版。说得通俗点,每个故事都像一块压缩饼干,蕴含着可以发酵的能量。我指的当然不仅仅是读者可以通过合理想象延展的故事尾声,我指的更是从词语、句子本身所具有的余韵而言。她并不想让读者认为她在讲故事,读者也并不认为她在虚构故事,她也不玩弄“使结构充满风险并且也给结构带来光彩”(罗兰·巴特)的一种结构游戏,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到紧张或恐惧并不是她的风格,尽管桑塔格说过,好的作品是会让人紧张的(这判断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她所写的正是普通爱尔兰乡村人家,普通的父子、母女、兄弟姐妹、朋友、邻里之间的平常情感。她的主角就是她身边的普通人,大部分是普通的爱尔兰乡村农民。克莱尔·吉根只是将日常生活中内敛、隐性的情感一针见血地写出来,表达精致、准确又冷静、克制、从容,对深刻人性充满同情、理解。她的选材不是随机性、偶然性,是她犀利观察后精准的筛选。而这种观察的犀利一般作家却并不具备。吉根曾说她对短篇小说更感兴趣,她是继爱丽丝·门罗之后极少见的只靠两部短篇作品集就跻身世界一流短篇小说家之列的作家。她认为,短篇小说很紧凑,你必须把大多数可说可不说的话删掉,这是一种减法原则。就如聊天,似乎说得很多,其实真正说的内容很少。短篇小说更有张力,世界上大多数长篇小说都太长了。她“很有兴趣描写生活中的一些关键时刻,这些关键时刻应当以某种激烈的方式来描写”。 这种激烈的方式常并非一定是引人入胜的矛盾冲突。一个适合的场景,一段耐人寻味的细节,几句看似平常的对话,往往揭示出她要表达的那些残酷而苦难的真相。吉根总是反复地掂量、斟酌、摆布每一个场景,每一处细节,甚至每一个句子和词语,直至安稳,成为故事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故此,吉根小说中那些难以预料的情节,那些转瞬即逝的短命情感,需要读者有非同一般的神经和与作者一样敏锐的直觉才能捕捉到,这与希区柯克电影中观众必以活跃的想象力身临其境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安小说中读者强烈的断案参与感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第一篇故事叫作《离别的礼物》,女孩被母亲打发去父亲房间陪父亲睡觉,大概一个月一次,总是在哥哥尤金出去的时候。“此刻,你站在楼梯平台上,努力回忆幸福的感觉,一个美好的日子,一个夜晚,一句友善的话。应该寻找某种快乐的东西,让分离变得艰难,可是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你想起的是长毛猎犬生崽子时的情景。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母亲开始打发你去父亲的房间。在水房里,母亲对着半桶水,把袋子摁到水底,直到呜咽的声音停止,袋子变得,一动不动。那天她淹死了小狗崽,她转过头来看着你,笑了。”一个普通爱尔兰农妇复杂隐蔽的内心世界最黑暗的角落就在吉根的笔下血淋淋地裸露出来,你很难用简单的善恶来定义这个农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难以预料的残酷情节就那样波澜不惊地铺开,不需要读者紧张地揣度想象,不需要借助悬念或其他任何叙述技巧便已将残酷而真实的世界击碎在读者面前。是的,作为读者,读吉根的小说,不能囫囵吞枣,你必须读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如契诃夫所说,如果故事中出现了一支枪,那它一定要发射。细节似乎看上去很随意,但它会直接影响故事的发展,就如《南极》中出现的那只猫,开始只是一只猫而已,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说到结尾,希区柯克或克里斯蒂安故事想象力结束的地方正是吉根故事想象力最丰富之处。希区柯克或克里斯蒂安的结尾总会使观众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这也是悬念大师们希望得到的最受鼓舞的肯定,不到最后一分钟,悬念大師们不会打开所有的灯光。吉根的故事结尾则看似波澜不惊,不疾不徐,实则余韵绕梁。前面提到契诃夫是吉根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契诃夫也是对吉根影响最大的小说家。如果说吉根小说的结尾受到了契诃夫结尾和欧·亨利意外式结尾的启发,我不否认,毕竟契诃夫、欧·亨利都是具有公约数气质的作家。但轻率滥用固定式结尾来定义吉根的小说则未免轻浮。那些通过过滤网筛选出来真正热爱吉根异色之作的读者是不会把吉根与契诃夫或欧·亨利相提并论的。换言之,痴迷欧·亨利式结尾的读者可以绕道而行了。吉根小说的结尾是独树一帜的吉根式结尾。
简单比较一下契诃夫小说和吉根小说的结尾,自会一目了然。“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发上,后来就……死了。” 这是我们熟悉的《小公务员之死》的结尾,叙述语言像小公务员的死亡一样简洁利落,只写结果,不表心境。讽刺意味大于余味。同是悲剧结局,我们看吉根的《南极》结尾:“……她能在黑暗中看见自己的呼吸,感到寒冷正慢慢笼罩住她的头部。寒冷开始降落在她身上,一轮寒冷的太阳缓缓升起,正把东方照得发白。那是她的想象吗,还是窗外正在下雪?她看着床头柜上的钟,钟上不断变换的红色数字。猫看着她,黑色的眼睛像两粒苹果籽。她想到了南极,雪和冰,还有探险者的尸体。然后她想到了地狱,想到了永恒。”吉根对女主彼时心境做了细致又蕴藉的描述,每个词语都勾连着可拓延的情节,比如有关猫和地狱的反刍性思考。读者的想象与回溯和女主所受的死亡前的煎熬一样长。在冷冽的多雪之境,不由令人反复想起以色列最著名的诗人叶胡达·阿米亥的《战场上的雨》,“雨落在我友人脸上/在我活着的友人脸上/那些以毯子遮头的人/雨也落在我死去的友人脸上/那些不遮一物的人”。这些落在死者和生者身上的雨,也曾落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思绪里,“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或曾经落下/下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雨》)”。冰冷的雨与雪,都会使悲伤蔓延倾圮。而这倾圮,又带着无言的悲剧之美,遥照了乔伊斯《死者》结尾处降下的那场明亮而寒冷的大雪。“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地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安葬着迈克尔· 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像带着私人标签的抒情诗,《南极》结尾的抒情性大于叙事性,这也是吉根很多小说结尾的共性特征。
“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楚蔑洛夫对他威胁说,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继续在市集的广场上巡视。” 这段是契诃夫短篇《变色龙》的结尾,故事仅到奥楚蔑洛夫威胁银匠结束,他是否收拾了银匠我们不得而知,也不迫切想知道。思维到此而已,既不诗意,余味也寡淡。
“三个人就这样坐在那儿等着:科迪莉亚,医生,他的妻子,三个人都在等,等一个人离开。”爱比破碎的梦还要冰冷。吉根《爱在高高的草丛》的结尾是我看过的小说中印象最深刻的结尾。撇开整篇单看这几句话也许会觉得平淡无奇,但就是这么奇怪,普通的句子在吉根小说的结尾就成为一首诗,未分行的诗。没错,是开放式的结尾,也是如契诃夫一样的简单叙事,但你知道它就是与众不同,它有自己的文化血液,它是小径分叉的另一个花园,是大相径庭的另一片天空,是对一种情感状态细腻而暗烈的抒情,它所绽放的几何美和静态美真是妙不可言,它刷新了我们对小说结尾强大的美学惯性,故事虽已落幕,但我們放不下这个故事,内心仍五味杂陈,似乎仍与三个人一起在等待,等一个人离开。
《护照汤》里的男人饱尝失去女儿的内疚,又要忍受妻子的折磨。痛苦让包含痛苦在内的一切变得缓慢,当痛苦加速达到沸点的时候,故事结束:“这是一个开始。这比什么都没有要好。”这两句几近哲理的小结,像一股长绳,丢在了落入深渊里的绝望男主身边。痛苦是否会离开,什么时候离开?当痛苦加速的时候,也许就是它离开的时候了。
《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的部分故事延续了《南极》余韵悠长的诗性结尾方式。《离别的礼物》借叙述抒情,“你忍着,直到打开并关上另一扇门,把自己安全地锁在小隔间里,你才哭了出来”。逃离了贫穷、粗粝、猥亵的家庭氛围的小女孩,逃离固有的困境,却不知最终要走向哪里。未知的漂泊、孤独、迷惘与眼泪一同倾泻而出。一个故事结束了,另一个故事刚刚开始,结尾提供了另一个向度与可能。《黑马》的结尾以想象抒情,“睡意袭来时,她已经在这儿了,苍白的手放在他胸口上,她的那匹黑马又在他的田里吃草了”。贫穷、鄙陋、懒散又粗鲁的短工因粗暴气走了温柔的女友,期盼已久的宽恕并未到来,凄凉的夜里孤独怀念着生活中曾有过的那一点暖意,“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尾声顾左右而言他,不言愁而神已伤,思念连梦境也不放过。
至于我们熟悉的欧·亨利式结尾,王安忆在《短篇小说的物理》一文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他的故事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作,不会让人的期望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 《麦琪的礼物》里,贫贱夫妻百事哀,唯一值得骄傲的是女人拥有一头瀑布般的金发,男人继承了祖上珍贵的没有表链的金表。而结尾为了给对方送圣诞礼物,女人卖掉了金发买了表链,男人卖掉了金表买了梳子。《最后的常春藤叶子》中生命垂危的青年画家只能看到病床外日渐凋零的常春藤叶子,丧失了生命勇气的她认为最后一片叶子落下就象征她生命的陨落。知晓此情的老画家贝尔在最后一片叶子落下的风雨之夜爬上墙画了一片叶子。《二十年后》的结尾以一张便条揭示原委:“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自己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女巫的面包》里面包店的老板娘对常来买陈面包的艺术家产生了好感,自作聪明地在陈面包里加了黄油,结果却毁了画家辛苦几个月画好的准备参赛的建筑图样。欧·亨利总会在结尾处给还没有思想准备的读者心理猛然一击,读者总会在心里惊呼一声“好巧啊!”或者“好意外啊!”就像在英国中产阶级那些读书人扎堆的地方,每次只要出现什么巧合,旁边就会有人议论说:“这就像安东尼·鲍威尔的风格。”
但吉根并不想创造一种出人意料的震撼式结尾的风格。拨云见月、柳暗花明、曲径通幽或者瞬间的逆转、错愕而困惑、醍醐灌顶……这类适合欧·亨利式的词语一点也不适合吉根。诚如吉根自己所说:“我并不想让读者惊讶。我愿意认为我的故事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有时候让人感觉突然,但它是必然的,顺着主人公的情感逻辑发展的。如果读者觉得结尾突然,他们一定犯了一些错误,漏掉了一些信息。”吉根的有些小说甚至像谜语,它需要阅读的智慧,比如《跳舞课》《烧伤》《水最深的地方》,谜底需要读者自己去领悟去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小说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
吉根的小说立意追求新颖但不以奇特为目的,情节张弛有致而不以跌宕起伏为媒介,结尾余韵悠然又不凭借出乎意料为桥梁。一言以蔽之,吉根就像一个化妆高手达到的最高境界——“妆成有却无”。
【责任编辑】 于晓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