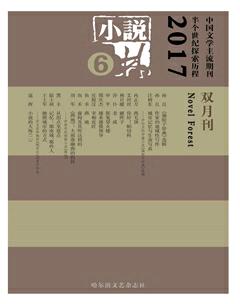记忆:那座城、那些人
四合院
一直想写一点东西,记录我生命中曾经的人和事。
伴随着这种念头浮现在眼前的常常是短短的、弯曲的小胡同,昏暗的、带着光晕的路灯;斑驳、沧桑的老树,缤纷的白色落英;夏天傍晚让路人猝不及防的疾风暴雨,冬日寒冷街头烤白薯铁桶冒着的团团热气。当然,还有那不时掠过上空飞翔的鸽群,以及堪称北京人永难弃舍 “桑园”的四合院……
幼年,最深刻的记忆是姥爷家住的四合院,北京西城跨车胡同。相比于那些规矩整齐,“口”字形一进院落,“日”字形二进院落,“目”字形三进院落的四合院,相比于“庭院深深深几许” 的大户人家四合院,姥爷家住的四合院不大,虽也有三进,但第二进、三进的院落并非在正对门的深处,而是在右侧。在主院的东北角有一个狭长的小通道,因为连接院墙和房屋,小通道不仅不长,还很窄仄,加上头上有顶,并不露天,所以我的印象中,小道从来都是黑黑的、挤挤的,总有一股湿凉的味道。
走过这条小道,二进和三进的院落就不是正规的四合院格局了。二进院三间北房一溜儿排开,每间房子都不大,没有一般四合院房前的高台阶,更没有方方正正的院落。房前只是一条通道,不长,尽头有一个小门,进到门里便是三进院儿了,一样只有一排三四间房,坐北向南。小门的南边是二进院和三进院共用的厕所,坑位不多,至今我仍留有清晨排队上厕所的印象。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很多,屋檐下常常倒挂着晶莹的冰柱,厕所里外,寒风凛冽,人们穿着棉裤棉袄,手揣在棉袄袖子里,缩着脖儿,不时地跺着脚,在京城冰冷但新鲜的空气中,等着排出身体里积累了一宿的污垢与浊气……
虽然不十分规范,但狭长的二进院,三进院还是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小院里有树,大约三四棵,都是好多年的老树。那时北京的树显得高大、挺拔,不像今天,人工制造的摩天大楼下,人类自己都变身成蝼蚁,自然生长的树木更是被挤压成了草芥。那时的夏天,树叶婆娑,树荫盖日,立身树下,不由自主地会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在小胡同的四合院里,树木遮挡了当头的烈日,也荫蔽了世间的嘈杂。
好像有一棵榆树,北京人叫他榆木疙瘩,很高大,已经有了些年纪。老树每年都会结榆钱儿,一到白白的榆钱儿挂满了树枝的时候,舅妈就会打了榆钱儿给我们做包子,那种美味记忆终生,仿佛再也寻觅不到。还有一棵枣树,不知为什么,我对这棵树结的枣是什么味道一直没有什么印象,但我记得枣花盛开的时节。每年六七月,青绿色的白花开满枝干,带着淡淡的香味儿,仿佛一副缀满花朵的华盖,伴着清新,伴着温暖,轻轻地在你身上抚摸,在你耳边诉说……
姥爷的家就住在二进院和三进院里,早年间姥爷活着的时候,两个舅舅和姥爷一起,住在二进院的三间房里。后来两个舅舅分别成家,分住在二进和三进院间的小门两端。小时候去看姥爷,后来到舅舅家玩儿,还真没有什么深宅大院的感觉,就觉得是京城街巷胡同,普通百姓群居的小院儿罢了。长大了以后,我有时会想,我的两个舅舅,一个是小学教师,一个是铁路工程师,就是现在所说的工薪阶层,大约也就只能租住这样的小院儿了。而小院的房东,也绝非什么豪门望族,不过是有着一份小家产的平民百姓罢了。现代人頭脑中的四合院,很遥远、很高大、很贵族,但我童年记忆中的四合院,很熟悉、很普通、很亲民……
二进院、三进院的简陋还是很难阻挡我幼年对四合院记忆的美好。以至于直到现在,我也一直认为,居住着房东一家的四合院主院就是老北京货真价实的四合院。院子的大门涂了红漆,朱红色,门两边儿好像还各有一个不太大的石礅儿,红门加上石礅儿,多少有点沧桑的感觉。院门有一个很高的门槛,到底多高我无法做判断,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门槛很高很高,迈过去很费劲。一进院子的大门,迎面是一扇影壁,上面画些山水仕女什么的,是一种中国水墨风格,黑白两色,好像一直画的是两个侍女。年节有时会加加工,但我记忆中从来没有另画过其他图案。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每到姥爷家,幼小的我看到朱门和门礅儿,迈过高高的门槛,面对厚厚的影壁,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庄严肃穆之感,仿佛进入了一个和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带有某种含义的殿堂。长大了,当我回忆起这种感觉的时候,不由得会庆幸,我生活在北京,生活在处处都蕴含着精神与文化,处处都含蕴着担当与传承的古老的北京。
沿石阶下去就是主院,除了东面的影壁,其余三面都是带沿儿的屋子,要登上高高的台阶才能走进屋子。北面的大房子冬日阳光充沛,夏日微风轻柔,放眼望去,磅礴大气;西厢房娇俏玲珑,雕刻着精巧图案的木窗散发着静谧的气息;而南屋是厨房和仆人居住的地方,凌乱,但充满了生活的味道。院子不大,方方正正,四角有四个大缸,缸里养着金鱼,鱼缸旁种着一丛丛的玫瑰。
通常情况下,我是在二进院、三进院里活动的,但也会常常贸然地冲进主院。记忆中雪后四合院里的冬天并不十分寒冷,白雪静静地落在石阶,落在房檐,也落在早已没了枝叶的玫瑰花丛之上。金鱼已被转移到屋里,只剩下鱼缸里的水冻成了结实的冰坨,清澈晶亮,冬日的阳光直透缸底。碰巧了,积雪会在鱼缸边落上薄薄的一层,仿佛给黑褐色的大缸镶嵌上了一圈洁白晶莹的花边,自自然然地给冬日的四合院平添了一丝妩媚和暖意。
而记忆中四合院的夏天,总是凉爽舒适的。走在院落里,铺着青砖的地面,踏上去细碎、阴湿;沙沙的风带着京城特有的清馨拂过脸庞,吹来阵阵玫瑰的香气;傍晚的时候,远处会时时传来鸽子飞翔的哨音,掠过小院的上空,也掠过人们的心头,带来了宁静,致远和祥和……
岁月流逝,我色彩斑斓的童年,我挚爱的家园!
苏先生和伊先生
四合院的房东是苏先生和伊先生,两个漂亮的女人。小时候,我一直想不明白她们是什么人?她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她们为什么可以这样生活?长大以后我觉得,她们活的是一种追求,一种状态;她们要的是一种自我,一种自在;她们任性,也必然是挣扎。和一般人相比,她们是另类,也是传奇。
小时候,我常常趴在门缝里“窥视”她们的生活,心头也常常涌出无数个为什么?她们俩都很好看,而且总是穿得很华丽。她们待人和蔼,说话总是慢声细语,就是我们这些乱蹦乱跳的小孩碰撞到了她们,或者吵闹影响了她们睡觉,也从来没见过她们变脸、发火,或大声呼叫。有时说起房东,我妈总会说,苏先生和伊先生是有教养的人,出身书香门第,都上过大学,有文化……而比她们年长的我的三姑姥姥却会说,都是好人家的闺女,真是可惜了的……
我不大懂三姑姥姥说话的意思,更想不清楚她为什么这么说,但在我早年生活的记忆里,对苏先生和伊先生的好奇与不解从来就没有淡化过。
首先是她们的生活方式,我从来没见过她们早上起床,一般情况下,北屋的声响总是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传出来的。先是仆人王妈送茶送水,伺候梳洗;然后就是厨子老丁传饭摆盘,碗筷叮咚。京腔京韵伴着粉脂的香气,溜过门缝在小院里漫延;欢快喜庆的气氛伴着咿咿呀呀的声响,越过花丛在四合院里跳跃。几许,两位先生打扮齐整,珠光宝气,流苏摇弋,踏上门口早已等候多时的人力车,飘然而去。我一直奇怪她们去干什么?更想知道她们会在几点回家?有几次妈妈带我住在姥爷家时,晚上我会借故迟迟不肯上床,或者躺在床上迟迟不肯闭眼,全神贯注地聆听着门外的动静,可惜我一次也没有等到她们俩回来。有一次,趁我妈高兴,我不失时机地询问,苏先生和伊先生晚上几点才能回来呀?我妈先是随口说,怎么也得三四点以后……然后马上警惕起来,呵斥我说,小孩儿家家的,问这个干什么?这并没有解除我的困惑,反而更加深了我的好奇:苏先生和伊先生晚上干吗去了?大人为什么不好好告诉我?
让我不明白的还有她们俩的关系。虽年幼,但我能觉出苏先生伊先生相互关心,感情极好,举手投足,让你时刻能感觉到她们俩之间的那种默契;言谈之间,让你清楚地体会到她们之间的交流与呼应。她们好像不是姐妹,也不是亲戚,她们不姓一个姓,长得也不像,但她们共同生活,相互关心,出入同行,同寝同眠。她们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让你感觉到,她们之间的相处,比姐妹更亲近,比夫妻更相融?我还能隐约感觉到,相比较而言,伊先生伟岸,颇有男子气概,苏先生婉约,婀娜多姿。于伊先生而言,苏先生小鸟依人,时时表现出了羞涩、依赖,以及无限的信任;而于苏先生而言,伊先生高大强壮,时时呈现出了仗义、支撑,以及可靠的呵护。
若干年后,我知道了三件事。
第一,她们是昆曲的票友,一个饰演小生,一个是青衣,有不错的艺术造诣。在大学期间,她们是同学,在一个剧社里总是饰演相恋相惜的才子佳人,书念得好,戏更是越唱越精致,以至成了校园内远近闻名的昆曲票友。毕业之后,伊先生工作了几年,苏先生一直在家,闲暇时,时不时装扮起来,和朋友们唱上一曲。尽管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但对于昆曲的挚爱却始终把两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再后来,伊先生辞职,靠家庭的财力和自己的积蓄买下了这个四合院,接苏先生一起,俩人一道成为货真价实的昆曲票友。一周内一定有几个晚上,两个人参加票友的演出,依然是一个小生,一个青衣,全情演绎着你亲我爱的古老爱情故事,直至深夜而归。
第二,她们是同性恋,早已相爱多年。长期的舞台恋情浸润着她们的感情,陶冶着她们的情愫。随着舞台艺术水平的提高,对剧情的理解的深入,两颗心也越走越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人开始意识到,她们的生命不可能再分开,她们各自的生活中,也不可能再容得下其他的异性。回忆起她们俩的音容笑貌,特别是两个人相处时的那种感觉,今天的我有时会想,岁月和经历,大约使她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现实生活,什么是剧情中的那个社会了,以至于她们也难以现实、准确地确定自己和对方的社会性别角色。让我感叹的是她们的勇气,我遇见她们的时候,大约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舆论氛围,不可能给同性恋以空间和喘息,但她们坚持自己的选择,任性地忠实着自我。我想,这大约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超出常人的坦诚和真实……
第三,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个凄凉的夜晚,她们俩吊死在北京郊外的一棵松树上。从大人们闪烁的言辞中,我听到了一个令我难以畅快呼吸的故事。先是大字报,后是抄家,然后苏先生听到了第二天要把她们监禁的消息。当天下午,两人烧毁了她们过去生活的所有重要痕迹,特别是那些让她们万分珍惜的剧照。一顿简单的晚餐,二人执杯互祝,为昆曲,为一生的相依,为天国的相聚洒泪惜别。然后,最后一次穿好戏服,画好戏妆,再次登上门口已等候多时的人力车,常年接送她们的老车夫老泪纵横,默默无语,拉上二人,走向无尽的黑夜之中……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无数个苏先生和伊先生的故事早已有了不同的结局,但苏先生和伊先生凄美的故事却让我始终难以忘怀。
有时,寂静的夜里,苏先生和伊先生会突然跳出来浮现在我的眼前,粉黛锦衣,委婉长腔,一段人生,一声叹息……
太监
姥爷家四合院的南边紧邻的是齐白石的家,他家的管家是一个原来清宫里的太监,大家都叫他公公,史公公还是齐公公?我记不清了。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到齐白石的管家是一个曾经在清宫里做过太监的人,姓尹。
尹公公个子不高,印象中矮矮胖胖,有一张黑黑的脸。都说太监声音尖细,但我对此并无太多印象,因为公公话并不多,每日都能见到他在门口出出进进,很是操劳的样子。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清宫里出来的,更不知道什么是太监,可能是孩子特有的敏感吧,在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中间,尹公公一直是一个窥探和议论的中心。记得有一次,一个长我一两岁的姐姐,悄悄地把我拉到胡同里一棵老槐树阴影下,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个尹公公是个不男不女的人……还有一次,几个男孩子打架,吃了亏的一方临走恶狠狠地指着对方说,你别美,赶明儿长大了,你就是个尹公公……记得那时,我们窥探和议论最多的问题是,他有老婆吗?有孩子吗?当然一直困扰我们,萦绕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的问题还有一个,那就是他为什么老板着脸?难道他不会笑吗……
虽然一直很关注这个被称为尹公公的人,但因为我并不住在那里,只是节假日被妈妈带回姥爷家时,也就时不时能见上尹公公一两面。因此,对于深藏在六十年前记忆中的尹公公,我的脑海里只留有些许的片段。
一是辛劳。我的印象中,尹公公总是一副忙碌的样子,或是在门口迎送宾客,或是在白石老先生前后张罗;要么是清晨和仆人一起潑水扫院,要么是黄昏巡查四周关锁大门。和周围的邻居们相比,齐白石的家算是大户了,年幼的我们分不清他们家里都有谁,只知道他们家里人口挺多,来的客人也多,有时还会有坐小轿车的客人来。那个时候街面上小轿车不多,所以碰到有小轿车停在他们家门口的时候,我们一群小孩就会远远地看着,指指点点,时刻伺机趁没人看见的时候趴在车窗往里看一眼……他们家还会经常有外地的客人来,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一住就是几天。尹公公是管家,凡有人来,不管是坐着轿车的贵宾,还是远方而来的乡党,不管是拜访求画,还是拜师求艺,不管是茶饮小聚,还是备餐宴客,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总见尹公公拖着矮胖的身躯,一溜小跑,或前恭后倨,或前倨后恭,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左邻右舍还会议论,说白石先生抠门儿,连家里装粮食柜子的钥匙都要把在手中。每到饭点儿,做饭的仆人得等老先生开箱取粮;凡有客人来,白石先生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留饭,尹公公身为管家,免不了上下协调,里外周旋,殷勤相陪,好言相送,个中的辛劳自不待说。
二是威严。尹公公不苟言笑,印象中,我好像就没见他怎么笑过。但我见过他训人。有一次,厨子不知做错了什么事,好像是趁白石先生不注意,米量多了,这应该是犯了齐府的大忌。我从他们门前路过,看见在门洞里尹公公正在训斥那个厨子。他黑着脸,两眼直瞪着厨子,好久都不说一句话,厨子不敢抬头,尹公公说了一句,看着我!声音并不大,更没有厚度,但很冷,很硬,很强,渗透着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厨子诚惶诚恐地抬起了头,尹公公仍然不说话,仍然用冷洌的目光直视着他。长大以后,我见过无数人训斥下级,训斥孩子。当我看到有的人长篇累牍,炫耀般地讲道理的时候,当我看到有的人高声厉语,气势压人的时候,当我看到有些人污言秽语,肆意谩骂的时候,就会想起昏暗的门洞里那个个子不高,声音不大,但显然控制着基本关系和整体氛围,不怒自威的老太监,想起那个虽然比太监高出一头,但却被人控制,自觉降低,诚心自责的年轻厨子。
三是怪异。小时候,一直觉得尹公公这个人怪怪的,我们都怕他。一个是他身上有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好像是“神圣不可侵犯”吧。这种尊严感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之中,表现在他整个人的状态里。尽管他少言寡语,但举手投足,会让你觉得没有任何闪失与不当;尽管他又矮又胖,但矗立身边,会让你时时刻刻感觉到威严与内在力量。在大人们的闲言碎语当中我也能听到,他是经常被人好奇议论的太监,好多人总是在想着怎样才能窥探到他的隐私,但邻居们谁也不敢跟他提及,更没有人敢用轻蔑和鄙视的眼光看他。另一个是孩子们特别怕他,尤其是女孩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不知为什么,走过他身边总会有一点阴森的感觉。我还清楚地记得,有时我们这些小女孩和他相遇,他会突然碰我们一下,机会合适,他会掐我们,胳膊或大腿。虽然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我依然能够记得那种感觉,不是身体上的,也不是物理性的,那种刺伤和恐惧来自心灵,是来自一个被摧残过的心灵的刺伤,是对于一个未知灵魂深层次的恐惧……
慢慢的,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他身世的零言碎语。他出自盛产太监的河北河间府,因家贫幼年时就被迫成为了“阉人”。其实,古时太监又被称为宦者、内侍、寺人,本来是宦官的一种官职。估计,尹公公的父母和河间府百姓一样,之所以让年幼的孩子受此酷刑,是希望孩子能过上好生活,不仅衣食无忧,还可以有望像李莲英一样,成为皇宫里有权有势的官宦。但尹公公进入到这群人当中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走向没落。后来,他随那些流落民间的太监一道,辗转到了齐白石家。胡同里的邻居们说,尹公公识字,不知道是原来在家乡读过书,还是后来在宫里学的,反正他爱看书。有时,难得他高兴,还会和邻居们就某一本书的情节和思想聊上两句。我那个写一手好毛笔字,一直认为自己挺有学问的大舅就曾说过,尹公公是个有点学问的人……
六十年是一个不短的岁月,可以使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成长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花甲老人。六十年来,尹公公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当中,伴随着鲜明的形象,还有那不可言说、不可透视的内心世界。其实当我们观察和思考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他的身世,他的故事所吸引,但我们真正走进过他的内心,尝试过以一个人基本人性的视角去理解他吗?
就像尹公公,有谁真正理解和体会过作为一个人,他深深的、无法言说的生理创伤,伴随着生理创伤而来的庞大、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刺痛,以及他在用怎样的信念和自控维持着生活的平衡的呢?
三姑姥姥
三姑姥姥是我妈的姑姑。在我童年的记忆当中,她仿佛是一朵素净的莲花,静静地绽放在岁月的留痕当中。印象中,她是大家闺秀,身材娇小,神色平静。在姥爷家住的四合院里,她总是一身素净的长袍,夏绫罗,冬绸缎;总是怀抱一只白色的小猫,脚下蹲一只小巴狗;总是静静地站在院子里玫瑰花丛旁,不言不语,神情落寞……
三姑姥姥的父亲,也就是我妈的爷爷,据说是清代海军的一个管带。因此,早年时他们的家境很不错,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三姑姥姥不仅衣食无忧,而且一兄一姐都对她呵护有加,她还念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听妈说,从小三姑姥姥就性情温和,乖巧听话,从不高声恶语,更无张狂刁蛮的恶习,是个左邻右舍人见人爱的好姑娘。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她的命运会如此多舛。
天有不测之云,本是北京城里富裕家庭的温顺女孩,因父亲的官宦身份,世情国运就直接危及了她的生活。甲午中日海战,父亲战死疆场,不见遗骨,也不知详情。虽有抚恤,但家境还是迅速衰落,三姑姥姥舒适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十七岁时,在大姐的主持下,她草草地就嫁了,哭哭啼啼地被送上了花轿,抬出了给她留下无尽温暖的家。
好在夫家富裕,嫁过去的三姑姥姥依然衣食无忧。更难得的是,先生也是性情温和,书读得好,知道疼人,夫妻你恩我爱,举案齐眉,感情极好。全家人都为这个小妹妹感到高兴,认识的人也都说,这姑娘命好,遇到了这样的好夫君,好人家,以后的好日子长着呢……
婚后,这个老实温顺,安静平和的富家媳妇,却做出了一件震惊社会,影响周围的“壮举”。过门不久,夫家婆婆生恶病,到处求医,却一直未能治愈。在三姑姥姥的婆家,公公和她的丈夫一样是个老老实实的读书人,丈夫是独子,又生性柔弱,婆婆就是一家的顶梁柱。婆婆一倒,家里老小立刻就六神无主,乱成一团。三姑姥姥更是急得不知所措,和丈夫一道,求医问佛,以至到了见庙就磕头,见灯就添油的地步。一日,寻得一居住深山的“名医”,开出一副中草药,不仅草药难寻,而且需要活人肉做药引。公公、丈夫非常为难,三姑姥姥卻立即表示,你们俩负责寻药,我负责药引……救人心急,且草药确实难寻,公公、丈夫顾不上多想,急忙四处奔走,打探消息,托人询问,终于将草药凑齐。煎药之际,三姑姥姥退入内室,不一会儿,手托一个盘子,上面有一块鲜肉,略显跛行地出屋,从容地对公公和丈夫说,这是我大腿上的鲜肉,去熬药吧……不知是深藏民间的医生确有些本事,还是三姑姥姥一家人的诚意感动了上苍,亦或是婆婆自知责任在身不可撒手离去,反正后来婆婆身体日渐康复,一家人重新回归了平静的生活。但儿媳妇割肉做药引治愈婆婆的事还是在坊间迅速传开,人们盛赞其孝敬的行为,冠她以孝女的美称,一时间,温润静谧的三姑姥姥成了名人。忠孝人家用她的事迹来教育女儿,疑虑的婆婆用她的事迹来敲打媳妇儿。若干年后,我在姥爷家遇见已是中年的三姑姥姥,曾经好奇地问她,你干吗要割肉啊!多疼啊!还得留块疤……三姑姥姥神情淡然地说,为救人呐,割点肉能长好,人要死了就没了……
据说当时的官府也被惊动,商议着授予她个称号,或立个牌坊什么的,但三姑姥姥的一家人,包括公公儿子,特别是她自己,本非图名逐利之人,对官府的称号、牌坊什么的没什么兴趣,因此根本无暇顾及,更没有苟且经营之心,这件事儿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倒是割股制药之事以后,丈夫更加呵护,公公婆婆更加爱怜,三姑姥姥在婆家的小日子越过越甜蜜。
可惜好景不长,婚后一年余,夫忽然患病,没熬过两三月,便撒手人寰。沉浸在幸福美满生活中的年轻媳妇,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的天就塌了。而当时,她却只有十八岁,直到七十余岁离开人世,三姑姥姥整整寡居半個多世纪。我不知道一直生活在富裕和谐家庭环境中的这个温顺安静的女子,是如何度过那一段,以至以后若干年的悲惨岁月的。
三姑姥姥没有子嗣,婆婆死后,她会经常住在娘家,我也就会常常遇见她。我小时候见到的三姑姥姥,总是淡淡、安静地在你身旁,少言寡语,从没有见过她开怀大笑。不知为什么,在院子里一见到她,我就会不自觉地放轻了脚步。因为你看到她,就会感觉到一种悲伤、哀怨的心绪,已深深地镌刻在她的灵魂深处,从面相到身形,从神态到精神,一丝丝,一团团,在向四周辐射……在她身边,你不敢喧闹,更不敢嬉戏,甚至都不敢大声说话,仿佛会有一种无形的情感和思绪,一种哀伤,罩在了你的身上,束住了你的手脚,绑住了你的灵魂……
丈夫死后,由婆婆做主,诗书世家的夫家,把一个亲戚的儿子过继给了三姑姥姥。这个被我们称为“开旭舅舅”的郑家子嗣,依然秉承着家传的忠孝之礼,三姑姥姥晚年,被儿子接到了自己居住的济南市,在家人的关护下,七十来岁,安然离世。
如今,当我在这个社会有着足够长袖飞舞的平台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我的三姑姥姥,想起她孤独的身影和落寞的神情,也会想起她晚年在“开旭舅舅”温暖目光注视下的平静生活。
三姑姥姥有文化,在她的寝室里,床边总是放着一本《石头记》,有时,她也会淡淡地说起莺莺和红娘……我总是在想,三姑姥姥不愁吃穿,而且有文化,在她起伏跌宕的一生里,在看似平静的岁月中,作为一个接触民国时代文化的女人,她内心会有怎样的痛苦和挣扎?
三姑姥姥十八岁守寡,一生落寞,但到了晚年,她和一般人家的老年人一样,脸上透着平和与满足。我总是在想,如果没有娘家的亲情,没有过继儿子的孝道,没有中华民族家庭里的种种文化的传统,她又怎么能够得到虽不能真正满足,但还算能过得去的日子呢?
作者简介:陆士祯,教授,1982年1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曾任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副总编辑、副编审,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务长、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等职,筹建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社会工作系。现任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促进会常务理事等职。著有《青少年社会工作》《中国特色志愿服务概论》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