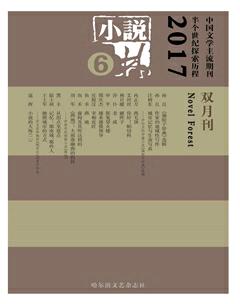作家的地域性写作
孙且
我的小说创作始于对偏脸子地域的书写。
每一个作家总与他生活过的地域相关,他不可能凭空产生,地域文化是他的母乳。
籍贯所负载的不仅是地理,而且内蕴着该地域的文化传统。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和维度来看,一个人的一生中,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至关重要——故乡,故园,那里的自然景观,习俗民风,历史遗存,还有方言等,无不从一个人能够理解事物开始,日积月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形成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心理结构。
地域文化的印记以“先见”根植于作家的内心,在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地会对母地的地域文化给予格外的关注和热情,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中所写,因为人“在地理世界中深陷其中无法避免”。
地理空间生成作家创作风格和气质的背景,那里的气候、氛围、甚至色彩和气味的痕迹,在作品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更深入地说,地域之于某些作家的作品内涵,可能构成某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和喻体。
一个地域在文化上越特别,越使写作者痴迷,我便是如此。
哈尔滨是一座独具历史魅力的城市,开放,包容,多元,在小说创作中,我力图赋予作为地域的偏脸子以文化坐标的意义。
作家的地域性写作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
有一种现象很容易被混淆,地域之于作家,易于被视作该作家的根。
在文学创作的发生学里,作家与地域的关联,只是构成写作的复杂因素之一。
有一些作家,并不受地域的限制,反而弱化地域性,形成我们说的离散写作。比如,纳博科夫从俄罗斯途经英国流亡到德国,之后又从法国流亡到美国,无论他在哪个异族,同样写出了跟地域性无关的杰出作品,或者也可以说,纳博科夫的地域性始终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
这类现象并非个案。
2017年10月5日,瑞典皇家学院将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是“一个不知家在何处的作家”,讨巧地用更令西方人接受的叙事方式,讲述早已与自身剥离的文化和记忆,同样可以获得成就。
正如北岛所说,“我随身携带的行李,只是我的语言。”
作家始终无法摆脱受自己民族文化影响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构成的限制。一个作家无论以何种方式写作,在何处写作,他均摆脱不了这根植于血脉的原动力。
作家借重地域题材和地域文化,可以获得足够的成功,但是,如果仅仅依赖地域资源有可能成为创作的桎梏,必须超越地域,借重地域性而突破地域视阈。
一方面,地域视角和地方经验存在自己无法摆脱的局限和困境,另一方面,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是人类的本质,人是一种双重存在,即作为自在之物的自然存在和作为自由主体的超越性存在。
十八世纪的歌德,腻烦了普鲁士诸侯小国对宗教、文化发展的地域限制,提出“世界是一种象征”。
文学创作最终要寻找到精神意义上的想象空间和文学地理,即建构作家的“精神原乡”。
当下,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日益汹涌,地域的文学书写和文化研究不仅仅承载着历史寻根的时代意义,也具有保护人文生态的民族寓言的高度。
这是我下一阶段努力的方向,借提炼地域性文化,表现超越时空的情感,构建自己的文学的地理和想象的空间,与相异的地域文化交流与碰撞中形成对话关系,以释放其自身的文学能量。
每一个地域,在作家笔下,不只有一个,有多少个视角就有多少个地域。
我的新作《偏脸子辞典》——还在继续修改中,没有最后定稿——就是想做出前面讲述的新尝试,现摘出几篇,请大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