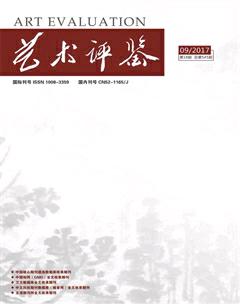寓黄梅之情于民族声乐
陈倩
摘要: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盛行在当代社会的民族声乐和起源于安徽的大方大戏——黄梅戏之间又有什么特别联系呢?本文通过介绍黄梅戏和民族声乐的相关背景,从“字韵”到“舞台表演”来谈谈两者间艺术情缘。
关键词:黄梅戏 民族声乐 字韵 舞台表演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8-0058-02
笔者自孩提时起耳畔边便时常传来音弦之声,四坊邻里间胡琴技艺、戏曲情声皆有。弄堂里窄窄的巷道抬头便是湛蓝的天空,一个娴适的午后阳光正好明净,隔壁大爷的录音机里传来一阵惬意之声——那是《孟丽君》的选段,其刚阿婉转色之声仿佛线铃一般穿过了童年的梦回响在耳际。《孟丽君》是各大戏曲剧种中经典不衰的名段,而笔者更钟情于黄梅版本。说到此,黄梅戏早期本是一些民间小调集成,辛亥革命至建国后才逐渐由黄梅调发展为较规整的黄梅戏延至今成为地方大戏。而在博大精深的中华艺术文化的长河中淌着一股清流——“民族声乐”,简单来说即是以声乐的形式演唱中国创作歌曲。无论是黄梅戏曲亦或是民族声乐在歌唱艺术中各自都有着璀璨夺目的风采,而在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当代社会,这两种艺术体裁的碰撞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谈到民族声腔不免使人联想至一句经典——“依字行腔、字正腔圆”,这是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美的声腔造型要求之一,同时当它的技巧融于表演也是情绪释放的必备原则,不仅如此,传统戏曲也同样应用这种法则。起源于安徽的黄梅戏无论是在表演还是声腔造型上都累积了丰富经验,就其声乐曲调来说,多数较为固定的曲牌;从艺术歌曲的创造来说它不是据词谱曲或依曲写词,很大程度上它要求演唱者吻合声腔和字韵的统一,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细致的处理和精心的创造。这种创作手法在要求表演者在舞台上需做到“声演同具”,从而达到非凡的戏剧效果。而中国民歌在表演方面也正是需要引借这种同步因而使得舞台效果更为饱满,如此一来,黄梅戏曲对民族声乐来说有着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此外,黄梅戏还有着其独特的“行腔之韵”,即湖广韵,其吐字清晰自然,曲调调迂回婉转,从听觉上明显有咬字上下起伏、旋律悠扬回旋的享受。这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了汉字独特的韵味,也符合了中国广大听众最感亲切的内在审美意识。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演唱的民歌作品韵律仅起伏在固定的旋律之内,若是乐感稍佳者添加些许装饰音或许能达到推波助澜的效果。那么,若是自然添加黄梅戏音韵在一些民族声乐作品中,是否会有锦上添花的效果呢。
一、“字韵”
黄梅戏与笔者此前想象的戏曲有所不同,单从咬字方面来说,其作品不会使人对字词有模糊感听起来反而清晰且流利自然。即便如此,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伴有着湖广韵特色的旋律,几乎每个字彼此间都起伏、婉转、迂回。大家耳熟能详的黄梅戏曲莫过于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演唱的《女驸马》,其中经典传唱歌曲——《谁料皇榜中状元》开启了笔者对黄梅戏曲的最初探索。比如“为救李朗离家园”中“李”字唱成“离”,“离”字唱成“力”;“帽插宫花好啊好新鲜”中“花”字唱成“化”,“好”字唱成“昊”等。就上文提到的《孟丽君》的经典对唱段《游园》——其中郦卿唱到“紫薇花对紫薇郎,好比万岁与娘娘”“牡丹应插金瓶上,凤栖梧桐皆朝阳”这个句段既体现了黄梅戏方言特色又突出了韵与旋律相结合的黄梅韵调风格。当中“万”字唱成“腕”,“娘”字唱成“酿”,而“阳”字因为地方方言因素,唱成“燕”和“样”的中间音。这些影响着整首歌曲的韵律起伏的“字”不仅仅包含了“湖广韵”的属性,同时也结合了一定程度的当地方言。不仅是一次听觉享受同时也叫人神清气爽如沐春风,那么这些又如何应用于民族声乐呢?
民歌《牧羊姑娘》讲述的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旋律生动且忧伤感人。我们不难发现,若在气息运用自如的基础上保持正确的高音位置且咬字靠前,那么从旋律伊始按照正常的歌唱路线至结尾是能够做到深情的表达作品的。问题是这样一首美丽的歌曲如果只是做到情绪到位难免有些普通,倘若将黄梅字韵与普通话相互置换是否会有特别感觉呢?我们暂可期待一下。如将“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什么这样悲伤”中“娘”替换成“酿”,“你”替换成“丽”,又或将“主人的鞭兒举起了抽在我身上”中的“我”换成“沃”等,在不更改旋律的情况下做小幅度的字韵替换即变成“对面山上的姑酿,丽为什么这样悲伤,主人的鞭儿举起了抽在沃身上”。从韵律的角度“酿”“丽”包括“沃”字不仅能与主旋律和声同化而且符合整体情绪基调,这样即时在原生旋律的基础上只换了几个字也会使观众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并快速融入歌曲氛围。
除此外,我们熟悉的湖南民歌《浏阳河》中“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此句用黄梅曲调加以修饰即变成“浏阳河,腕过了几道弯”更加意味十足。不仅如此,中国的诗词歌曲引用黄梅音韵来修饰则能更加意蕴犹存——《如梦令》据李清照词改编成曲,其调清雅其境清幽。“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可将“晚”唱成“腕”,“花”唱成“画”,这样美丽的词律伴以黄梅韵脚相携,那朦胧的画面感便随之若隐若现。
二、“表演”
提及舞台自然离不开表演,而演员是舞台表演的核心,因此,向观众传达作品风格和基本内涵使其从视觉上对舞台产生依赖便成为了一个演员最基本的素质要求。黄梅戏曲随台本脚色的不同其身段表演各不相同,手段也较为复杂,但戏曲选段运用于舞台表演却可以相对幅度的简化。且以2000年央视戏曲春晚上韩再芬老师的作品《王昭君》为例,王昭君反映的是一个兼美丽和烈性于一身、不畏远嫁他乡且促进番和的这样一个典故型女子形象,因而要求演员在舞台上不仅唱到位还要将“昭君”的形象神韵传达到位。
韩再芬老师在《王昭君》一曲中扮演王昭君角色,表演上采用武旦的身眼步法且外柔内刚故而刚柔并进,眼神坚毅柔和又不失昭君端庄之形象。她在上台和前奏间隙有一些台步走动为塑造人物形象和戏曲情境做铺垫,进而唱到“昭君北去为和亲告,别了建章宫孤衾寒冷,不在有上林苑柳下伤春,远嫁塞外是我自请,愿汉胡永结秦晋两欢欣”时出自对歌词和情绪的理解开始从静态表演去倾诉人物遭遇。其神韵手势柔美而刚毅,让作为观众的我们仿佛看到怀抱琵琶远骋大漠的坚毅无畏的华夏儿女的形象,瞬间如临其境。这不禁让笔者想到中国民歌舞台经常碰到一种尴尬情形——演员美丽大方歌声也优美动听,可为什么你听着听着就走神?原因很简单,抓不住观众的灵魂就抓不住他的眼神。
就以歌剧花木兰选段《我的爱与你相伴终生》为例,同样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烈女的形象的花木兰有着比昭君更加坚毅、果断的性格,而这又是一首柔情且充满儿女长情的咏叹调,因此我们在通过表演来刻画舞台人物形象时情绪是复杂而矛盾的。大多数时候,表演者在舞台上就会用伸手、抚胸或摆头等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和情绪,甚至有人直接一唱到底,这样舞台氛围不仅尴尬,最重要的是如若观众不容易看出作品要表达的情境和内涵也就很难为之所打动。倘若将黄梅戏中青衣和旦角的身段元素加入《我的爱将与你相伴终生》的表演,舞台效果又会如何?
《我的爱将与你相伴终生》旋律一开始仿佛将你带进一片广阔无垠的草地,有一位身着战甲神情坚毅的将军正坐在草地望着湛蓝的天空若有所思。此时演员可以随前奏缓缓上台进入情境,随后唱到“啊,哥哥,我的好哥哥,我多想亲亲的喊你一声”可应用武旦用手势,武旦神情端庄且出手稳重较符合木兰形象定位。乐句进行到“百灵鸟唱得多么动听你听啊,它也在倾诉着爱的心声,梦里依偎在你的怀中想说爱你却又不能”——多么想卸下沉重的战争包袱做一个普通的人妻,然而国家危难之际身不由己,儿女情长只能深掩心中,可见这时候的木兰情绪已经进入了一段小高潮。演员在此段歌声和情绪都是复杂的,因而既要表现木兰作为将军的丰毅又要细致女儿的柔情牵挂,如若引用一些青衣步法点缀则能细化人物特点。另外,此曲旨在刻画木兰倾吐心声外还有更多愁思因而有大量的伴奏旋律,像该片段结束前伴奏就长达一分多钟,原则上歌唱演员可以不必继续留在舞台,但由于“我的爱将于你啊相伴终生”刚好是木兰情绪的顶峰点若是截取一段伴奏弱化再加一些旦角舞台走位,那么整首歌曲无论是情景还是情绪线条就更加完整了。
三、结语
艺术文化有着它独特的包容性亦如“同者相继不谋而合”,无论是民族声乐还是黄梅戏曲在各自领域都是璀璨夺目的,今日为表现更好的艺术效果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它们能相互吸收包容,如此艺术情缘可见国学艺术文化的魅力不容小觑。我们为营造更好的艺术效果引用它們的长处发扬它们的闪光点,希望给艺术热享者呈现更有特色的中国艺术文化。
参考文献:
[1]苗莉.黄梅戏行腔在民歌演唱中的运用[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8年.
[2]胡艺兰.浅谈中国民歌与黄梅戏的异同[J].现代交际,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