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打工者的“世界史”
——读《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 文 / 龙梆企
中国海外打工者的“世界史”
——读《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 文 / 龙梆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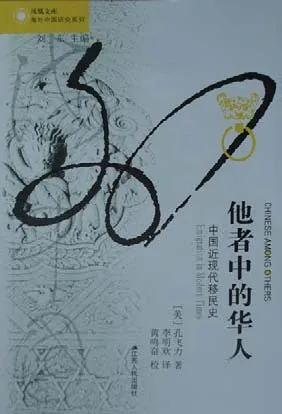
似是而非的议论
人的迁徙与流动,改变着世界,也改变中国。今日之中国,迁徙与流动已然是全社会的集体体验,几乎每个个体,或至少每个家庭都被卷入其间。
但尽管身处其中,对这个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个体的感受和认知,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迷惘与困惑。
比如,网络舆论,乃至茶余饭后朋友间的闲谈,说到今天的海外移民,往往是千篇一律的怀疑与恐惧。人们多少有些想当然地把这种移民行为,描述成有钱人卷钱跑路的故事。好像移民后,就不再跟中国发生联系,而他们带走的资产,也被视为中国财富一去不复返的流失。
这样的悲观论调,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出在哪里?
读历史学者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我们或许会有启发,再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或许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孔飞力是美国历史学家,2016年去世。他擅长从社会视角分析历史,此前他最著名的《叫魂》,就是一部从中国社会内部入手的晚清社会史。这次孔飞力研究的是海外华人。虽同样与中国社会史有关,但视角已改从外部。从外部,从华人移民社会看中国,自然可以看到从内部所看不到的地方。所以,这样一种“内外兼修”,使孔飞力在这本书中的见解,相当有洞察力。
再拿上述问题来举例。如果用孔飞力的研究结论来推论,那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比较乐观。也就是说,那些海外移民,不仅不削弱中国的实力,反而会加强中国在世界的影响。
为什么会得出这种截然不同,甚至与我们直观经验相反的结论?因为孔飞力发现,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移民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很独特的世界,他们虽然离开了中国本土,但却依旧与他们的家乡、家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移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家乡。”孔飞力总结说。
当然,今天的移民跟历史上的移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从历史上得出的经验不能直接用于预测未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经验依旧是重要的参考。
无形的“通道”
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文化独特的社会。其独特性,根源于中国传统的家和家乡的观念。
孔飞力分析说,中国人“家”的观念,基本原则是共同奉献,共同分享。比如,家长的去世,男性子嗣平均分家产,这是家庭成员的权利,但家庭成员也有义务。这种义务就是,无论离家多远,都肩负着家庭的道义责任,必须将收入的一部分寄回家。
在家庭之外,还有家乡。家乡是家的扩展,移民同样有无法割舍的情感和道义责任。情感方面,我们比较熟悉,俗语说的“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就是这种情感的表达。至于道义责任,则通常表现为对家乡公益事业的捐助,对家乡追随者的接引。
对于新移民来说,亲情和乡亲是他们在异域谋生的依靠。通过跟先行者的联络,新移民获得情感上的慰藉,甚至也得到工作、谋生技能上的引领。
历史上那些去海外谋求生计的劳动者,彼此之间通过故乡和亲人的纽带联系为一个整体,抱团取暖,精神上互相支持,生意上互通有无。于是,华人社会逐步形成一些地缘性组织,这些组织,又进一步强化了华人的社会竞争力,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社群。
历史上,会馆就是这种地缘性组织。会馆因地缘关系而组建,有的是一个省,有的是一个县,还有的仅仅是一个镇。这种地缘性组织,有共同的语言——地方方言,有互相的熟人,成员之间无论是聊家常,还是谈生意,都有互相信任的基础,在脆弱动荡的移民社会,这种乡情联结起来的关系,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孔飞力把移民社会这种互相抱团的现象,用生物学的一个名词来描述,叫做“小生境”。这个词的原义是描述同一个物种往往会生活在同一片区域,借用来描述中国移民在海外的生活方式,比较形象。
移民与家乡的紧密联系,造成了移民社会的两个文化现象。一个就是在移入地出现“小生境”这种集群现象;另一个就是在移民与老家之间,形成一条无形的“通道”。这两者的文化根源,都源于中国传统社会对家与家乡的依恋。
孔飞力创造性提出的“通道”概念,是建筑在移民与老家之间的无形的,但又持续性的资源流动管道。这条“通道”靠情感维系,把移民在海外的成就与故乡的发展牢牢联系在一起。孔飞力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在中华帝国晚期,此类通道,即金钱的、社会的与文化的繁忙路径,可谓纵横交错。”
其实孔飞力说的“通道”,在今天中国各地被誉为“侨乡”的地方,体现最明显。地方政府也特别擅长于维护这一条条无形的“通道”。这或许也是中国快速发展的秘诀之一。
发现东南亚
《他者中的华人》一书,研究海外华人社会,但其中涉猎最多的内容是东南亚,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他关注的中国的东南亚华人,主要是中国沿海从16世纪开始的持续不断的移民。这些移民的原籍早期以福建居多。很奇怪的是,他没有注意到从陆路到东南亚的移民,比如跟东南亚陆路相连的云南。这是很令人惋惜的地方。
孔飞力对移民社会的研究,实际上是间接地研究中国的地域文化。因为移民社会以地缘为纽带构建的“小生境”“通道”,其背后的文化都是按地域来区分。所以,福建的华人与云南的华人,恐怕也会有不同。
第二,东南亚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为一部分离乡背井的中国人提供了生计,更在于它是中国融入世界贸易的舞台。孔飞力把东南亚华人,放在新大陆发现后世界贸易增长的背景下考察,认为他们肩负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的中介人的角色。由此,他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新大陆发现之后,东西方文明在东南亚相遇,中国与欧洲在这里开始了世界贸易中的联手经营。
对近500多年历史,我们习惯的理解是,西方人积极进取,开拓世界市场,而中国故步自封,一步步落后于世界。但孔飞力从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中发现,中国不仅没有自我隔绝,而是卓有成效地融入新时代的世界贸易中。
换句话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是开路先锋,但世界贸易的好处,中国得到的并不少。在东南亚的港口,“从福建厦门出发的中国帆船满载丝绸、瓷器前来交换墨西哥的白银。当西班牙大帆船满载贵重货物返回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中国贵重货物从那里再转往欧洲市场)时,中国帆船则载着墨西哥白银返回中国家乡。”与此同时,还有荷兰、葡萄牙的船只也运载墨西哥白银经由欧洲和印度前来中国。
16世纪中期,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国是日本。被葡萄牙占领的澳门是日本白银的集散地。但“到1775年,从墨西哥流向中国的白银已经超过了日本,从而经由新大陆以及位于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将中国与欧洲市场连结在一起。”
东南亚华人,为什么能够充当中国与欧洲贸易的中介?
孔飞力分析指出,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东南亚统治者特别重视与明朝的关系,他们通过生活在这里的华人来实现跟明王朝的联系。华人是这些当地统治者的客户,作为他们商业事务的经管人,实际上长期卷入东南亚的商业体系之中。
16世纪欧洲殖民者先后抵达东南亚,占据了东南亚的港口等商贸通道。东南亚港口城市易主,但华人的社会地位依旧得以维持。孔飞力总结说,早期殖民者在三个方面严重依赖华人,一是与中国的贸易,二是从殖民地获取财富,三是为殖民城市提供服务。
欧洲对东南亚的征服,靠的是坚船利炮,但中国的东南亚移民,靠的则是勤劳的双手。所以,在殖民者进入东南亚后,东南亚的华人也不得不与殖民者合作,为其所用,以换取保护。
这种合作充满变数。欧洲殖民者对东南亚华人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不得不合作和扶持,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是中国的利益代理人。这种矛盾态度,直接造成了历史上东南亚的多次屠杀华人事件。
比如,1603年菲律宾的马尼拉是欧洲人第一次大规模屠杀华人。孔飞力说,1639年和1662年间,在马尼拉华人遭到报复性屠杀。在印尼的巴达维亚,1740年也发生了类似屠杀。
被屠杀,最足以说明华人在东南亚的艰辛。但正是这样的艰辛,造就了此后几个世纪里中国在世界贸易上的王者地位。这一地位,后来被鸦片贸易,以及欧洲的工业革命撼动。但这已经是几百年后,也就是1800年前后的事情了——中国的衰落,其实并不是很久远的事情,距今也就200年;而今日之中国,已再度崛起,那这200年的衰退期,在世界文明史上算是很短的现象。总之,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反而给中国描述了一个可堪回首的往事。我们对历史,不应抱持那种苦大仇深的态度,我们有理由更加自信。
所谓“闭关锁国”
对过去500年历史的误读,可能跟历史教科书里面那句多少带着情绪的“闭关锁国”的评语有关。
近代中国历史是以西方为参照写的,所以,观念里头似乎有一种“人家的历史”如何如何好的预设。
所以当西方人到处殖民掠夺时,我们就无比痛恨中国的“闭关锁国”。但中国真的闭关锁国了吗?
事实显然不是。孔飞力认为,中国尽管一度有海禁,但海禁的效果并不明显。海禁就是禁止民间海上贸易,但海禁时期,往往走私猖獗。这种走私一度发展为走私“集团”。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中国的海禁并不是持续不变的国策,而是有时海禁,有时又废除海禁。近500年的历史谈不上“闭关锁国”。
比如,明朝前期的朱棣时代并无海禁。还有官方组织的郑和下西洋。但郑和之后,明朝开始搞海禁。这一海禁持续了100年,直到1567年被废止。
1567年是《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关键的年份,这一年朝廷废除海禁,孔飞力借此认为,这是中国近代移民史的开端。
关于历史的划分,我们习惯于把1840年视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但在移民史的研究里面,孔飞力则把中国“近代史”提前了273年。孔飞力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他认为,海禁废止的时间正好也是西方殖民者抵达东南亚的时间。此后,中国通过东南亚的移民进一步融入了世界。而这个时期也正是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全球化”的开端,可以说世界近代史的开启跟中国近代史也几乎同步。
孔飞力的这种颠覆性的说法,再次提醒我们中国并不孤立于世界,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中国一直在场。
继续说海禁。清朝初年,也实行了海禁。海禁的原因跟明朝相似,都涉及到国家安全。明朝是因为蒙古的入侵,战略重点从海上转移,而清朝则是前明的残余势力盘踞海上,不得不实行严格的海禁以断绝他们的生路。
清朝初年的海禁持续了30年,1684年,占据台湾的郑成功的后人,投降清政府,海禁也随之废除。
不过,“闭关锁国”虽然全不是事实,但也不能矫枉过正,高估历代统治者对海外贸易、海外移民的友好程度。事实上,1567年之后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对海外贸易,尤其是在海外做生意、并常驻海外的中国人有很深的偏见。这种偏见,就像在东南亚的欧洲殖民者对华人的偏见一样,怀疑他们对自身安全构成威胁。
1727年,雍正皇帝就说过这样的话:“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说他们“不安分”,算是打官腔,实际的意思是,这些人不得不防,小心他们跟“番夷”勾结。
所以朝廷规定,去海外做生意不能停留超过2年以上,超过就要严加处罚。“跨国流动就被贴上了不忠不孝的标签。”孔飞力做了精辟的概括。
国家从来不鼓励民间去跟欧洲人竞争,甚至对那些衣锦还乡的南洋华人加以苛责。历代统治者欠那些在海外夹缝中生存,但依然心系祖国的华人一个道歉。这个道歉来得太迟,直到1893年,清朝已经风雨飘摇了,朝廷才正式豁除海外华人的污名。
打工者的历史
孔飞力的中国近现代海外移民史,换一个角度也是出国打工者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历史上那些海外移民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找不到出路,不得不去南洋(东南亚)、北美这样的广阔世界寻求生计的普通人。
这些人跟今天的外出务工者并无太大区别,不同的是,跨越的文化差异更大。所以,孔飞力说他们是生活在“他者”中间,而也唯有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才让这个群体为了保护自己,自发形成一种对抗性的组织和文化。今天北美的“唐人街”,比中国还更“中国”,就是明证。
所以,近500年来海外移民的原因,跟今天乡村外出务工者大体相似。都是劳动力富余,而土地的产出又不能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当然,明朝还有特殊情况,就是户籍制度有调整,住户可以流动。这个情形用今天熟悉的语言,也是国家层面的“改革开放”,地方和民间由此逐步有了活力。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海外移民,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而主要的移民原因就是解决生计。当然,这期间也有其他一些比较罕见的移民现象,那就是政治难民。这在改朝换代之际比较突出。
另外有一类政治难民,并非平民,而是前朝的军人。在越南南部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是南明(明朝灭亡后,朱家后人建立的短暂的政权)的残军。这类现象,1949年后又再度出现,也是东南亚移民研究不容忽略的。
把《他者中的华人》放在打工者的语境下理解,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农村问题,或许会有启发。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农村的青壮年人口都离开村子到周边城镇,乃至更远的地方谋求生计。这个打工潮流,跟历史上那些去异域“淘金”一族很相似,都是普通劳动者,都对家庭、家乡有朴素的感情。
孔飞力的移民历史的研究提醒我们,只要乡村社会的组织和文化没有被铲除,外出工作,乃至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就不会真正走远,他们会回来,会用他们的方式回来,乡村某种程度的凋敝或许只是短暂的现象。
此外,正如海外移民为中国融入世界所做的贡献一样,今天离乡背井的普通劳动者,同样有未来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 赵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