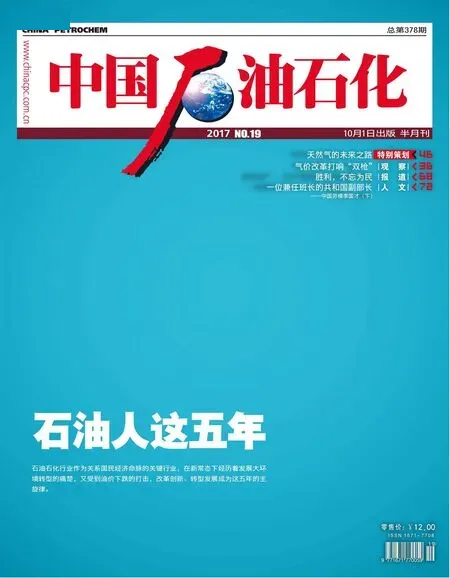一位兼任班长的共和国副部长—中国劳模李国才(下)
○ 文/于万夫
人文
一位兼任班长的共和国副部长—中国劳模李国才(下)
○ 文/于万夫

1975年初,43岁的李国才,奉命进京,出任石油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舍不得 留不住
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全班人齐刷刷地都到了,比往常隆重,就像班里有重要意义的大活儿派下来了似的。
李国才一声不吱地坐在那里,全班36人,一个不缺。他过电影似的,挨个瞅着这帮弟兄,不由自主,眼睛有些潮湿了。
副班长包庆洪把李师傅要调走的事儿说了,然后郑重其事地宣布:下面请李师傅讲话。
没人鼓掌,人们在突如其来的惊愕里还没缓过神来。
李国才站了起来,瞅一会儿,然后充满深情地说:“伙计们,我要走了!我是陪伴你们十几年的老班长,跟着我,你们没少遭罪,星期天,节假日,谁闲着过?咱加工班这点家底,不容易,是大伙的汗哪,一滴一滴的汗哪!我时常感到心里有愧,荣誉都让我一个人得了,活儿是大家干的,真的,不是挑好听的说。加工班里每一人都是好样的,当劳模都够料!”
说到这儿他确实感到愧疚,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忘不了这个班,我忘不了大家伙,一有空儿我就回来。你们到了北京,不管私事还是公出,别忘了去看看我。我没什么文化,当个班长还多亏了有你们大家的帮衬。到了北京,如果干不出什么名堂,我没地方去,指不定还得回咱这个老窝!”
这回掌声响起来,老班长要走了,真的要走了!
“有一件事,我得托付给大伙儿。我走以后,这个班不能散了心,一定比我在的时候更好,好上加好。早出晚归,辛辛苦苦的老传统不能丢了。冬天,下雪了,遵义路上的第一趟脚印,永远得是咱加工班的人踩出来的!”
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个掌声是表态,是请老班长放心明确而清晰地表态。
“国才,你放心吧,加工班这面旗倒不了!”包庆洪老师傅激动得站起来了。
舍不得,留不住,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北京,石油化学工业部。
李国才还没进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厅主任带他去见康世恩部长。
起身握手,也没有什么客套话,两人就坐在了会议桌前。康世恩给李国才鼓劲儿,相信他不会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
康部长说,你兼任的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吉林市革委会副主任、吉林市总工会主任等职务都要辞掉。管道加工班班长可以兼着,不用交出去。
“好,好,我就等部长这句话!”听了这个安排,李国才由衷地高兴。

●1975年冬天,时任石油化工部副部长的李国才(前中)在辽河油田高升采油厂,用他的高压锅炉热采稠油获得成功。
“只要能脱离开,你随时都可以回加工班干活,当你的班长。石油化工部这边,部长分工想把机械制造和物资供应这两摊交给你,你看行不行?”
“就怕干不明白,辜负了组织上的期望。”李国才说的是心里话。
虽然康世恩同意他继续“兼任班长”的这个安排有点出乎意料,但让李国才感到踏实。这是组织上对他的理解,对他的“特殊关照”。几天来,他一直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地了。
真的,经历了这么一次,他才实实在在认识到,我李国才离不开加工班,离不开那帮老伙计,离不开那忙忙碌碌、没完没了、总也干不完的活儿。
时代把他推上了这个舞台。干得了,干不了,他都没有选择。他必须在这个舞台上,经受并面对未来的挑战。
李国才必须在康世恩面前,在其他几位副部长、老干部面前,认真完成角色转换的艰巨任务。
在石油化学工业部干部大会上,李国才不能不说,应该也必须有个表态。他讲的不多,实在而又中肯:“大家都知道,我就是一个工人,一个在第一线干活、只念过3年书的工人。组织上给了我这么重要的岗位,让我当副部长,真怕干不了。在30多人的加工班当班长还行,当副部长有点太抬举我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试试吧,反正来的时候老伴说了,干不了赶紧回去。”
一阵笑声,紧接着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李国才起身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当副部长的5年间,只要不在吉林,李国才几乎是一天一个电话,从没间断过与加工班的联系。特别是班里的一些大活儿、难活儿,接不接,怎么干,加工班都听班长的。工资关系也在管道加工班,每个月都是妻子去领他八级工那102.20元,部里每月补贴50元,在北京的生活费基本够用了。

●1960年,李国才应邀到工厂做事迹报告。
任上22项成果
1970年开始大规模勘探开发的辽河油田,是个贮藏量很大、有前景、有潜力、有希望的大油田,但关键是无法解决稠油开采的难题。辽河油田的高升采油厂,打了十几口井,就是不出油,油层挺厚,但黏度达到了4000厘泊。
当时中国的采油技术也不行,装备落后。请来几位美国专家考察后认为,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往地下注入蒸汽,理论上讲升温后应该能将稠油开采出来。但是高升油田井深1600多米,这么深的井,美国的热采锅炉到了中国能不能行?没有把握。
这是个难题,石油企业的世界性难题,美国也不例外。
康世恩部长亲自来到盘锦,在幅员辽阔的油田,走了几个采油厂,看了几口井,确实感到是个棘手的难题。
明明知道脚底下就是财富,就是油海,却弄不出来,让人束手无策。
作为中国石油的掌门人,“稠油开采”的难题康世恩并不陌生。位于山东省北部黄河三角洲地区,属于东营市的孤岛镇,有个全国最大的三级构造油气田。1967年勘探,1971年投入开发。孤岛油田是受构造控制的层状油气藏,埋藏深度为1120~1350米,原油性质较差,为高密度、高黏度的沥青基石油。
采油厂从武汉锅炉厂购进了4台高压注气锅炉,用了没几天就烧坏了,不但没喷出油来,锅炉也坏得无法修复。
康世恩部长视察孤岛,提出让他们到吉林,去找吉化的李国才,看他有没有办法?
这是1974年末的事情。李国才还没有副部长的身份。
今天面对辽河的难题,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康世恩这次亲自找到了李国才:“我记得你造过锅炉,能不能造一台150个压力的热采锅炉,让辽河的稠油喷出来?”
这已经是首长第二次下达研制“热采锅炉”的指令了。李国才立刻有了“军令如山”的压力。
在把山东孤岛锅炉的制造进度和情况向康部长做了详尽汇报的同时,李国才强调了其中的难度:“我造过锅炉,只干过13个压力的生活用锅炉,没造过高压锅炉,更别说150个压力了。”
康世恩说:“咱们中国地下有4亿吨稠油,要能日产200吨就行啊。”
部长的石油梦,就是支撑李国才的动力源。他立即回到吉林,回到他的加工班,用了3个月时间,主持制造了一台试验压力700公斤、运行压力450公斤的高压热采锅炉。
长途跋涉,半夜11点,这台锅炉运到辽河油田高升采油厂,在连续向地下注气一天一宿之后,原油开始箭似的喷涌出来。
这口滴油不产的井,创下平均日产76吨的纪录。
辽河油田的领导兴奋地说:“李副部长,赶快回去,给我们多造几台锅炉,就要这样的。”
李国才加工班一口气给辽河油田造了20台锅炉,总共花了不到30万元。
据辽河油田统计,20台锅炉,共产稠油37.1379万吨。
任丘油田位于冀中大平原风景秀丽的白洋淀畔。1975年7月,任丘西南辛中驿附近的任四井喷出高产油流,日产达1014吨。这口井喷油,不仅宣告任丘古潜山油田的诞生,而且从此结束了河北省不产石油的历史。经国务院批准,一场有3万人参加的冀中地区石油大会战拉开帷幕。
然而,古潜山的地质特性决定了岩层的硬度太大,当时钻井使用的苏式钻头,打不上4米轴承就研碎了。换一次钻头,需要一个星期。
钻头,硬生生地挡在那里,成了会战的拦路虎。
余秋里、康世恩亲自出面,召集石油化工部、一机部相关领导和专家,专门就“钻头问题”在任丘开了现场会。
散会后,李国才找到康世恩,揽下了这桩咬手的活儿。石油化工部“钻头攻关组”成立,组长由副部长李国才担任。
从北京,到上海,到成都,到任丘,为了钻头的“中国制造”, 李国才事无巨细地奔波,试了改,改了试,钻井深度从4米,到29米,到90米,到540米,终于实现了追赶“休斯敦”的目标。
有人统计过,1975年至1980年,在石油化学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任内5年,李国才先后取得22项技术革新成果。
副部长,班长,22项技术革新成果,这些本来完全没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却是李国才5年“高官”人生的主题词。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李国才和他的“大口径合金钢高压弯头”受到表彰。
疾风知劲草
当副部长已经五年,李国才一直在北京六铺炕石油部的干校楼住独身,一个标准间。1980年夏天,化工部在和平里化工大院分配给他的一套116平方米的房子,李国才在搬家的同时,人事工资关系也从吉林办到了北京。
根据职工考核三项条件,经群众评议,李国才由“建安”八级升为“超八级”,工资晋升至118.40元。
就在这个时侯,摊上事儿了,他突然被推上“被告席”。
早在1979年1月,吉林省主管锅炉的行政部门以“文件”形式,向国家主管部门报告说:李国才的锅炉从设计制造到安装使用,均没按《蒸汽锅炉安全监察规程》第二章的规定履行批准手续和进行技术鉴定。这种锅炉不仅使国家浪费了大量钢材、煤炭,而且给有关部门在锅炉安全管理工作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使我省的锅炉安全监察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使党的事业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1979年3月,国家主管锅炉部门主办的—本杂志以“读者来信”形式,把锅炉问题的分歧和争斗公之于众。
恰在此时,中国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渤海2号”沉船事件,这给当时的石油工业带来了极大冲击。1980年8月,国务院做出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上任不到两年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去部长职务;主管石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处分。
1980年9月,首都两家大报,接连发表《立即停制“国才式锅炉”》 《李国才弄虚作假专横跋扈》的消息和报道,文章在把李国才定位为“造反派”的同时,全面否定李国才的业绩与贡献,否定他的政治品质。
面对舆论的压力,李国才被解除了化工部副部长职务。
就在停职反省期间,有一天,浙江来了五六个同志敲开了李国才的家门。
位于中国浙江海盐县秦山镇,被誉为“国之光荣”的秦山核电站,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和运营管理的第一座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这座电站的建设,使中国成为继美、英、法、俄、加拿大、瑞典之后,世界上第七个能够自行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
为了压制核反应堆“直径890毫米,壁厚90毫米”主管线的弯头,建设者不得不找上门来。正在“停职反省”的李国才知道,这是决不能含糊的国家大事,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水压机的操作,到内外胎具制造,李国才帮助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者,创造了“非焊接、冷压一次成型、最大型号”不锈钢弯管的世界之最。
最美不过夕阳红
中央对李国才的问题很重视。化学工业部会同吉林省、吉林市对李国才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而全面的调查与核实,推翻了“假劳模”“造反派”等不实之词,并认为1954年参加吉林“三大化”建设开始到1980年“副部长”任上的20多年,他先后实现技术革新189项。他用自己扎扎实实的努力和奉献,为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国才的事迹与荣誉相符,是实事求是的。
1983年7月,李国才被任命为化学工业部中国化工装备副总工程师,“副局级”待遇。
坐落于山西省长治市潞城镇的山西化肥厂,是我国引进德国、日本、挪威技术的第一套以煤为原料,年产合成氨36万吨、硝酸54万吨、硝酸磷肥90万吨的大型现代化复合肥料厂。但那里的生产始终不正常,停车事故频发,化工部部长秦仲达把李国才派了过去。

●李国才的高压锅炉在辽河油田高升采油厂。
问题确实不少,有管理问题,也有设备问题。就拿带式过滤机来说,不到1毫米厚的过滤带,说坏就坏,坏了就停,成了生产流程上的薄弱环节。
李国才从仓库里领了一桶胶水。星期日,员工休息,他挽起袖子,操起刷子,把胶水认真仔细地涂在过滤带的两边,凉一会儿,再涂一遍,一共涂了7层,挺厚,挺涩,不打滑了。就是这么一个“土”得不能再土的办法,运行起来却大不一样了,过滤带竟破天荒的一整天没有坏。第二天,第三天也没坏,经受了考验,使住了。
煤气发生炉是从德国引进的,经常出现水管堵塞现象,水泵使不住,用不上几天就报废了。李国才设计了一个不怕腐蚀,不怕杂物,吞吐自如的长脖泵,25千瓦,2890转,真空密封轴,每小时排粉渣灰水500吨,困扰生产的又一个“老大难”解决了。
接着,他又解决了运送原料煤的传输管道与震动筛堵塞,挪威制造的不锈钢取样器用“中国制造”取代等一系列问题。
1989年9月,在被授予“化学工业劳动模范”称号之后,李国才又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1963年,1979年,他两次被授予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但作为“全国劳动模范”这还是第一次。
不少人,包括一些官方人士,劝他为自己的革新成果申办专利。但李国才挺犟:“谁用我的发明都可以,谁用我的技术都可以,谁有课题找我进行新的‘工业嫁接’更可以。只要我的发明和技术能让一个企业走出困境,我就万分高兴。到死,我也不会拿着我的‘专利’去换钞票。”
一个人一个活法儿。李国才这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不管对与不对,反正他觉得这样活着舒坦。
1993年2月,李国才应该退休了。
退 休 前,1992年12月,他做出了一个“破例”的决定:给“锅炉”申请专利。1993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把印有国家专利局国徽印章,有局长高卢麟签字的第137245号“实用新型专利证书”郑重颁发给他。
就在李国才取得专利证书,张罗退休回家的时候,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出版社隆重推出一部装祯精美,有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国家副主席王震题词的《中国劳模》一书。
这部巨著的第一卷第一页第一人,就是李国才。
点 评
工匠普通 需要呵护
历史就是历史。它是走过的路。李国才是时代造就的人物。他足足当了十年“领导”, 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领导”。生活简简单单,工作勤勤恳恳。他已经尽力了。即便有错,也是那个时代的错误,那个时代许多人甚至所有人都犯过的错误。
李国才是伴随新中国,同国有企业一起成长、成熟、成功的“超八级”工匠,著名劳动模范。他的故事,是发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故事,是一个与新中国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功勋卓著的劳动者“一辈子”的故事,是能给读者带来“思考和启发”的中国故事。
不论工匠,还是劳模,或者普通人,每个人的成长与命运都离不开时代,离不开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经典,作为最活跃、最先进的生产力,活跃在生产建设第一线的劳模、工匠,他们很普通也很特殊,不仅需要认可、宣传,而且需要珍惜、呵护。
本文照片均由闫若谷提供
责任编辑:陈尔东znchenerd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