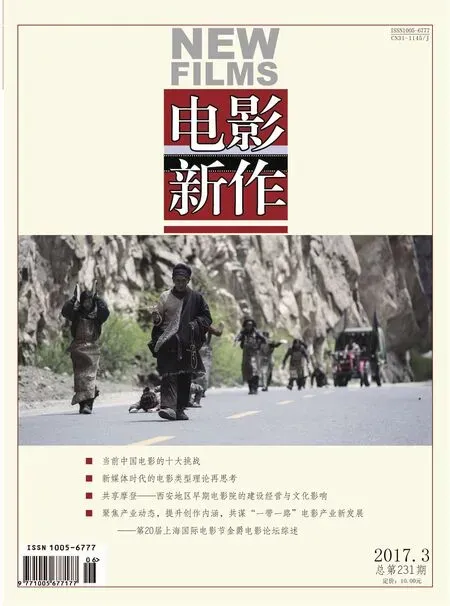作者风格的突围
——法斯宾德家庭情节剧的对位研究
甘 琳
作者风格的突围
——法斯宾德家庭情节剧的对位研究
甘 琳
家庭情节剧属于对日常生活做出最敏感回应的类型电影,能够在一直以来的类型进化中贯通着世俗和文化的发展变化。作为一位具有强烈作者风格的导演,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在自己细腻风俗画的家庭情节剧创作中没有囿于类型片满载叙事惯例的刻板语境中,反而在对位的突围中进一步扩大了家庭情节剧的表现范畴。
家庭情节剧 复调对位 空间叙事
为了纪念德国电影大师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逝世35周年,2017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大师致敬”的经典放映单元放映了6部法斯宾德的经典电影作品,6部中占半数以上的家庭情节剧类型片成为该影展单元的焦点。相对于同时期“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其他导演,法斯宾德拥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和商业的双重成功。告别了早期《爱比死更冷》和《外籍工人》等固定镜头和极简风格的尝试后,法斯宾德开始师承德裔导演道格拉斯·塞克的家庭情节剧的类型模式,“我认为我先前所言的为大众拍片的时机到了”①。从《四季商人》开始,法斯宾德电影中视觉设计的密度有了技巧性的提高,极简主义不再成为唯一的出路,风格转向后的通俗剧情拉近了他与普通大众的距离。然而,有意识的空间和叙事策略又没有让他笔下的家庭情节剧情堕落为“矫揉造作”的廉价,反而和传统的家庭情节剧达成了一种对位式的复调和突围。
对位法本是指复调音乐创造中,多条相互独立的旋律相互发声并彼此结合的创作技法。二十世纪初,现代西方音乐为了摆脱“旋律-和声”风格的主调和弦音乐的包围,大量创新了横向线条的复调对位音乐,以此形成的不协和对位反而让发源于传统的“复调”风格音乐能够在“个性写作”的基础上迸发出新的火花。本文将借助音乐术语中的这一“对位”概念,以影片中空间和叙事的互为替补为切入点,分析法斯宾德家庭情节剧在对观众文化心理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对传统家庭情节剧规范体系的适应以及颠覆。
一、转换绝境的意义
为了制造出皆大欢喜的结局,家庭情节剧往往会在最后把所有的线索收集起来,所有的走投无路都会被不可控的力量解救。这种大团圆的设定可以追溯到欧里庇得斯的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会将自己故事的剧情推动到极限之后,才让神离开宝座,出面搞定一切”②,原本被压缩逼仄到极限的叙事空间在结尾被“及时解围”(deus exmachina)。结局时间的紧迫感反而催生了一种均质而广延的形式上的叙事策略,它如接口一般缝合了前后叙事链条,使得角色在所处的结局空间里得到了最大的舒展。
道格拉斯·塞克在他的《地老天荒不了情》以及《深锁春光一院愁》等影片里曾堪称完美地运用这种“表面快乐”的反讽结局。在塞克电影里,反讽的现实越是愁苦,虚妄的快乐结局反而愈加彰显。日常生活的界限隔离在幻想的幸福外,剧中人物与观众的幻想内核产生了叙事上的重叠,这也是家庭情节剧在类型框架里对现实意识形态的裂痕进行的一种修补。

图1.《恐惧吞噬灵魂》
然而,法斯宾德并没有认同家庭情节剧里的这种虚假修补态势,个人失败和核心家庭的解体经常被咆哮式地处置给观众,绝境没有被解围,或者说,被解决得并不彻底。《恐惧吞噬灵魂》的结局里,外籍工人阿里因胃溃疡而病倒不支,打破了之前剧情里过于“挑衅般简单”的故事设定。“如此结局的用意,当然是将这个我疯狂喜欢,也非常看重的故事,临门一脚地踢进现实以及观者的脑海里。”③好不容易既抵御了外辱,最终达成共识的阿里和艾米最终被无法治愈的胃溃疡偷袭,现实才是一剂真正的猛药。《恐惧吞噬灵魂》里胃溃疡被告知为是外籍工人常有的症状,而《深锁春光一院愁》里的坠崖是无法控制的力量的耦合。《恐惧吞噬灵魂》里的疾病隐喻显示出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失调,社会被看做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和失衡。疾病变成了一种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内在自我的发泄。对意识形态的修补不再成为传统家庭情节剧中绝境的意义,编织出“无法解决”的绝境的现实意义才是法斯宾德的家庭情节剧的深层叙事轨迹和目标。
并且,法斯宾德绝境意义的转换也经常带有政治话语的并置。《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的结尾,由瓦斯炉引发的致命爆炸混合了收音机洋洋得意地宣告,联邦德国赢得了世界杯冠军的消息,随即银幕上出现了阿登纳、艾哈德和施密特等战后执政者交替的面孔。玛丽娅个体无意识的衰败与国家的表面繁荣形成了行动上的互文阻碍:玛丽娅在丈夫入狱期间证明了自己卓越的社会谋生能力,最后却绝望发现自己的一切作为不过是两个男人间的筹码,玛丽娅并不能从理想所依赖的社会形势那获得她完全期待的自主和行动性。德国战后社会基于自治个体的理想主义观念由于权威主义的习性作祟而无从发泄。同时,拒不屈服的集体意识只能从生活中抽身出来(玛丽娅的自杀),而不是改变之,德国银幕中人物命运的衰落即民众普遍内心麻痹的反映。绝境没有获得转机,反而被转换成时代体认下的揭露,时代陷入嘲讽自身的困境中,法斯宾德意欲用结局中生命力的瘫痪来召唤出在类型框架中被抛弃的真正的现实经验。
二、虚假的行动释放
“传统家庭情节剧的叙事核心是寻找理想的丈夫或理想的父亲,女性的困境在于没有经济安全感,也无处宣泄情感诉求。”④从属于挫败的焦虑和压抑成为家庭情节剧中的女性甚至部分男性角色所一贯面对的嘲弄,为了化解这些嘲弄,传统家庭情节剧中的角色往往会生发出一系列“无意识的自由行为”,试图解锁家庭对其的困扰和桎梏。
同样地,法斯宾德也对自己电影中的人物角色注入了一种毫不动摇的独一无二的冲动来迎接家庭情节剧关于“无意识自由行为”所营造的极端情感的快意。他尽量最大化地释放角色,尤其是女性角色的行动面向,尤其当电影的历史语境被放置到战争中时,女性甚至可以成为拯救性质的决定性人物。主角们在故事中或许能成功干出一番事业,或许能寻找到理想的伴侣,或许能通过纯粹的牺牲而成全世俗生活的意义,只要摧毁了来自外部的敌人威胁,而不是基于内在的分裂主体,便能在欣慰的幻觉中理直气壮。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就能够在这种被类型框架所刻意安置的“无意识的自由行为”中获得银幕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位移。
在第三帝国的政权统治下,《莉莉·玛莲》的女主人公薇莉的恋人是瑞士籍犹太地下组织成员,而自己却是一个为纳粹德国唱歌的歌手,她非常清楚自己要活下来,并且是以一个艺术家亟待出头的需求活下来。在个人和国族的离散里,法斯宾德妥善地编排薇莉的行动,我们总是能在景框中看到薇莉以一种“奔跑”的姿态践行自己的“无意识的自由行为”。战争中,女性固然有她们的角色,但若要打破角色定位或脱离轨道可容易得多;倘若是男性,则立刻被冠上逃兵之类的罪行。所以,法斯宾德把所有关于政治、社会和情感的幻想都移植到了薇莉身上,这个角色似乎前所未有地被赋予了最大化的行动性。然而,在叙事切面之外,这种最大化的“无意识的自由行为”反而在空间中被反讽和消解了,行动成为一种假设和过渡。
当希特勒为了接近薇莉而赐赠给她一座高档公寓时,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摄影机运动的异样。薇莉在公寓内巡视,不像之前大多是快速的推拉镜头,摄影机一气呵成以一个一分半的长镜头追随薇莉运动,形成了薇莉能够自主运动的假象。在即将绕回原地的长镜头的最后,薇莉在镜子前停留一会儿,她企图通过镜像之物确认自我和时空的可行性。对于纳粹政权的橄榄枝,她不愿主动做出抉择,她滞留在此,在这个圆形轨道里,她的进退皆是无效的,她求助于镜中虚像,期待被回忆之物(恋人罗伯特)能在虚像中显现出来并将她拔离出这个分裂的现实中。
在这个回旋的长镜头里,薇莉又回到了原点甚至可以说她进一步退化了,她之前所有行动的释放、自由的意识行为都似乎并没有在这段运动镜头中得到认可。成功的事业、理想的伴侣这些类型框架中一一用来移置观众幻想的元素既证明了女性角色的行动迸发,恰恰也成为其被动属性的征兆,战争给予女性逃离轨道的机会只是一个行动的假象,女性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战争的过渡”,女性依旧要面对家庭伦理之核的嘲弄。
回归到战争外的日常生活的隐喻,法斯宾德在《卡斯特婆婆升天记》里更加深刻地反思了女性行动在家庭情节剧中的有效性限度,并得出了嘲讽的结果:女性被捆绑在厨房和家庭的桎梏中,潜移默化地被剥离了真正自主行动的意义。在丈夫去世后,卡斯特借着强烈的倾诉欲走出厨房接触社会公共空间,但是法斯宾德却给她安置了一个最微小也是最具隐喻意义的行动符号:影片中的卡斯特从头到尾一直在重复手工作坊工作中把圆形零件拧入方形元件的视觉效应。所有交往理性的过程都附属着这个动作,他和儿子的对话大都是在组装零件的过程中完成,无政府主义者拜访她时,她仍然在组装零件。这个内容上的复调,隐喻着资本对庸常家庭的入侵,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公共领域里反而无法适从,身份逐渐被模糊和失焦。在法斯宾德的家庭情节剧里,女性的行为释放一方面可以无限可能,另一方面又被空间框化为近乎无效,行动被横向瓦解成多个可供解读的对位面向,这种游移多变的诡谲含混与二十世纪后音乐创作中的“横向无忌对位”不谋而合:音乐中音与音的关系无须遵从不协和解决到协和的进行规则;电影中,类型与类型的叙事变奏也可以交织着对抗与补充。

图2.《中国轮盘》
三、根基于表现主义的视觉传统
一战前后,摄影机首先在德国彻底实现了灵活性,电影中具有表现主义特质的运动镜头以及各种棚内搭建的夸张变形造型揭示了德国人在几乎无法触及的精神层面的危机,他们在这场绝无仅有的内心独白中意欲逃离外部世界。“一旦德国人决意为灵魂寻找庇护所,他们就根本不允许银幕去探索已被他们抛弃的那个现实。”⑤被中产阶级把持的电影行业害怕效仿社会主义者那样将观念和心理体验的问题追溯到经济和社会的起因上去,所以,一战前后,表现主义在德国电影业的繁荣更像是中产阶级以原始感官和体验的塑造为由的,对社会进行心理麻痹的一个隐晦手段。
法斯宾德的《萝拉》是对冯·斯登堡《蓝天使》的经典翻拍,这部有力地重祭战后表现主义视觉传统的影片,承袭了斯登堡对德国人心理面貌的讽刺和批判,清楚地阐明了二战后德国社会堕落腐化的一面。《萝拉》中大量运用了红、蓝、绿等非自然光线。萝拉和冯·伯恩坐在汽车里准备结束一天的约会,冷色调的蓝光包裹着冯·伯恩,暖色的红光映衬着萝拉的热情,蓝红两色将一个密闭的空间进一步分割,二人身份的非现实的割裂感充斥屏幕。
种种舞台效果般的表现主义视觉调度一扫传统情节剧平实而温和的视觉范式,在平滑中对光线进行了一次疏离的浮动和反拨,突兀的感官体验对位出了极强的社会诉求——战后50年代的德国,阿登纳领导之下的快速而充满隐患的经济奇迹所建立的权力结构正不断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法斯宾德在自己的家庭情节剧中所植入的超乎现实的表现主义视觉元素与传统情节剧中基于人为性虚假而刻板化的视觉布景在结果上看来,都是“影像模拟”对“现实真实”的一种偏离,不过,这两种非单一统合性的视觉考量并没用形成简单的依附和排斥关系。
正如勋伯格所说:“在泛音列中,不协和只是在泛音列中相隔较远的协和。”⑥音乐中的“不协和”将对位中的音高或声部分离并相互对立,并使一条旋律更加明显地衬托出另一条旋律;而在家庭情节剧电影的类型框架中,表现主义元素的差异化形塑反而成为传统家庭情节剧自觉暴露叙事可能性的新的尝试:表现主义不再成为麻痹阐释的借口,反而可以挑拨传统家庭情节剧中虚假真实的反动,高反差的色彩和情绪化的布光可以代替中产阶级客厅里光鲜的平光布置,关于社会现象的意识反思更容易被极端的形式感启发而不是刻意“正常化”的视觉模拟。表现主义的舞台光线正好成为伯恩“个人正直和政治漠然”的混合体的体现,重要的不是异议分子如何改造世界,而变成了社会如何成功吸收异议分子。
为了进一步扩大表现主义在家庭情节剧中的实际作用,法斯宾德创作的《中国轮盘》甚至直接放弃了情节剧中“借助演员来说故事”的叙事模式,叙事的推动完全依靠摄影机的旋转、推拉和升降。当“中国轮盘”的游戏结束后,安娜无法忍受女儿对自己的残忍与鄙夷,她射杀了被女儿视为“真正母亲”的家庭教师。丈夫与安娜在镜头前不停地反向运动,调整出一系列回避与介入的身体动作,摄影机由内向外一边360°围绕夫妇二人,一边扫视整个格哈德家的客厅。中产阶级客厅里的隔阂和极尽造作在这个突如其来的运动镜头里显露无遗。女儿与母亲的绝望关系粉碎了二战后德国资产阶级坚信的人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和自然关系的传统。女儿将母亲视为“二战期间贝尔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夫妻两人各自心怀鬼胎出轨,所有家庭情节剧中本该通过廉价通俗的冲突叙事操持的人物关系被表现主义中眩晕的运动所代替,镜头直接映现了事物活动痕迹的指标符号,镜头和原本事物形成了直接的物质性联系。
结语
法斯宾德之所以能够成为德国“新电影运动”的心脏,一方面在于他混合着传奇人生的电影经验,另一方面就在于他作者属性的标签对传统家庭情节剧的赋格逃离与变调。转换绝境的意义、混沌人物叙事的行动力,以及表现主义的加持,都让法斯宾德的家庭情节剧电影如一曲演奏着的对位复调音乐,电影的表层结构与传统家庭情节剧看似具有无逻辑和无序的关系,但是深层结构里关于家庭内核的“离题”与“切题”又能在突围中完成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让“家庭”与“情节剧”这两个几乎固态化的传统议题展开出新的维度。
【注释】
①[德]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法斯宾德论电影[M].林芳如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43.
②[英]乔·哈利戴.塞克论塞克[M].张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3.
③[德]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法斯宾德论电影[M].林芳如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55.
④杨远婴.家之寓言——中日美家庭情节剧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5.
⑤[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史[M].黎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1.
⑥[美]约瑟夫·马克利斯.西方音乐欣赏[M].刘可希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530.
甘琳,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