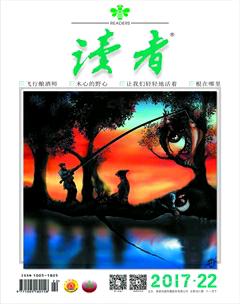自由之地
〔日〕村上春树++施小炜 译
说句真心话,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对学业不太擅长。倒不是成绩糟糕透顶的差生,成绩嘛,也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只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学习,实际上也不怎么用功。
为什么对学业不热心?理由非常简单,首先是因为学习太没意思,我很难从中感受到乐趣。换个说法就是,世上好多东西都比学校里的功课有意思。比如说读读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去海边游游泳,打打棒球,和猫咪玩玩;等到长大以后,又是跟朋友们通宵打麻将,又是跟女朋友约会……相比之下,学校里的功课就无聊得多了。
其次,对于跟别人争夺名次之类,我自小就提不起兴趣。倒不是我矫揉造作,什么分数啦、名次啦、偏差值啦,这类具体表现为数字的优劣评价很难吸引我。这只能说是与生俱来的性格了。
我属于那种对自己喜欢的事、感兴趣的事就要全神贯注追求到底的性格,绝不会说句“算了,我不干了”就半途而废,得做到心安理得才会停手。可对于我不感兴趣的事,做起来就不会太投入。或者应该说,怎么也生不出全神贯注的心情。
对体育运动也是如此。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对体育课厌恨至极。被逼着换上运动服、到操场上做一些根本就不想做的运动,令我痛苦难耐。所以有很长一段时期,我都以为自己不擅长体育。可是踏入社会之后,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尝试着运动,才发现运动原来是这么快乐的事啊!我眼前豁然一亮。那么,以前在学校做的那些运动究竟算什么呢?这样一想,不禁茫然若失。当然,人各有异,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但说得极端点,我甚至怀疑学校里的体育课,会不会就是为了让人讨厌体育才存在的。
如今想起来,在学校念书期間,最大的安慰就是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以及读了许多书。
说到书,我就像握着铁锨往熊熊燃烧的炭窑里乱铲乱投一般,一本又一本,如饥似渴地读过各种类型的书。单是一本本地品味和消化,每天就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为其他事胡思乱想。有时也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或许是好事。如果环顾自己周围的状况,认真思索那些不自然的现象、矛盾与欺瞒,直接去追究那些无法认同的事,我很可能会被逼入绝境,饱尝艰辛。
与此同时,我觉得通过涉猎各种类型的书,自己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而然地“相对化”了,这对于十多岁的我也有重大的意义。就是说,书中描写的种种感情,我差不多都感同身受地体验了一番,在想象中自由地穿梭于时间和空间之间,目睹了种种奇妙的风景,让种种语言穿过自己的身体。因此,我的视角多少变成复合型,并不单单立足于此刻的地点凝望世界,还能从稍稍离开一些的地方,相对客观地看看正在凝望世界的自己的模样。
假如我没读过那么多书,我的人生恐怕要比现在更加凄冷、更加贫瘠。对我而言,书籍就是一所学校,是一所为我量身定制的学校,我在其中学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那里既没有烦琐恼人的规则,也没有分数评价,更没有激烈的名次争夺,当然也没有校园欺凌。我能在“制度”的重重包围下,巧妙地设立另一种属于自己的“制度”。
我想象的“个人的恢复空间”,就是与此相近的东西,而且并不仅限于阅读。我想:那些无法顺利融入现实的学校制度的孩子,那些对课堂学习不感兴趣的孩子,如果能得到这种量身定制的“个人的恢复空间”,并且在那里找到适合自己、与自己相配的东西,按照自身的节奏去拓展这种可能性的话,大概就能顺利而自然地克服“制度之墙”。这需要家庭的支持。
我的父母都是语文老师,所以对我看书几乎没有一句怨言。尽管对我的学习成绩颇为不满,但他们从来没对我说过“别看什么书了,好好复习迎考”之类的话。
我对学校这种“制度”实在喜欢不起来。虽然遇见过几位好老师,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但几乎所有的课程对我而言都味同嚼蜡。在结束学校生活的那一刻,我甚至想,人生只怕再也不会这么枯燥乏味了吧——就是枯燥乏味到这种地步。但不管怎么想,在我们的人生中,枯燥乏味还是会络绎不绝,会毫不留情地从天上飘落而下,从地下喷涌而出。
可是,对学校喜欢得不得了、不能去上学心里就空落落的人,恐怕不大会成为小说家。因为小说家就是在脑袋里不断创造出只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人。比如我,在课堂上根本不好好听课,只顾沉溺在无穷无尽的空想中。
不管遇上怎样的时代,身处怎样的社会,想象力都拥有重大的意义。
能让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起来的,说到底还是孩子自己——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教学设备,更不会是什么教育方针。孩子们也不是人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就好比既有擅长奔跑的孩子,也有不擅长奔跑的孩子;既有想象力丰富的孩子,也有想象力称不上丰富,却会在其他方面才能优异的孩子。理所当然,这才是社会。
一旦“让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起来”成了规定的“目标”,那么这又将变成怪事一桩了。我寄望于学校的,只是“不要把孩子的想象力扼杀掉”,这样就足够了。
请为每一种个性提供生存的场所。这样一来,学校一定会变成更充实的自由之地。与之并行的,社会也能变成更充实的自由之地。
(李 峰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德〕海尼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