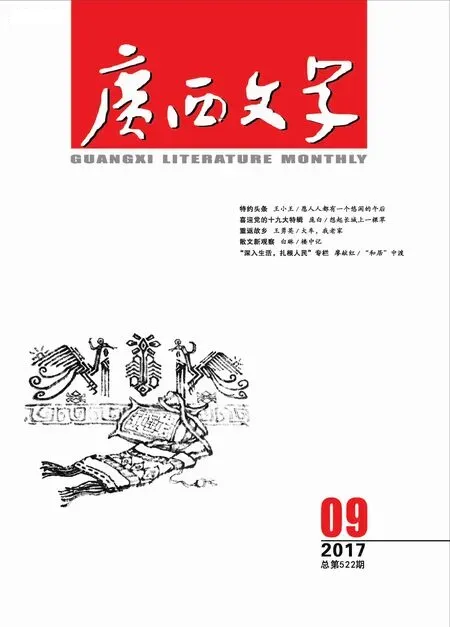漫游记
王小忠/著

1
和朋友约好要去色达——这个并不炎热的夏天,我一直在通钦街口等他。夏季到了末尾,他还没有来。在尘世,许多不曾想到的事时刻发生着,在电话里,他平静而祥和的语气中满带遗憾。我也就此放弃去色达,但并没有打消去草原的想法。家族很早以前都在草原上,所以我放不下草原,只有在草原上,才能感受到生命的自由和奔放,于是我只身去了遥远的草原。天阴沉沉的,太阳躲在云影里不肯出来。我的一脚踩着川主寺、松藩古城、九寨沟,另一脚踩着瓦切、红原、马尔康,双手指向川青线上的阿坝、达日、甘德、果洛……
公路在草原上像光芒四射的虹,把大山和茫茫草原阻隔的两地瞬间相连。四川、甘肃、青海的物产在这里相互交换,互惠互利。灰色的云渐渐变成片片绯红,蓝天露出了脸,路边牧人的帐篷和经幡又在眼前绚烂起来。帐篷前竖着酸奶、虫草、骑马的大招牌,选择以商辅牧已经成了牧民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我的朋友久美就在这里。久美是四川阿坝人,他一边放牧一边在草原上开商店,这样的日子已经好多年了。
和久美见面是很难的,这几年久美无论在牧业或生意上都很顺利,他有了自己的车,来回奔跑更加方便。认识久美的时候,他正值壮年。记得那年他们一家不远千里来甘南草原听经,我给他们拍了好多照片,并寄了过去。收到照片后他给我来电话,言辞里充满了感激。就那样来来往往,我们成了朋友。其间,我去过几回阿坝,可他再也没有来过甘南。
久美比前些年壮实了许多。我们坐在一起,他不大说话,但说起“草原人家”住宿点,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这是响应政府发展旅游业的号召,在草原上设点为游客提供方便,既赚钱,也算念嘛呢(是牧民群众每天必需的功课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一般牧民随身都带有念珠,一有空闲就数着念珠念嘛呢,为众生祈祷幸福)。草场承包到户了,每年都要严格谋划,根据草场面积和牧草长势留下合理的畜群,其他的全部出栏。幸亏道路通畅,既为游客提供了方便,也增加了收入的机会。
久美还说,夏天他几乎不去牧场,就喜欢天天看着公路。看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穿梭不停,心里就踏实。
路能帮助大家找到香巴拉,也是因为太多的人向往那仙境,所以路上才有那么多灵魂和白骨。久美重复着又讲起他阿米(藏语,爷爷)的故事来。
阿米曾经在茶马古道上做过背夫。马帮从四川雅安出发,经飞仙关,走天全,出禁门关,翻二郎山,过泸定,至康定,到西藏,然后把丝绸、布匹、茶叶、盐巴等东西驮回来。立起家业多不简单呀!
阿爸继续跟马帮穿草地,过雪山。直到有一年,同伴们把阿爸的马赶了回来。马上驮着小镜子、桃木梳子、手电筒、砖茶……唯独没有驮回阿爸。
阿米常说,去了禁门关,小命交由天。阿爸把命就交给那条艰辛的道路了。
听说要修路,无论在哪儿修,阿米总是要捐些钱的。在阿米心中藏着无数马帮和背夫无路可寻或遇到劫匪时的豪壮勇气和血泪情仇,也装着他们勇走天涯的无穷疾苦。
久美说起阿米的故事,往往是最动情的,他黝黑而深邃的脸颊上总会挂着泪珠。
正说话间,帐篷外有人大喊:“剁脑壳的!”
久美既惊喜又羞涩地笑着出去回了一句:“挨千锤的!”
这样称呼彼此,我是第一次听。我问他们,他们互相望了一眼,呵呵笑着,不给我解释。
“也不给我来个电话。”久美有些嗔怨。
那个大笑的女人说:“路这么好,我想来就来了。”
久美已经结婚了。当年他和我一样,只是个青涩少年。想不到短暂的几年光阴,大家都拥有了新的责任。有责任是温暖的,这份温暖和责任或许才是我们执意寻找香巴拉的真正源头。
午后时分,我离开久美的帐房,随他的妻子去了另外一片草原。
久美知道,我不是单纯来看他的。我要去深处的草原,寻找我要寻到的那些事物。
2
到了久美那边的牧场,我又见到了阿依(藏语,奶奶),和那年在甘南见到的情形一样:头发雪白,脸蛋泛红,满带慈祥。我给她拍过好多照片,她一见就认出了我,并用熟练的汉语问我家里的情况。
阿依不大习惯和久美住,一来不太方便,二来久美喜欢东奔西跑,按阿依的说法,久美是不安分放牧的孩子,是她心里的敌人。所以她和久美的妻子住在另一片牧场上,但她没有忘记久美,问长问短,全和久美有关。这片草原距离久美的住处相隔不是太远,然而这片草原相对安静点,住牧场的人不多,牛羊也很分散,帐篷更是星星点点。
阿依从一个小帐房里躬着身给我拿来糌粑和酥油,然后坐下来和我说话。
“草原上失去领地狗以后,人的麻烦就多了。”她一边说一边用宽大的袖筒擦了擦眼睛,“你看,这儿一群,那儿一帮,很难分出是谁家的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才发现,东一片西一片草地上的羊身上都涂满了红的、黑的、绿的、蓝的不同颜色,草原看起来像一张五彩缤纷的花毯子。
阿依继续说:“整个乱了,羊群不听人的使唤,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吃饱也不扎盘。”
我一边吃着酥油糌粑,一边认真听阿依的讲述。
“那时候,草原上狗很多。”阿依取过她的经轮,边摇边说,“狼群轻易不敢进栅栏,就算骚羊,也不敢随便进入别人家羊圈。早晨一打开栅栏,就不用人操心。领地狗在自家草原四周尿一泡尿,羊啃草啃到那儿就会自动回首。别人家的羊啃到那儿,也会自动调头的。都让那帮土匪给害了。”阿依说到这儿,便深深叹了口气。
“土匪?”草原上现在不会有土匪吧?
“不是吗?狗都让他们给悄悄贩光了。”阿依说。
“他们贩光了狗?”我还是没有明白。
阿依说:“挖矿的那帮土匪!草皮被破坏了,山都掏空了,这也就算了,可你说他们不好好挖矿,倒打起狗的主意来了。”
我似乎明白了一些。这里发现大量的金矿以后,的确驻扎了许多工程队。
阿依说:“他们成天在草原上转悠,是防不住的。”
我算是明白了,同时也想起人们热议的贩狗潮,可人家贩的都是藏獒呀!
“迷药,迷枪,麻袋,他们用尽各种办法。”阿依说到这里便不住擦眼睛,“草原上出了内贼,要不他们也很难下手的。现在草原乱了,人不如狗呀!”
阿依所要说的远远不止这些,也远远不止我所听到的这些。草原很显然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清洁和纯厚。当然,社会环境的变化无孔不入,人心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怎么能够保持住最初的那份本真呢。
领地狗的领地意识很强,一只狗能看好整片草原,人怎么能做到呢?况且,领地狗被贩卖后,失去生存的领地,它的领地意识就会渐渐丧失。这不是绝种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没有看到,当草原变成花地毯,领地开始出现混乱的趋势,战争就不远了。可惜更多的人只看到利益,不会想那么长远。人只会给自己制造烦恼,烦恼也是因为利益所驱动。这其间的复杂关系怎么能说得清楚?
住在阿依坚守的那片草原上,好几天时间里我都开心不起来,心里装满了阿依的那句话:“人不如狗呀!”
3
离开久美的另一座帐房,带着阿依做好的酥油糌粑,走着想着,我已经从南边的草地漫游到了空旷而硕大的玛曲草原上来。
几间空心砖垒起来的低矮的房子,四周挂着的哈达和经幡的颜色早已脱落,似乎有了好多年。房子左右两侧是用松木板扎起的一排排栅栏,栅栏里圈着牛羊……这方极为简陋的领地就是朋友的冬窝子。平日他们几乎不来这儿住,只有转场的时候才来,带上常用的生活器具,然后去别的地方。几只牦牛拴在栅栏边上,背上已经驮满了家当。三个脸庞黝黑的男人还在继续捆绑东西,我远远向他们打招呼。藏獒飞奔过来,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狂叫着。戴着毡帽的那个男人站起来,大声呵斥着藏獒。
戴着旧毡帽的那个男人就是我朋友贡巴,他们正在准备转场。高原上的夏季来得晚,这会儿他们要到高山牧场去放牧。另外两个是贡巴的朋友——拉毛扎西和阿班,他们在同一个牧场住了好多年,亲如一家。草原辽阔无边,但不允许你单枪匹马漫游。多少年来,他们踏遍雪山和草地,随牛羊东西漂泊,被狼群围堵却是常事。随草场承包和适度放牧制度的不断深入,牛羊渐渐少了,狼群也不见了影子,草原相比都市,显得十分孤独而寂寞。尽管如此,放牧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愿过于分散。
贡巴以前是民办教师,由于他阿爸去世得早,牛群发展又快,他不得不回家帮母亲和妻子放牧。拉毛扎西和阿班就在临近的牧场,是来帮贡巴转场的。贡巴说,他和妻子要离开贡赛尔喀木道,一直到深秋才回来,冬天再转回冬窝子。离开贡赛尔喀木道要经过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口,那里的风非常凶猛,需要朋友帮忙堵截大群牛羊,送过那个风口他们就回来。
贡巴以前没有说过转场的事情。
“山口的风有多厉害?”我问他。
他憨厚地笑了笑,慢慢给我说。
“四千多米的山口,夏天也冷得令人牙齿打架,人骑在马上随时都有被刮下来的可能,此时如果没有很多人围追堵截,牲畜就会顺着风跑,不会沿牧道走。牛犊和羊羔要夹在牧群中间,否则就会被刮跑。风来的时候往往会夹带着雷鸣闪电和倾盆大雨,十分吓人。牧群滞步不前,这时候就需要将牛羊收集在一块儿,等大风大雨过后再走。转场人太少是不行的。雨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只好取下牛背上的帐篷,各抓一角,遮掩在头顶上,要蹲下身子,不然会被大风带着飞起来。一旦飞起来乱石堆就成了墓地,不用举行啥仪式,全尸都保不住。”
贡巴讲得绘声绘色,我听着,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贡巴看了看我,微微笑了下,继续给我说夏季转场必须经历的一切。
“身子紧贴草皮或石头,钻心彻骨地冰凉。高海拔感冒了可不是闹着玩的,肺气肿、咳嗽吐血、血压突增、呼吸不畅,随时都会要人命的。”
贡巴给我讲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拉毛扎西和阿班也放下了手头的活,和我们并排坐下来,争先恐后说着。
他们的讲述是极其轻松的,从他们身上你看不到有丝毫恐惧感。那是怎样的乐观和豁达?数百年来,他们在高原上生存,没有逃离,也没有选择新的高地,如此坦然地面对生活,你不敬畏?或者,没有任何感触?
贡巴接着说:“那些小碎石被风刮着到处乱跑,互相碰撞,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那次我们看见了一只长得跟石头一样颜色的老鹰,展开巨大的翅膀,迎风而立。刚开始我们以为它受伤了,要不然它不会在如此大的风雨中驻足。牧民视鹰为神明,我们想帮它看看是翅膀受伤了还是腿受伤了。靠近它的时候,才发现它的羽翼下是一对乌亮乌亮的小眼睛。小鹰在石头上冻得瑟瑟发抖,要是没有那双大翅膀它们早就让风刮跑了。我们用帐篷替老鹰遮挡一会儿风雨,可是老鹰受到惊吓,不住鸣叫,并用翅膀严严实实护住两只幼子。经过努力我们还是把老鹰一家遮掩在帐篷下,直到风雨停歇。鹰的眼睛里布满了柔情和慈悲,那情形能把血性男儿的心融化成春水。”
贡巴接着又说:“可能是老鹰正带着孩子们练习飞翔呢,没想到风雨突然来袭。”
拉毛扎西说:“时候不早了,我们上路吧。佛祖保佑,但愿今天山口的风睡着了。”
贡巴和阿班附和着说:“嗷赖(藏语:表示肯定的语气,相当于是),大风睡着了!”
贡巴没有告诉我山口的风到底有多厉害,可我已经知道了。草原上的牛羊、牧人、马匹、格桑花、雄鹰、石头,它们都被大风一一吹过,它们与风一样都是自然之子,都在高原上领受苦难和寒冷的馈赠,但却更懂得慈悲和爱。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大概也是慈悲和爱了,也似乎只有慈悲和爱方能战胜一切。可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众生恰好忽略了慈悲和爱,那颗充满了私欲和占有的心灵,怎么能够抵御如此强悍的风雨呢!
夏季山口的风雨虽然奇冷无比,但我听到或看到的却是蕴藏着无限暖意的草原。大多数人一提起草原,心怀里全是蓝天碧草的浪漫和天马行空的自由。其实,草原潜藏着的更多的则是艰辛与酸楚。能够懂得且坚强活着的人一定是幸福的,他对生活肯定有着更为深邃的理解,对生命肯定有着你意想不到的感悟。也只有那样,生活回馈于他的才是真实的纯粹和洁净,生命给予他的才有真诚和感动。
我问贡巴:“草原生活这样艰辛,还想回去当老师吗?”
他说:“草原上的家人和牛羊更需要一个男子汉,把辛苦全交给女人,不是草原男人的本色。”
我想,一个没有经历过或不懂得生命意义的人,这样坚定的话是不敢说出来的……
目送着转场的朋友和牛羊,我坐在车上喃喃自语:“今天天气这么好,不会有风。”
4
我决定要去玛曲县阿万仓政府以南的贡赛尔喀木道湿地。贡巴虽然去了高山牧场,但我还是想去那儿。因为对草原的爱恋和难以名状的向往,也因为那份源自久远年代里对家族生活状态的探寻。
夏季的贡赛尔喀木道(藏语,意为贡曲、赛尔曲、道吉曲三条河流与黄河汇流之地)风景优美,河流回环;湿地与湖泊辉映,雪山与黄河并存;北方大地的阳刚之气与江南水乡的清柔之美融为一体,是探险家、摄影家、文学家的理想之地。也是因为它具备了北方和南方相济相融的特点,所以,贡赛尔喀木道也成就了玛曲县旅游业再度开发的可能。
阿万仓在正北,它具备城市和牧区共有的特征。茫茫草原上是两排三层平顶,四周是密密麻麻的瓦房。饭店,书店,蔬菜店,裁缝店;银匠铺,铁匠铺,修理铺,百货铺;汽车,摩托,马匹,还有卧在阳光下看守家园的藏獒。牧人的房子挨挨挤挤掩映在草丛之中,一群牦牛在附近的草滩上徜徉,羊群在更远的地方扎盘……这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生意人,当地牧民大多也是一边经商一边放牧。千年岁月让房屋与人和自然有了农耕式或田园般的默契,安恬闲适,不争不闹。
不远处就是寺院,长长的经房四周转经的大多是老人,他们缓慢悠闲,脚步和心灵合二为一。是年老了,再没有精力与风雪和狼群拼搏?一边转经,一边祈愿,是完成涅槃还是自我救赎?
我在这里遇见了一位提着兔笼子转经的老人,野兔是他用来放生的,然而他的放生背后却有着一段令人惊心的故事。我随老人一起转经,一边转一边听他缓慢地讲述。
那年高中刚毕业,就遇上了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时候最响亮的口号。我带着政府给上山下乡知青准备的三样东西:一个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黄色帆布挎包、一顶草帽和几本书来到了阿万仓草原传授羊群育种。来到阿万仓,我们就被暂时安排在牧民家里,跟着他们放牧牛羊。阿万仓方圆几十里都是草滩,密密匝匝连绵不绝,这种空旷和寂寥使年轻的我陷入空前的忧伤和烦闷中。
入冬前我跟着牧民收割牧草,在打草过程中发现有野兔子。原来那片草滩上生活着成千上万只野兔,它们世世代代在草场附近养育儿女,繁衍生息。
有一天,我发现一只野兔蹲在草堆前,喊了一声,那兔子就钻进了护草垛的网眼绳里。我活捉了兔子,可是当地牧民是不允许杀生的,于是我就拿着兔子到另外的知青点上,烤着吃了。当时吃着高兴就把兔子怎么钻网子里的细节向大家做了炫耀。可是没有想到,一时间知青们都开始编织网罩,大肆捕捉野兔。
刚开始七八个人带着大网,一头撑上一根木棍,把网支起来,只要兔子轻轻一碰网就会跌倒,专门有一个人藏在网边的草丛里,其他人从远处拿着木棒一边大声吆喝,一边慢慢前行,兔子都惊动出来,一个个贴入网中。
秋阳迷蒙的旷野里,知青们的欢呼声、吼叫声、嬉闹声飘过阿万仓空茫而静谧的上空,直到暮色时分,知青们带着捕获的猎物才回到原地。
有一天,一位老阿妈对我说,你们这样造孽,山神会不高兴。草原上的老鹰和狼会疯起来,你们是没有来世的人……
那年月连肚子都吃不饱,谁还怕山神怪罪。
知青们在草原上捕兔的行为愈来愈烈,每天不只是三五张网,而是十几张,甚至更多。当我看见那些灰色的、黑色的、白色的野兔,一个个嘴角流红,耷拉着脑袋被堆放在草地上的时候,我一下就晕倒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患有严重的晕血症)。那次我发了三天高烧,那位老阿妈说,捕兔子是我带的头,我的罪孽最大,要我转经念佛,才能赎罪。
我在低矮的土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想着堆成山的兔子尸体,心里十分害怕。于是,我就把沾满兔子血迹的那些网偷偷塞进火塘里,烧成了灰烬。
第二年春天伊始,天空里盘旋着的雄鹰开始叼食公社的小羊羔,有人为了护羊羔被老鹰抓伤的消息也不断传来,草原上狼也成群结队出现了……
我的心再一次被揪疼。好长一段时间里,我的梦中满是老鹰们饥饿的哀叫和狼群的长嗥。一直到两年过后,这片草原上的老鹰和狼群才逐渐消失。
返城之后的那些年月,我虽然在物质上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可是每个漫长的夜晚,我总是梦到野兔、老鹰、狼群,还有那位白发苍苍的老阿妈……
无法拒绝那样的梦,也无法从当年捕食野兔惨烈的场景中走出来。我的大半青春留在了阿万仓,留在了贡赛尔喀木道湿地,我将无法遗忘在阿万仓的那些岁月。坐了几天车,我从郑州只身来到阿万仓,之后就一直养育野兔,养大后就把它们放进草滩深处。可草地上的兔子还是很稀少,根本谈不上繁盛。十几年过去了,那些劫后余生的野兔还似乎心有余悸,它们在草地上很少露面,一旦出窝,也是势如闪电,快如疾风。
我们是没有来世的人,老阿妈当时就说过。牧民们信奉不杀生、不欺侮、不贪痴,保持世间安稳净乐。而我们自是读书人,却始终不肯做到这一点,小聪明换来大灾难,由谁来担当?
老人说着,神情就激动起来。我看着笼子里的小兔子,那明亮机灵的眼睛充满了好奇。它不晓得生离死别,不知道被追捕的恐惧,见了行人也不躲避。我就此想到,老人当年初遇的野兔大概也是这样吧。
为了平缓老人感伤的情绪,我不住劝慰他。其实在那样的年月里,谁能坚守住心灵的慈悲呢?
我想,其实转不转经无所谓了,他的灵魂已经得到了圆满。
5
穿过贡赛尔喀木道湿地,继续向南,就是青海久治县康赛尔乡。
“当桑烟和太阳一道升腾而起时,我在这里等你。”几年前朋友索南这样说。其实,我已经距他所说的地方不远了。
必须到那里走一走,因为一种信念,因为活着的困惑和感恩。但是,我不得不放弃几年前的约定。因为贡巴不在,也因为我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草原时常会失去方向。如果说这一切是借口的话,那么接连几天的大雨可能是我放弃的根本原因。
贡巴去了高山牧场,他的帐房也随之撤离,我只好住在他朋友拉毛扎西的帐房里。拉毛扎西和贡巴一样,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天天问我去哪里?还需要什么?去哪儿?需要什么?我也难以说清了。
多年前,我随着拉围栏的几个朋友漫游在这片草原上,期间遇到连日阴雨,差点送了小命。是索南和他的妻子给我们送了半袋糌粑,并且把一顶小帐房借给我们用,才活了下来。后来,大家一直想去感谢他,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具体在什么地方。这片草原辽阔无边,而且索南他们也是终年在草原上漫游。但我一直记着当年他说过的话。已经踏进了这片草原,我应该去找找他。尽管我心里知道,那样的寻找毫无前途,但于我而言,却意义重大。我几次试图把想法说给拉毛扎西,而终究没能说出口。看着他日夜操劳,一躺下就鼾声如雷,怎么好意思开口。
拉毛扎西要去久治县一趟,这是我在贡赛尔喀木道的第八天。
天气终于有所好转,然而太阳还是不见影子。微风徐来,扑打在脸面上的除了冰凉,剩下全是湿漉漉的潮气。拉毛扎西到那边去购置些东西,我是带着渺茫的希望,祈愿能够遇到索南。我们带着各自的意愿,天还没有亮开就走出了贡赛尔喀木道湿地。人的一生就这么走着,停着,再走着。可是,我们很少回过头去看看自己歪歪斜斜的脚印。当我们真正明白一生之中那么多远行的意义时,我们或许已经老了。说不出是悔过,还是自豪。那种源自一个人内心的秘密根本就无法说清。对此如果没有任何感想,是因人因地的不同而找不到了语词,还是千言万语的凝聚而找不到迸发的出口?这种感想时常存在着,可我做不到坦然地接受或面对。我们都有点矜持,沉默着,就那么走着,各自怀着不同的想法。
已经走出了很远,两匹马也明显迟缓下来,不住打着响鼻。
“稍微歇一歇吧。”拉毛扎西说着就停下来。他卸下了马鞍子,让马在身边的草地上吃草。这时候,南边的天空泛起了朵朵白云,大地透亮了许多。
躺在潮湿的草地上大约半个小时,隐隐约约,我听到了呜呜鸣响的海螺声。
拉毛扎西忽地站起来,说:“远处是天葬台,我们走吧,路还很远……”
应该是在远古时代,过着狩猎生活的人类祖先都弃尸于荒野,那种原始的做法接近了灵魂的本真,使灵魂得到最彻底的回归。野兽和飞禽让灵魂深藏大地,或飞腾天宇,找不到任何踪迹。然而,这涅槃背后是否存在着最原始的阵痛?我想到这里,不由自主用双脚在马肚上磕了一下,紧紧跟随着拉毛扎西。
草原依然无边无际,凉风习习,异样的味道随风而来。桑烟和秃鹫的行影,糌粑、茶叶和酥油的味道,以及喇嘛的诵经声此刻似乎在眼前若有若无地显现着。
路在感觉中越来越远了,漆黑的夜色一层又一层向我们围拥而来。这条路到底是远还是近?
拉毛扎西问我,你听到经幡的响动声了吗?它的响动即是灵魂的召唤。我没有听到,是因为我还在路上,所以我要好好地活下去。风渐渐大了,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夹杂着私语,夹杂着巨大的力量,夹杂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害怕。
和拉毛扎西赶到久治县的时候,天色已很晚了。在一家小旅馆里,我们和衣而眠。可我怎么也睡不着,纠缠我的是不是天葬路上对灵魂的膜拜?尘世安静了,可人心却偏偏不能安静下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风餐露宿,我们都要经历应该经历的一切,永不歇息。
拉毛扎西购置好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而我在久治不大的县城里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索南,也没有遇到曾经熟悉的面孔。就那样,我们又返回到贡赛尔喀木道湿地。心里尽管有着许多纠缠,但不得不用最快的方式去终结这次漫游。在草原上留下了什么?几千年来我们都不曾彻底搞明白,而短暂的漫游怎么能够解开祖先们栖居在这里而不愿离开的秘密?
离开阿万仓,翻过几座山梁,过了河曲马场,就看见玛曲县城了。那座以母亲河(玛曲藏语译为黄河)为名的县城在草原之上正诞生着新的生命和英雄。我透过车窗,看着眼底摇晃的牛羊,它们从一座牧场正赶往另一座牧场。灵魂所要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将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歇息了,灵魂还会继续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