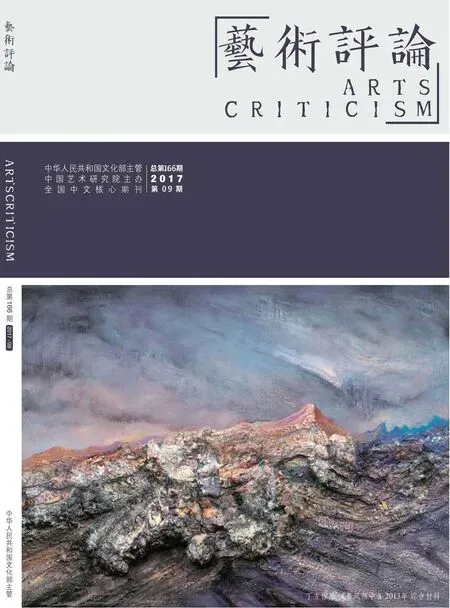追求中国话剧的高境界
——创作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剧场艺术
张 殷
追求中国话剧的高境界——创作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剧场艺术
张 殷
中国话剧已经步入110年的历史,在此进程中,作为唤醒民众觉悟、复兴民族尊严的革命文化运动,一路走来,披荆斩浪,所向披靡,始终以饱满的热情与竭尽的力量参与到中国各个阶段的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与祖国同命运共坚守。
当年中国话剧界的老一辈们,深知要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因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贫困颠沛的岁月中,他们始终对自己所从事的剧场艺术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拼命三郎的干劲,一次次将完美的舞台艺术呈现给观众,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只有达到剧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才能使演出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才能对民众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话剧史上,以此为标准推进剧场艺术向前发展的事例不胜枚举。正是有了这种对剧场艺术标准的严格要求,才有了不同时期话剧理论界和创作领域对内容与形式的反复讨论与探究。
1932年,熊佛西领导的定县农民演剧活动,其标准的第一条就是研究农民戏剧的内容与形式;最后一条是建筑乡村露天剧场,以便实验“区单位的剧场制度”。
1936年,国防戏剧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也是先研究内容与形式,然后找到了露天剧场演出时事实录剧和街头短剧的方式。
抗战戏剧也是在一次次地研究内容与形式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诸如街头剧、茶馆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多形式的剧场艺术。
然而,要创作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剧场艺术,绝非易事。

话剧《雷雨》海报
中国话剧大师曹禺先生,曾经出入戏曲舞台悉心学习多年;曾经在话剧舞台上摸爬滚打多年;曾经在图书馆里苦读细品多年,然后才以孜孜不倦的干劲,以崇尚艺术科学的精神,完成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可以放在巴黎最漂亮的舞台上演出的‘近代剧’”,成为了永恒的中国话剧经典作品。他在创作中既怀抱着一种牵动人心的幻想、希望和期待的理想情愫,又像科学家一样,严谨于戏剧的知识和技巧,懂得戏的结构的奥妙和作用。可以说,在观众和许多中国话剧同行人看来,他已经是达到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中国首屈一指的话剧大家了。然而,在中国话剧的剧场艺术中,显然还有更高要求的另外的声音。当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在剧场艺术中大放光芒的时候,张庚、欧阳予倩、李健吾、朱自清等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各自从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场面安排、悲剧概念,以及世界观等角度对曹禺先生的作品给予了高标准的评判。尤其是张庚先生提到的把握进步的世界观的要点,可谓一针见血。
曹禺先生在创作《家》之后的作品,中国话剧界公认没有他前期的创作那样富于经典性,那也应该归结到他在社会变革面前,还没能做到将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地步,由此,也给中国话剧剧场艺术留下了太多的惋惜。
毋庸置疑,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首先需要从事剧场艺术的话剧人具有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和洞察世事人心的敏锐的艺术触觉。
在整理中国话剧史的过程中,我常常被某些事件感动,也常常从这些事件上受到深刻的教育。借此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研讨会等系列活动,让我可以有机会将最近的几点思考和大家交流。
一、对中国话剧史何以从1907年划定的思考
1907年2月和7月,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李叔同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组织的春柳社,模仿日本新派剧的剧场样式,先后演出《匏止坪诀别之场》的片段和5幕剧《黑奴吁天录》。中国话剧史便以1907年为中国话剧发轫之年,记为中国话剧元年。
何以以春柳社在东京的演出为始呢?何以说改编本《黑奴吁天录》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出完整创作的剧本呢?我以为这正是老一辈中国话剧史论工作者在同时具备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和敏锐的艺术触觉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
1907年2月和7月的行动,也是缘于李叔同等人的政治眼光和艺术触觉的结果。1906年12月,就学于东京上野美术学校的李叔同(天津人)与曾孝谷(四川人,1873-1937),以李哀、曾延年的名义发起了中国留学生的综合性文艺团体——春柳社文艺研究会。其简章写明:本社以研究文艺为的,凡词章书画音乐剧曲等皆隶焉。
由此推断,出于李叔同和曾孝谷在文学艺术上的见识,他们发现要想从事文艺,必得以研究为本;要想以研究为本,必得研究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问题,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的融合整一,才是研究文艺的最高境界。
一方面研究文学中的新思想、新观念;一方面研究剧场内的新形式、新做派。喊出了“演艺之事,关系文明之巨”,“冀为吾国艺术改良之先导”的口号。
——他们开始研究林琴南(林纾)的改译本《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它们代表了在晚清政治变革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追求自由的信念。
——他们制定了“春柳社演艺部专章”,明确提出向欧美演剧和日本新派剧学习的宗旨:“演艺之大别有二:曰新派演艺(以言语动作感人为主,即今欧美所流行者);曰旧派演艺(如吾国之昆曲、二黄、秦腔、杂调皆是)。本社以研究新派为主。”《匏止坪诀别之场》的演出开创了中国剧场艺术的新形式,新思想用新派演剧形式表达,醍醐灌顶的作用惊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黑奴吁天录》走进日本东京大剧场本乡座的演出,一方面,首开新派演剧的剧场公开性演出之例,首开国人以新派演剧完整地呈现剧场艺术之例。此剧的剧场实践证明,其“布景的独出心裁,舞台的统一,演员的熟达……不让日本的业余演出”(伊原青青园语)。“剧本按现代话剧分幕形式口语写成,没有加唱,没有独白和旁白,幕间没有幕外戏”(欧阳予倩语)。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商业演出模式的初探:预先在《东京朝日》《东京每日》《读卖》《都》等10家报纸上做了宣传,租用本乡座舞台两天,租金为500日元;后台管理由本乡座包租。票价是均价日币50钱,最先卖出去的300张票,每人还获赠价值10钱的明信片——《匏止坪诀别之场》剧照。另一方面,以国人读得懂的内容,即“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以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林纾语)。“盖非仅悲黑人之苦况,实悲我四百兆黄人将为黑人续耳。且黄人之祸不必待诸将来。”和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在为我同胞“蒙昧涣散,不能团结,之终为黑人续”的感慨和感伤下达成共鸣。日本及欧美观众在惊叹留学生演出这种内容的剧目的同时,对留学生们模仿西方剧场艺术所做的研究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中国青年的这种演剧象征着中国民族将来的无限前途”。
有些史论者为李叔同1905年创作的《文野婚姻》打抱不平,认为《文野婚姻》是一出“在戏剧矛盾、情节结构上比较复杂,有一定的戏剧性”的剧本。但是我们都知道,它之所以不能称为第一出完整的创作,是因为它不具备完整的剧场艺术,它没能带给观众一定审美满足的影响力。
因此,中国话剧史以春柳社的发端为发轫,正是源于春柳社的两次演剧既有内容上的新思想,又有研究剧场艺术的新实践,两者缺一不可。而春柳社的后来者将新剧同志会挂牌上演的剧场取名为春柳剧场,而不用习惯的中国式“舞台”命名,也透出了中国话剧从一开始就具有的世界剧场艺术气魄,也使中国话剧肇始就处于高境界的境地。源于此,中国话剧的发展才能在具有一定思想高度的剧场艺术轨道上急驰。
二、对剧场艺术轮演制度的思考
中国话剧史上公认的经典作品有两座高峰,一座由曹禺先生率先铸就——《雷雨》,另一座由老舍先生领头移山——《茶馆》。曹禺在先,是开路者。从1907年中国话剧的正式起步,历经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有了一座高峰,这是惊世之举,了不起的创作。第一次完结了中国新思想以来,口号声震耳欲聋,行动力软弱疲沓的窘迫;第一次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是讲科学懂艺术的;第一次让国人敢于睁开眼睛正视我国的传统陋习。因此,曹禺的前期三部曲的完成,从舞台创作角度上说,终结了中国话剧剧场艺术探索的初期阶段。
在剧人们一片赞叹与惊呼声中,中国剧人以清醒的政治眼光与敏锐的艺术触觉捕捉到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问题,其中张庚先生的剧评,为中国话剧剧场艺术敲响了警钟。他的关于世界观的批评论点是这样论述的:
现代的剧作者如果没有一个进步的世界观,那他会把握不住一个悲剧题材所必不可少的“最集中的事件”,因为要把握它,正像要在矿砂中炼出金子一样,是需要炼矿术的知识的,要从驳杂的有常事件中找出集中的事件,就需要现代剧作家的炼矿术——进步的世界观……《雷雨》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上所表现的不幸,就是在我们反复述说的这点世界观和他的创作方法上的矛盾。
可见,张庚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关键性问题。
曹禺先生在这些评论声中,他的艺术触觉是敏锐的,他反复仔细地揣摩剧评人所指的方向,因此,继《雷雨》之后,他的剧作一部比一部更丰富更统一,终于完成了像《北京人》《家》等这样达到内容与形式完整统一,具有剧场艺术力量的作品。
但是,因为曹禺先生的剧作比起其他的剧作,已经相对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高位,致使此后的剧团在轮演这些作品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的剧场艺术的要求对《雷雨》做些更改,以至10年不改,20年不改,50年不改,80年不改,终于造成了诸如《雷雨》的笑场事件。可见《雷雨》的剧本思想已经在高速发展的剧场艺术的轨道上被甩在那里。
自《临床神经病学杂志》创刊伊始,慕容慎行教授即一直关心并支持我刊工作,为我刊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人已去,风范长存,我刊在深切缅怀慕容慎行教授的同时,将以他严谨治学的精神激励自己,奋勇进取。慕容慎行教授,我们永远怀念您!
话剧是剧场艺术,80年后的今天的剧场已经和80年前的大相径庭,今天的观众已经和80年前的大相径庭,今天在剧场里发生的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也大相径庭,可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
可喜的是,中国话剧剧场中,也有创作团队在继续《雷雨》的艺术创作,在改编原本的框架,甚至在更新它的内容。可见,轮演制度将是促进剧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一种有效和有力的工具。
曹禺先生的作品如此,吴祖光先生的作品亦如此。
吴祖光先生的《风雪夜归人》一出炉,就被列为“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曾经获得过上海剧艺社征集剧本第一名。它带着含义深长的哀愁,向观众宣说着一种真理——在那些被人践踏在脚底的阴暗的泥沙里,正埋葬着许多像珠玉一样优美纯洁的灵魂;他们虽然永远受着卑污和强暴的玷污或摧残,然而总有一天,他们是会挣脱污腐,开露光芒的。纵然,他们也许仍会被暴力压倒,被污秽埋没,以至于力竭气绝;然而只要他们能有一个机缘,得以一露光辉,不也就证实了生命的意义了吗?
但剧评人的触觉是敏锐的,华君评论道:遗憾的是魏莲生二十年苦斗的收获,不是不应该仅以一个衰老毁损的生命回到旧地来捡拾陈旧的足迹吗?玉春是首先不满家鸟似的生活而后唤起魏莲生的共鸣的,可是在莲生被逐之后,她自己为什么又会柔顺地做了徐辅成10年忠实的奴婢,10年贤良的太太呢?这一切留给了观众一个模糊的印象,反而消弱了前三幕的戏剧力量。
剧评人在当时并没有点醒吴祖光先生,然而,有一个人却始终锲而不舍,终于让吴祖光先生在此剧轮演30年后,改动了全剧的结尾。这个人就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这出戏,他看过7遍。在重庆时,他就对吴祖光先生说过:玉春那么光辉的形象,那么聪明,那么有头脑,她能够说服魏莲生,说明她是充满智慧的女子,但在戏里你给她这么处理的话,就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要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她就不应该做这样的妥协。此剧接着轮演,30年中,每次周总理看见吴祖光先生都会询问,剧的结尾打算什么时候改和怎么改。
事实上,我们要再次重申一部作品在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统一的难度。吴祖光先生背着改动这个“包袱”,背了整整15年。这15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等社会变革,他的世界观也跟着社会的变革在一次次的洗刷和重构。终于到了1955年,他动笔了。但这一次,并未改好,连他自己都不满意,因为,他将尾声改成了足有一幕的长度(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风雪集》上,1955年6月版)。后来,他跟周总理汇报时,怎么也说不明白,他只好悄悄地又改了回去。当1957年4月,人民艺术剧院准备演出这部剧,中国戏剧出版社要出单行本时,吴祖光才终于想清楚怎么改了:原剧本的尾声不动,其中只改了两句话。盐运史徐辅成问苏弘基说:二十年前你送给我四件礼物,其中一件就是玉春这个活人,我至今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她送给我?因为玉春从进我家门起,她就一句话也不说,成了一个哑巴啦。吴祖光先生用改过的两句话,表现了那个时代“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她不可能逃出去,充其量也只能这样消极抵抗”的自觉之举。短短的两句话,用了15年,足可见剧场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有多么的难以实现。
因此,要大力提倡轮演制度,并鼓励导演、演员以及一切参与创作的演职员共同补救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问题,因为话剧毕竟是综合性的剧场艺术,毕竟要在剧场完成统一的再创作。
吴祖光先生遇到的是周恩来总理,他是幸运的。在那个年代,不只是他一个人幸运,可以说是有一大批的剧人都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完成剧场艺术的,因为周总理就是中国话剧人中既有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又有敏锐的艺术触觉的专业的艺术家。
三、对中国话剧需要领导者的思考
阅读中国话剧史,你会发现,有个编剧原本不是个编剧,他只是个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棠棣之花》,从1920年开始编写然后总共修改了20年,也没能搬上舞台在剧场演出,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啊。幸而这时周总理发话了,他提出要在1941年10月,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活动中,上演《棠棣之花》。于是,满眼充满感激泪花的郭沫若,埋头又修改了一遍剧本,年已50岁的他忐忑地请著名的导演“审查”,这位导演摆了手,他再拿给下一位,连续四位著名导演都婉辞了他,认为剧本“有诗没戏”。在不幸之中他真是万幸,遇到了好领导。周总理在党内做出了决定:“责成石凌鹤(共产党员)导演,大家协助。”郭沫若当即表示:“请导演对剧本大胆修改,自己甘做戏剧初级学生。”就这样,石凌鹤大胆地做了修改,仅第五幕就删去了8页,同时减少为烘托气氛而设置的群众、乐队、宫女等,着力塑造了春姑、聂政两个人物,发展了春姑钟情聂政的戏份。如第二幕增加了春姑不惮少女羞怯,折桃花一枝献于聂政,表达对聂政敬慕和爱恋之情,希望聂政平安回来相聚,为后面春姑以死殉聂政,垫下绝妙的一笔。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参与排演,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在首演结束后,给郭沫若提出了两千余言的建议,郭沫若认真修改后,才出版剧本。从此,他的《棠棣之花》被誉为是“充满了人生正义的真情”的“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成功”剧目。
周恩来的举动,大大激励和焕发了郭沫若作为编剧的才情与斗志,在此后的18个月中,他以一鼓作气势如虎的笔力,写出了《屈原》《虎符》等6部中国话剧史上优秀的历史题材剧,他本人也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开山者和领头羊,引领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思潮。毛泽东主席曾热情地肯定和鼓励郭沫若的历史剧“大益于中国人民”,“不嫌其多”,希望“继续努力”。
周总理的力挽狂澜,不仅仅是解救了一个编剧人才想要创作的烦恼,他的成就在于,他高屋建瓴地发觉了历史题材在那个年代对于内容上所能做出的对现实的贡献,有了比较成熟的形式,内容的升华被摆到了剧场艺术的前沿,没有适应时代的内容,再成熟的形式也只能是形式。同时,他以犀利的目光,看到编剧所具有的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反映,将有助于引领整个中国话剧的剧场艺术。因为《棠棣之花》中所表现的是正义的一群人,每个人物的心胸都洋溢着爱——母子之爱、姐弟之爱、朋友之爱、男女之爱、正义之爱。正如当年章罂借《新华日报》(1941年12月7日)所说的:“《棠棣之花》表现了郭沫若先生对人类本性中纯爱和正义的理解和深意……同一个材料,由两个世界观不同的作家来写,就可能写出两个不同的剧本,给观众两种不同的认识。”
从这件中国话剧史上的著名事件上,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话剧需要有“具备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和保持洞察犀利的艺术触觉”的创作人员,更需要有“具备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和保持洞察犀利的艺术触觉”的领导人的组织与支持。
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下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指示将永远激励着中国话剧人。以史为鉴,从来中国话剧就是紧跟中国领导人的决策与部署,才有光明灿烂的今天,追求中国话剧高境界的今天同样需要一批“具备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和保持洞察犀利的艺术触觉”的创作人员,更需要认真学习与贯彻国家领导人对文艺方针的各项指示精神。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作优秀作品的要求,要求我们要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同样,只有做到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才能迎来中国话剧的高境界。在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之时,中国话剧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追求中国话剧的高境界,创作出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中国话剧剧场艺术,将永远都是纪念中国话剧的主题。
注释:
[1]春柳社文艺研究会简章[N].时报.1907.4.22.
[2]以笔名冷红生发表。
[3]“租费极昂,出人意外。欲罢不能,若努力为之,又非留学生少数人所能筹办。幸有某公允借5百元,乃敢定义。”见春柳旧主.春柳社之过去谈[J].春柳.1919(2):2.
[4]灵石.读黑奴吁天录[J].觉民.1904(7):29.
[5]张庚.悲剧的发展——评《雷雨》[J].光明(上海1936).1936(1):60-65.
[6]华君.观《风雪夜归人》零感.新华日报[N].1943.3.15:第4版.
[7]吴祖光.《风雪夜归人》的前前后后[M].吴祖光.写剧生涯.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张 殷:中央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