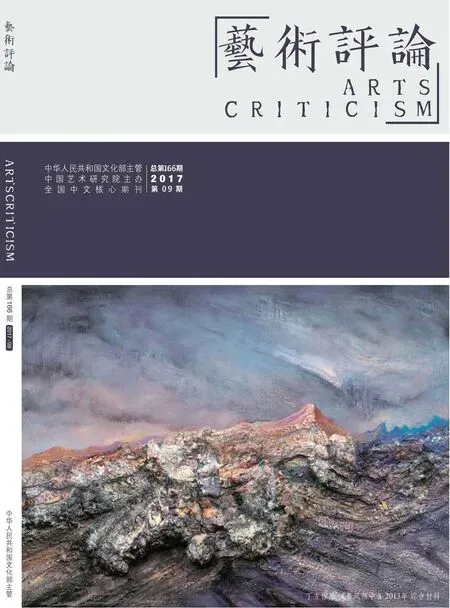曹禺:中国话剧诗化之集大成者
——为纪念话剧110周年而作
田本相
曹禺:中国话剧诗化之集大成者——为纪念话剧110周年而作
田本相
我曾经论述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并且认为诗化现实主义是中国话剧的传统。但是近几年来,我经过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文学的传统是诗化传统;中国话剧的传统,则是在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的传承中,形成了中国话剧的诗化传统(我将在《中国话剧和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一文中对此进行专门的论述)。而就中国话剧的诗化传统之形成和发展来说,曹禺是中国话剧诗化之集大成者。正如中国戏曲的伟大剧作家王实甫、关汉卿、汤显祖等将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融入中国戏曲的传统,创造出中国戏曲之典范,曹禺则是以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将外国的戏剧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话剧之典范。
一、诗的感悟
我在《曹禺传》中专门写了一章《诗的迷恋》。正是在曹禺的少年时代,他的天才的诗性如春花绽放。诗对他来说,是对人生的叩问,是对生命秘密的探索,是对社会的抨击,甚至是对宇宙的探寻。
曹禺少年时代就萌生的忧郁苦闷,以及那种孤独寂寞之感,在他内心激荡着不息的情感波澜。同时,他那富于浪漫色彩的个性,使之对诗有一种特殊的追求。他在一段时间里特别喜欢写诗,并且用诗作为他抒情的工具。他接受过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的熏陶,也读过不少新诗。1928年上半年是他写诗最多的一个时期。在这些诗作中,荡漾着他那旺盛的诗情,或凄婉清冷,或恬淡幽静,但它的诗境又是那么朦胧超脱。如《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带着蕴蓄着的怅惘,郁结着的伤感,在雨夜送别行人,叹息着行人明晨便将无踪无影。曹禺曾说:“当时我对诗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认为诗是一种超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我自己只觉得内心有一种要求,非这样写不可。”(《简谈〈雷雨〉》,《收获》1979年第2期。)超脱也好,朦胧也好,但它的情调却是凄楚而悲凉的,诗的意境也是完整的。曹禺作为一个诗人的气质和才华已闪现出来,尤其透露着他有一种人生大感喟。不久,他又写了一首长篇抒情诗《南风曲》,这首长诗写得更为飘逸了,好像田园牧歌一样。他的想象力是那么飞扬,把我们带入一个村童的梦境之中。在晨光中,林野静默,山峦安谧,草香迷人,绿茵酣适。南风吹来了,送来湿土的香味,山野静悄悄,村童渐渐熟睡。“吹得睡灵儿出了躯窍,吹得睡灵儿飘飘摇摇”。于是他梦见一个柔媚美貌的洗衣少女,纷披的长发,雪白的裸足,漫歌着抑扬的村调。村童的心灵不自主地惊喜,赞叹这少女是“这般柔媚,这般美貌”,他被迷住了。但是禅寺的钟声却惊醒了他的梦境,不由得使他痴想颠狂。可是眼前只剩下“残花”“土冈”,伴随着那单调的钟声“当当……当当”。如果说《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是在离情愁绪的不言境界中,蕴蓄着的是怅惘,郁结着的是悲伤,而《南风曲》就更多地体现了对一种浪漫的缥缈的境界的追求,但又是一种对美的向往的破灭和失落感。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同时写的另外一首诗《不久长,不久长》。这首诗的思想情绪,看上去是相当消极而悲观的。寻找一个深壑暗涧作为自己的坟墓,神往一个静谧森然有着鬼魂相伴的境界,让自己的灵儿永远睡在衰草里。的确,这很难令人明白,曹禺当时那么年轻,却为何产生这种人生“不久长”的悲叹和感伤,为何产生这样的玄思冥想;又似乎积淀着一种人生苦闷,在寻求着解脱;在无奈的叹息中,对生命发出他的疑问。尽管我们不能把作品的思想同诗人的思想等同起来,但这些思想情绪毕竟是一个存在,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从诗人心中流露出来的,总是反映着他的某些思想情绪。曹禺曾说:“我的青年时代总是有一种瞎撞的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求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他曾苦苦地追索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思考着人生的课题,有时未免搅得他坐卧不安。在这些诗中正有着这种追索的苦闷印痕。苦闷,并不都是坏事,它往往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孕育着思想的变动和飞跃,一旦从中挣脱出来,便会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甚至,苦闷本身就有它的潜在的价值。从艺术上来说,这些诗体现出他的美学追求,他追求诗的感情,诗的意境,追求思想情绪的诗意表现,这点,对他未来的戏剧创作倒是影响深远的,由此,指示着通向戏剧诗人的路途。
他虽然写的诗不多,但是他却有了诗的感悟,诗的灵性。他是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说,他是带着深厚的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走上戏剧的舞台的。
二、诗的宣言
《雷雨》于1934年发表于《文学季刊》第3期上,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引起重视,虽有国内在校学生尝试演出过,但社会影响有限。《雷雨》所受的最早的关注来自日本的两位青年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他们把这部剧作介绍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激起了留学生们的演出热情,终于促成了1935年4月在东京的公演。滞留日本的郭沫若和日本著名的戏剧家秋田雨雀都给了很高的评价。就在杜宣和吴天准备演出此剧时,他们曾写信给曹禺,说他们的演出打算将序幕和尾声删去,这引出了曹禺的一番激昂的答辩。那时的曹禺,带着一种虎虎生气,在复信中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见解,就其思想和感情来说,是十分坦率和真诚的。这里,绝没有敷衍,没有客套。他鲜明地宣称:

1937年,中旅演出《日出》剧照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原谅我,我决不是套易卜生的话,我决没有这样大胆的希冀,处处来仿效他。)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
(《〈雷雨〉的写作》,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第l卷,花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曹禺提出写《雷雨》是在写一首叙事诗,这绝非一般地讨论自己的创作,而是提出了一个“戏剧诗的美学观念”。他是对“五四”以来的话剧创作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反思后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他对外来的戏剧和戏剧理论进行借鉴思辨的结晶。
我在有关田汉的论述中,曾经谈到田汉对中国话剧诗化的开拓性的贡献。但从中国话剧的发展来看,曹禺则是中国话剧诗化的集大成者,不但形成了他比较完备的话剧诗化的主张,更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渗透着融化着中国的诗的传统,几乎中国诗学的所有的审美精神和审美范畴都沉潜在他的戏剧诗里。
《〈雷雨〉的写作》可以说是曹禺的一篇创作宣言——中国话剧的诗化宣言。
首先,它是对“五四”以来误解了的社会问题剧“只谈问题,不顾剧艺”倾向的一个反拨。“五四”时期新剧的倡导者,在《新青年》上推出《易卜生专号》(1918年第4卷第6号),胡适率先发表了《终身大事》,于是社会问题剧的创作蜂拥而起。如人生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恋爱问题、军阀混战、政权腐败问题、阶级对立压迫等问题,一时都成为戏剧热衷反映的内容。
这些剧作虽然折射着时代的精神,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热情,但是,总的看来却太拘泥于现实问题,而缺乏戏剧作为艺术的存在所必需的条件——戏剧性。为此,“问题剧”曾经遭到宋春舫、向培良、以及“国剧运动”的倡导者的批评。而曹禺提出以诗的观念写剧,正是对这些“问题剧”所暴露的问题的反驳。他强调他的《雷雨》“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显然他是不赞成那些浅薄的“问题剧”,并力图同它们划清界限的。
曹禺一再声明,他虽然承认他受了易卜生戏剧的影响,但是他对易卜生的理解,却摆脱了“五四”时期对易卜生的误读、误解的定势。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在“五四”时期影响很大。他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还说:“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后来,胡适也承认,他们倾力介绍易卜生,全在于宣扬易卜生的思想。
曹禺不但演过易卜生的剧作《娜拉》《国民公敌》等,通读过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而且他的大学毕业论文也是关于易卜生戏剧的。他当然晓得,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决不是只写社会问题的,其实,易卜生特别强调应把戏剧作为诗来写,特别强调戏剧创作是诗人的任务。这一点是全面把握了易卜生戏剧的曹禺独具慧眼的发现。
易卜生在《诗人的任务》中说:“做一个诗人是什么意思呢?我费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做一个诗人实质上是观察,但是请注意,他的观众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观众现在所看到、所了解到的,全都是诗人早就观察到的。……我近十年以来所写过的东西,我在精神上都经历过。”他不但强调这种“精神”上的“经历”,而且强调这种“经历”中曾经被鼓舞的被振奋的东西,他说:“鼓舞我的,有的只是在偶然的、最顺利的时刻活跃在我的心间,那是一种伟大的、美丽的东西。”而易卜生所迷恋的所要写出的正是这种“诗意”。(易卜生:《诗人的任务》,《外国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从易卜生的剧作来看,他的写实,并非像“五四”时期那些易卜生的鼓吹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提出社会问题,仅仅是写出“社会种种腐败龌龊”;而是更追求写出他精神经历中的真实和生活中蕴藏着的“伟大”和“美丽”的“诗意”。这些才是易卜生现实主义戏剧的精髓。
不过,应当明确,曹禺的“诗”,更多地是熔铸着中国诗歌的美学传统。
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金院本、元杂剧、明南戏、清传奇,中国的艺术,特别是戏剧传统中,从来都弥漫着浓重的诗的气息,显示着民族的诗性智慧。但是,就中国话剧产生之初的历史状况而言,它恰恰是以反对这种以旧戏为代表的诗学传统,颠覆其现存形态,来为自己打开进路的。“问题剧”走到极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话剧对传统戏剧诗学传统的背离。
曹禺则以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感受和艺术胆识,深刻地把握着易卜生戏剧的艺术精华和艺术内涵,并化为他自己的戏剧诗的美学概念。因此,可以说,当曹禺向社会发出了他的戏剧诗宣言时,他既摆脱了把戏剧仅仅当成是揭露问题的工具的庸俗社会学的戏剧主张,也摆脱了只为渲染情绪而将一首叙事诗写成对话体的非戏剧的创作模式,从而实现了中国现代戏剧与传统诗学精神的沟通与对接。
把易卜生仅仅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剧的剧作家,是“五四”时期对易卜生的一个最大的误读,一个遗留甚久的误读。胡适毕竟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具有艺术灵性的人,他虽然是“五四”文学领袖之一,但他似乎缺乏艺术的灵性和天资,老实说,他的新诗写得不算漂亮,剧本也写得不大好,但由于他是新文学的旗手,艺术上的影响很大,而他对于戏剧艺术的误导,不仅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直至今天仍然是应当值得重视的问题。
其次,曹禺在写给杜宣等人的信中所一再提到的“幻想”和“狂肆的幻想”,以及强调观众把《雷雨》“当作一个故事看”的说法,历来未曾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实际上他涉及到现实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升华的问题,甚至是现实主义的本质问题。写实“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雷雨》所写的罢工等等,还有后来人们所总结的诸如《雷雨》意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等,这些皆与社会问题有关。但是,他特别提出的“狂肆的幻想”,即在创作中更需要高度飞扬的想象力,如《雷雨》中的那些血缘关系的巧合,以及人物命运的残酷的巧合,真叫人听来好像是“神话似的”故事。而这些就非一般所谓“写实”所能概括。在似乎脱离写实的“狂肆的幻想”中,却达到了更高的真实,也就是我说的“诗意真实”。曹禺虽然没有以明确的理论语言来概括他的想法,但是,他却以他的创作实现了他的主张。
当曹禺说,他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时,足见作为一个戏剧诗人,他是十分重视戏剧的情感因素的,不但写剧的动因是情感的驱动,而且他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也在于在感情上能够达到动人的艺术效果,自然在其建构剧情和塑造人物时,也熔铸着作者的激情。也就是说,曹禺话剧的诗化是特别强调“情”的,把主体的“情”注入对现实的观察和现实的描绘之中。
三、诗意真实
曹禺的话剧诗化也表现在他的真实观上,也有着他自身的特点,尽管他没有用理论的形式概括下来,但在创作中,在他后来的回顾中都有着深刻的表述。
我在有关曹禺的论著中对曹禺的真实观曾作过概括:即“诗意真实”(田本相:《曹禺全集 · 后记》。)在这种诗意真实中,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雷雨》在东京演出剧照
首先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诗意的捕捉、感悟、提炼和升华。比如《雷雨·序》中说:“《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构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这里所谓的“不可言喻的憧憬”或者他说的“神秘的吸引”“抓牢我心灵的魔”等,看来未免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而实际上是对现实的诗的感悟,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题材的诗意的把握。它是一种创作的状态,但更是一种艺术创作中的美学感悟。比如,他说:“《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就是他从《雷雨》的真实中所感悟的人生的、社会的,甚至是宇宙的哲学。他那种“情感的憧憬”,“没有能力来形容它(人生、社会、宇宙——引者注)的真实相”,就深化为《雷雨》的诗,残酷的诗:“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显然,从作者的美学追求来看,他的戏剧的诗,要求戏剧必须写出生活的诗意,或者说诗意的哲学。
在《日出》的创作中,他说,在他心头最初涌动的是一首诗,是陈白露几次吟诵的那首小诗:“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当然不能把它看作是《日出》的全部主题,但却是他对《日出》的题材的诗意的发现。类似于陈白露一类人的存在,注定是不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延续。她们不是害人者,她们的生命曾经显示过美丽和纯净,但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了她们的灵魂,她们注定会成为那个旧世界的殉葬品。这是曹禺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对这样一种人生的最本质的概括。因此,叶圣陶评论《日出》,说:这个剧“其实也是诗”(叶圣陶:《其实也是诗》,天津《大公报》,1936年12月27日)。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曹禺的话剧诗化是一个很高境界。在曹禺看来,一个剧作家应当是一个思想家,一部伟大的剧作应当有着深刻的思想,当然不是那种思想的概念,而是透过剧情、人物所流露出来的思想。
文学反映生活,可以更广阔,更深厚,应当看得广泛,把整个社会看清楚,经过深入的思索,看到许许多多的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人物再写。
(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曹禺全集》第5卷,第106页。)
一个剧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才好。一个写作的人,对人,对人类,对社会,对世界,对种种大问题,要有一个看法。作为一个大的作家,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然,尽管掌握了很多的、很丰富的生活积累,但他没有一个独立的见解,没有一个头脑来运用这些东西,从中悟出一个主题来,那是写不出深刻的作品。
(曹禺:《我对戏剧创作的希望》,《曹禺全集》第5卷,第328页。)
对戏剧的思想性的高度追求同对戏剧诗的艺术境界的追求是统一的,在曹禺看来,从素材当中开掘的独到的诗意哲理性和美学内涵的和谐统一,正是伟大作品的生命。而尤为令人关注的,是曹禺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的向度,以及这之中燃烧着的理想情愫。
一个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必然带着他的观察和思考的向度,也可以说,必然烙印着作家的世界观的深刻痕迹。曹禺描写现实的特点是,在污秽中看到圣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或者说,他是以一颗人道的诗心去观察现实、观察人物的,因此,他的真实观中,就熔铸着十分动人的理想情愫。《日出》对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黑暗、无耻、腐朽,做了最深刻的揭露;但是作者却不是在展示罪恶,展览黑暗,而是怀抱着希望,憧憬着光明,燃烧着理想,去观察和描写这些人间的地狱和魔鬼。于是,他发现了陈白露的人性的诗意,翠喜品行的诗意,发现了黑暗中有着日出的曙光,绝望中有着人生的希望。
这里,曹禺在表明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思想,即怎样观察现实和描写现实的问题。显然,他不但力图同自然主义区别开来,同照相主义区别开来,而且把他的真实观注入了诗意的内涵,形成一种诗意真实观。契诃夫也曾这样说过:“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不过由于每一行都像浸透着汁水似的目标感,你除了看见目前生活的本来面目以外就还感觉到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一点就迷住您了。”(契诃夫:《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2期,第176页。)
因此,曹禺对现实主义就有了他独到的理解。他认为现实主义,也并非是那么现实的。在谈到《北京人》的创作时,他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总觉得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在这个戏里,瑞贞觉悟了,愫方也觉醒了,我清楚地懂得她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但是,我没有点明。她们由袁任敢带到了天津,检查很严;又是在日本占领的地区。这样写,不但要写到日本侵略军,当然把抗战也要连上了。这么一个写法,戏就走了“神”,古老的感觉出不来,非抽掉不可。这个戏的时代背景是抗战时期,但不能那么写,一写出那些具体的东西,这个戏的味道就不同了。这点,我和有些人的主张是不一样的。现实主义当然要写时代,但把那个时代的事都写进去。写对时代的感觉,我很佩服我的师辈茅盾先生,时代感写得很准确,政治是个什么情况,经济是个什么情况,都写进去了。这个戏是在四川江安写的,写的是北平。要明写,袁任敢带瑞贞走,他是有路子的,他自己可能就是共产党人,或者是靠近党的人士,他装傻就是了。甚至连江泰也知道瑞贞是接近共产党或进步人士的。我不能这样写,我也不愿意这样写,更不能把这些都写个透底。如果这样,我就觉得这样不得不使戏失去了神韵。说得明白些,戏就变了味,就丝毫没有个捉摸劲儿,也就没“戏”了。说到底,我的体会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路子,并不是说都按现实的样子去画去抄。我还是那句话,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
杨晦的《曹禺论》对曹禺的环境描写持批评态度,他说曹禺的戏几乎都没有确切的背景,要有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曹禺声明,他不会像茅盾先生的小说《子夜》那样,在明确的历史时间概念中对现实生活的内容做出逼真的再现。他很重视“神”“神韵”和“味”这些中国传统诗学的概念。远则不说,魏晋以降,“味”被广泛运用于文艺批评,如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看来曹禺强调的是韵味,它指的剧作更内在的意蕴,是“味外之旨”。这正是曹禺的话剧诗化所追求的核心和精髓,这似乎是不可言传的,但却又是可以感到的,可以作出理论解释的。“味”作为一种审美判断,似乎是不确定的,但是,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就感到自己所写的是否具有美学的价值了。说得更明确些,“一个优秀的诗人,追求艺术表现,即‘以全美为工’,这样才能获得‘味外之旨’。司空图有“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之说,可见“味”对于创作之重要。(参阅蒲震元:《析“品”》,《中国艺术批评模式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160页。)
曹禺的话剧诗化剧作在中国话剧历史上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是它所表述的以及从剧作中所体现的话剧诗化的美学思想却没有被及时总结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曹禺:《谈〈北京人〉》,《曹禺全集》第5卷,第76页。)
四、诗的创造
在曹禺的诗化的戏剧创作中,几乎所有的中国诗学的审美范畴均化入他的作品中,这些对他并不是理念,而是在中国文学诗化传统的熏陶中形成的。
传统的美学范畴之一,有“诗可以兴”之说。对其的解释,基本有两种,一是把“兴”作为一种修辞手段;二是作为审美范畴。我赞成张海明对“诗可以兴”的阐释和论述。他认为魏晋以后,随着诗缘情观念的提出,触物起情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晋人挚虞的“兴者,有感之辞也”(《文章流别论》),继之有刘勰的“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故义必明确;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文心雕龙 · 诠赋》)。在张海明看来,刘勰以“起情”释兴,将兴与情联系起来,是他的一大贡献。贾岛则说得更为明确:“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二南密旨》)。心物相感,交互作用才会产生兴。(以上参看张海明:《经与纬的交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08—190页。)显然,兴是一种审美的范畴,也是一种创作的状态。

1935年,曹禺(中坐者)在《财狂》中饰韩伯康
譬如《雷雨》的创作,他说是在写一首诗,就是在这样的缘物起情,心物交感,情不可遏的状态下创造出来的。作为一个戏剧诗人,他十分重视戏剧的情感的因素,不但写剧的动因是情感的驱动,而且他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也在于在感情上能够达到动人的艺术效果,自然在其建构剧情和塑造人物时,也熔铸着作者的激情。也就是说曹禺话剧诗化是特别强调“情”的,把主体的“情”注入对现实的观察和现实的描绘之中。
曹禺的戏主人公多半是有原型的。但是原型对他绝对不是模仿的对象。他的人物创造,可以说是在“缘人起情,心人交感,情不可遏”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曹禺对我说,繁漪是有原型的,是他的同学陆以洪的嫂子。“我和陆以洪是相当要好的,有时是无话不说,天南海北,甚至是他的隐私。写蘩漪这个人物,就是他把一个类似蘩漪女人的故事告诉了我,在我的心中放了一把火。”还说,“陆以洪和他的嫂子有爱情关系。我是从陆以洪那里受到影响,才写了蘩漪这个人物。他这位嫂子不像蘩漪,最初的印象是陆以洪给我的,她长得文静、漂亮,并不厉害,但是,却一肚子苦闷,她不喜欢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总在外边跑。她和陆以洪的爱情关系到底深到什么程度,其内情,我就不知道了。”
只要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绝对不是对现实的人物的原型和故事的模写和照搬。像蘩漪的原型,在旧社会是不被人同情的,甚至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受到严酷的摧残和打击。就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也不一定会同情这样一个“偷情的女人”。但是曹禺却对这个嫂嫂有着非同一般的“发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艺术“发现”。他发现“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他不但同情她们,而且发现她们心灵的美。曹禺说:“是不正常的发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曹禺说,正是这位嫂嫂在他的心灵中放了一把火,于是升华出一个繁漪的形象来。

《原野》演出广告(1937年)
还有陈白露,在生活中也有原型——王又佳,曹禺说:“他的父亲和我父亲要好,是朋友,我就是这样同他认识的。她不是陈白露,也不是交际花,但她确实漂亮,也非常聪明。真正的交际花我也见过,但王小姐不是。她是胡闹,她不是卖钱的。我同她家不是十分熟,但这个人呢,却一下子把我写陈白露形象点燃起来了。就像陆以洪的嫂子,使我点燃了蘩漪的形象。”“触发写陈白露的还有当时的艾霞、阮玲玉的自杀事件,她们都是电影演员,最后自杀了。这些事是颇令人思索的。就是这一切汇聚起来了,才有了陈白露的形象。”(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页。)
曹禺是熟谙中国诗歌艺术三昧的剧作家,他说他在写一首诗,在他创作的想象中,他所建构的就是一个诗的戏剧的大厦。我以为,从最初的个别的人物、一些片段,逐渐进入艰苦的整体构建的是戏剧的诗的意象。我赞成陈伯海的意见:“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意象的经营事务艺术。”他说这与“抒情传统在诗歌作品中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而情感活动本身无法直接指陈,只有凭借引发或寄寓情感心理的物象和事象给以暗示,烘托。为此‘意象’(表意之象)便成为抒情艺术的独特道具,通过意象的营造来映照和展现人的情感体验,构成诗歌抒情的必由之路。”(陈伯海:《意象艺术与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曹禺的戏剧诗的创作的特点,因人(物)起情,以抒情为主导,倾力营造戏剧的意象。
即以《雷雨》来说,它所营造的就是具有诗意的雷雨的戏剧意象。我们还很少看到一个剧作家在孕育着他的剧作时,像曹禺这样把他的巨大热情浇铸在他营造的戏剧意象之中。曹禺把他对时代的感受和对现实的激情同自然界雷雨的形象交织起来,使得《雷雨》中雷雨般的热情和雷雨的形象浑然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景交融的诗意境界。雷雨既是整个戏剧的氛围,又是剧情进行的节奏。雷雨既是破坏旧世界力量的象征,又蕴藏着作家对宇宙不可知的神秘憧憬和苦闷。剧中人物几乎无不呼吸着雷雨的气息,感受着雷雨的激荡。第一幕开场,暴雨前的郁热闷人的空气低压着,四凤喘着气,嚷着“真热”,显然作家并不是单写天气,也暗示着人物内心的烦闷。好像蘩漪对雷雨的感觉更为锐敏,她的心情始终和雷雨的变化伴随着。在第二幕中,她那段雷雨前的独白,使内心火山待发的愤懑和郁闷的自然气氛水乳交融:
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着你们。
这可以说是蘩漪的诗。借景抒情,情切动人。尽管作家没有具体描绘自然的氛围,但从蘩漪对雷雨前低气压的感受上得到了更逼真的展现,同时,把周家环境的禁锢逼人的气氛也真实地描绘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正好衬托出蘩漪此时此地的心情,显示出环境把她逼得非来场喷发燃烧不可。像这样情景交融的境界,在《雷雨》中渗透着,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作家的诗意感受,使他寻求着戏剧的诗意境界的创造。狄德罗说:“美妙的一场戏所包含的意境比整个剧本所能供给的情节还要多;正是这些意境使人们回味不已,倾听忘倦,在任何时期都感动人心。”(狄德罗:《论戏剧艺术》,《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1期,第154页。)《雷雨》对戏剧的意境创造,是凝结着中国戏曲和古典诗词意境创造的精灵的。在这方面,《雷雨》使我们领略到民族艺术的风姿和精神。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我们也看到作家追求诗的意境创造,追求着抒情风格,即使他曾经追求着契诃夫的风格,但仍然看到作家始终是用民族艺术的风姿和精神去融合去摄取的。

《日出》演出广告(1937年)
曹禺不止一次说,中国戏曲的编剧特点是很值得学习的。“在不重要的地方只几笔带过,在需要大段抒发人物感情的地方抓住不放。”在这里透露出,作家抓住了中国戏曲善于在矛盾冲突中刻划人物感情的特点。在中国戏曲中,为了很好地刻画人物性格,往往使人物通过唱腔抒发感情,展现其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透过写人物的情来刻画人物性格。如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刻画张的形象就是这样。张瞒着妻子,因慑于鲁斋郎的淫威把她送给了鲁斋郎。张内心十分痛苦。于是作家为他安排了【南吕 · 一枝花】、【梁州第七】两段唱腔,使之把内心交织着的羞愧、愤怒和痛苦的复杂感情抒发出来;而人物性格也得到展现。为此,作家不惜笔墨,翻来覆去,直到把情写得淋漓尽致,同时把性格也写透了。如果说中国戏曲是借“唱情”而写人物;那么,《雷雨》则是借“说情”而写人物了。在人物的台词中,人物的感情得到抒发,人物的性格得到展现。如第二幕蘩漪乞求周萍不要走的一场戏,人物性格展开激烈冲突。蘩漪拚命抓住周萍不放,求他不要弃她而去;而周萍则拚命脱开困境。作家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纠葛上,而是借此让他们各抒其情各展胸臆。在周萍拚命摆脱的动作中,着意揭示他感情的懦弱、厌烦和苦闷;在蘩漪死死抓住对方不放的动作中,揭示她受抑压的痛苦、怨恨和愤懑。对周朴园、对周家罪恶的满腔怒火化为不可遏止的控诉激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她那特有的阴鸷性的爱和恨。
同样,写周朴园和鲁侍萍重逢的场面,作家不惜笔墨,也是为了使鲁侍萍积郁三十年的恨和悔抒发出来。在这些地方,显示着作家戏剧诗人的特色,作家的热情转化为人物性格的激情,使人物展现着他们内心的隐秘,使观众直接听到他们心灵的声音、深藏的痛苦和叹息。有些人物的台词是可以作为诗来读的。
曹禺剧作的结构,也是诗的。《雷雨》的结构,颇像交响乐的结构,序幕和尾声,尤其是巴赫的弥撒曲运用,不但增加了其音乐感,将你带到一个具有忏悔意味的境界之中,而且由于序幕和尾声,使全剧的意涵更为辽阔和深远。音乐的节奏和戏剧的节奏的交融,使之更具有诗的韵味。
而《日出》,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主旨,采取了大对比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结构,再没有比《日出》的艺术结构更能引起众说纷纭的争论和评价了。有人说:“割去第三幕,全剧就要变成一篇独幕剧”,也有人说,《日出》的结构是“两个横断面,两个印象”;有的说:“第三幕仅仅是一个插曲”,等等。批评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第三幕同全剧的关系上。最早为《日出》结构进行辩护的是欧阳凡海的一篇文章。他说:“不管《日出》在外表上看起来如何没有起伏,如何没有故事的发展,然而事与事,人与人之间的结合,依我看来,决不是任意的,或互不相关的。所谓结构,不事张扬造作的结构,才是真正的结构。”(欧阳凡海:《论〈日出〉》,《文学》第9卷第1号。)在一片对《日出》的异议批评声中,他从整个戏剧的内在联系上把握《日出》结构的特点,这个意见有它的独创之处。
对一部剧作结构的评价,不能脱离开剧作的主题。一个成功的结构必然是充分表达了主题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讲,结构也从来没有固定的格式。只要是富于独创的主题,也必然会带来独特的艺术结构。对《日出》的结构也应作如是观。《日出》结构的卓越之处,在于它用不事张扬的结构深刻地表现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无论是戏的开头和结尾,还是幕与幕之间的互相关联,都紧紧扣住对人吃人社会的揭露和抨击。作家自觉地运用他对社会的认识组织了《日出》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他“自己的哲学”的产物。
《雷雨》的结构,他借鉴了易卜生和希腊悲剧结构的某些因素,他特别想用序幕和尾声的结构形式,叫观众“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回去,心里留下“水似的悲哀”。“欣赏的距离”说还影响着作家。《日出》的结构明确地服务于作家的战斗企图,叫观众想到“什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正因此,作家是按照社会现实的对立斗争的图画结构起他的戏剧大厦。有人说,《日出》的结构颇像高尔基的《在底层里》。的确,《日出》第三幕很像高尔基描写的底层中蜷伏争吵的人们。但是,《日出》的结构不仅描写了底层,更写了上层,在结构的大对比中,揭露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吃人的社会。所以,《日出》的结构是现实主义的结构,也是作家独创的结果。
对于《日出》第三幕,从来没有人否定过。争论的焦点在于有人认为第三幕是个游离的存在,不能成为全剧的“有机体”。这种意见,恰在于它没有从作家的整体构思的内在联系上去认识《日出》结构的独创性。在我们看来,第三幕最鲜明地体现了作家对那个禽兽世界进行激烈抨击的立足点,他是怀着对地狱里生活的人们的深挚同情去评价《日出》中的社会的。他的整体构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可怜的动物”的血泪来控诉和暴露那个不公平合理的社会的。失去了第三幕,《日出》的抨击力量就失去了它深厚的人民性基础。同时,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作家是把陈白露的悲剧同翠喜、小东西的悲剧一起加以考察的。通过这一组形象提出了卖淫制度的问题,从而有了内在的联系。从一般的结构方法要求,中心人物和事件应该始终贯穿不断,但是,曹禺作为一个敢于进行艺术探索的作家,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突破常规,“用片段的方法”和“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在似断实联、似散实聚的结构艺术中,比较完满地实现了创作意图,这显示了他的独创性。作家说:挖了第三幕“等于挖去《日出》的心脏”。作家竭力为第三幕辩护,不仅因为第三幕使他付出巨大的劳动,也因为第三幕确是能体现作家艺术构思及作家审美立场的核心和关键。在作家看来,那些地狱里的人们,最迫切盼望着日出,“最需要阳光”,以此显示“日出”的迫切意义。作家为《日出》结构辩护,显示他的艺术自信心。他坚持的不仅是艺术的创新立场,也坚持了他的战斗的立场。据凤子回忆:在日本演出时,国民党驻日使馆强令删去第三幕,认为“暴露了下层人民生活,有碍国体”(凤子:《在上海》,《文汇报》,1957年12月29日)。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幕的战斗性。的确,删去这一幕,就使《日出》黯然失魂了。
在诗意氛围的创造上,《北京人》较之以前剧作也有新的发展,它把诗意的抒情渗透在整个剧作的世界中而达到更加完美和谐的境界,并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曾家小花厅的格局,把人们带入特定的环境之中。沉重的苏钟,宝石红的古瓶、董其昌的行书条幅、素绵套着的七弦琴……这一切都显得古色古香,全然是一个读书知礼的封建世家的环境。户外传来的嘹亮的鸽哨声,伴以单轮水车“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还有剃头师傅打着“唤头”发出蜂鸣般的嗡嗡声响,更把我们带入旧时北平的生活气氛里,显示着环境的地方色彩。这花厅里的一切,都点缀着这个家庭的历史,也可以烘托出这里的主人公们“徘徊低首,不忍遽去”的情感。大幕启开,逼债的喊声逼迫上来,这个典型环境就显示它浓郁的戏剧气氛,和整个剧情进展,人物的活动交融在一个整体之中。
在《北京人》中,作家把他的人生感,历史感化为自然景物的描绘中,无论是季节、气候、时间,都成为点染和烘托出特定的戏剧氛围,既塑造着性格,又推动着剧情。由第一幕的中秋节正午时刻,到第二幕的中秋夜晚,到第三幕第一景的深秋黄昏,第二景“黎明以前那段最黑暗的时候”。每一幕每一景都具有象征性,蕴藏着作家巧妙的构图企图,都是剧情所必需的自然气氛,我们几乎很难把时间稍加更动。把整个剧情安排在秋风萧瑟万物飘零的秋天,正是这个崩溃衰落的世家的喻象。第一幕是中秋节,不但毫无节日气氛,而是堵到门口的逼债,景与事的反映对比,就蕴含着深刻的讽刺意味。第二幕是凄风苦雨中的中秋之夜暗示着这个破落的家庭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第三幕第一景乌鸦噪晚,正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写照,而第二景,随着方瑞贞的出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晨鸡报晓,预示黎明的前景。而饶有深味的是,第三幕的时间正是曾皓的寿辰,而恰在这一天杜家要把棺材抬走,其讽刺意味尽在不言之中了。在《北京人》中,戏剧的情境是诗的情境,一切景象均为喻象,而一切喻象都寄寓作家的情意,而又是把情意隐蔽在作家所设计的景物之中。
《北京人》在运用象征手法上更为圆熟而丰富。从“北京人”的剪影,到杜曾两家争夺的棺材,从看得见的鸽子,到看不见的耗子,在作家笔下都导演出有声有色有味的戏来,都在强化着感情,加深着意蕴,丰富着韵味,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达到一个诗意隽永的戏剧境界。
曹禺审美意向的转化是自觉的,在民族抗战的年代,不但催促他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反思它的传统的优点和弱点,而且从民族艺术的传统中摄取有益的成分。他曾说:“诗有‘赋、比、兴’,就以《北京人》里猿人的黑影出现的情节说,这种安排就好比是起了诗中‘兴’的作用。有了‘北京人’的影子出现,就比较自然地引起袁任敢在隔房后面那段长话,其用意也在点出这个家庭中那些不死不活的人们的消沉、疲惫、懒散和无聊。”这些,都说明曹禺把传统的诗学融入戏剧创作之中。
曹禺诗的创造兴奋,在写《家》的时候,达到一个高潮,他准备把它写成诗剧,但却未能如愿。他说:“本来想用诗的形式继续写下去,因为感到吃力,所以只写了几段独白。”(《曹禺同志漫谈〈家〉的改编》,《剧本》1956年12月号。)但是,它仍然是一部戏剧的诗。我曾说:曹禺将瑞珏、鸣凤、觉新等人的“‘内心世界的忠实的表达’提高到一种诗化的境界。他把人物的爱情的痛苦不幸和美好向往都升华为诗的情致,熔铸为诗的语言。五四以来的剧作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位剧作家像曹禺这样,把人物的心灵诗意的和爱情的芬芳,刻画得这样细腻迷人。”(《曹禺剧作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8页。)他仍然不甘心,他对诗剧创作的迷恋,决心要把《三人行》写成一诗剧。这出戏是写岳飞、宋高宗和秦桧的故事。“在重庆只写了一幕,太难了,全部是诗,没有别的对话,吃力得不得了。”他还要写诗人《李白和杜甫》,可惜都夭折了。这样强烈的诗的兴奋,在他新中国成立后的剧作中依然透露出来。在《胆剑篇》中,勾践的胆的独白,以及《王昭君》中孙美人的形象,全然是从古诗宫女意象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吴祖光先生称赞曹禺“巧妇能为无米炊”。
我之所以在纪念话剧110年周年之际,论述曹禺在话剧诗化上的成就,是因为其中积淀着中国话剧发展的深刻的经验,或者说是规律。也是为了验证曹禺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席话:“如果我、田汉、夏衍、吴祖光,我们这些人没有中国的文学艺术的传统,是很难啃得动话剧这个洋玩意儿的。”他道出一个道理,中国文学艺术的传统,中国文学艺术的诗化传统,是中国话剧借鉴外国戏剧和创造中国自己的话剧的根基。在我们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之际,曹禺先生的这席话,以及他致力于话剧诗化的实践,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田本相: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蔡郁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