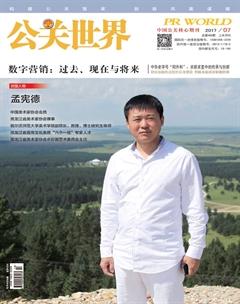宋建明:一位“好色之徒”的色彩之途
冯智军
色彩,如同空气,每个人都司空见惯地身处其中。有这么一群人,在色彩学科里不断地探索其中的奥秘,“好色之徒”,也许是坊间对他们戏谑而恰当的称谓,宋建明就是其中的一员。
宋建明,色彩的研习者、思考者、追问者、实践者和建构者,他将色彩与设计看作一团云,“尽管我们一路上都在走、在看、在思考,但它的边界在哪里?它可能就是盲人摸的那个大象,实在太庞大了,我只能是摸一点认识一点。”从20岁至今,经过40年的反省、实践、迷茫、思考、整理、建构,宋建明再谈起设计、色彩,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迷茫了。“心、眼、图、物、境”与“人、事、物、场、境”,面对这团云般的“大象”,宋建明用了两组10个字作为对内与对外探究方法的钥匙,来概括关于色彩与色彩设计训练及色彩现实营造的方方面面,而这其中,“境”最重要,因为,它与人心、人性及美感紧密相连。在他看来,色彩就是解决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问题。
色彩发生在哪里?宋建明认为就是衣、食、住、行、用、玩、赏、商。“在当今我国的现实社会中,所谓的玩、赏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与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联,与产业关联。回望我们的城市与乡村,尽管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平庸化、乏味现象还是举目可见。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在我们的周遭比比皆是。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色彩是其中一个维度。”宋建明说,我们这个行业不能简单地前行,要在脚踏实地中不时仰望星空、遥望前方,去思考这类问题,做所谓的无为之为、无聊之聊的工作,这大概也是文创领域的学科、专业和行业的特征。
从迷茫中开始探寻之路
1978年,宋建明从福州市美术公司的一名美工考入中国美术学院,学的是染织美术设计专业。宋建明有很好的绘画能力,对色彩也非常敏锐,按理说做好产品设计的色彩应该顺理成章。然而,宋建明从绘画色彩到设计色彩的转化过程并没有感覺到想象中那样的得心应手,总是达不到他预想的效果。“转化的时候我觉得很吃力,虽然不难看,但没有我想象得好。 ”
年轻时宋建明深为苦恼,总觉得应该有规律可循,他凭着一股血气,立志非搞明白色彩究竟不可。于是他带着问题求教很多的师长,但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答复。再翻阅书籍,当年色彩学的书籍少且浅显,也是空手而归。于是他就开始再扩大到外文书籍中继续探寻。大学里学的是日文,于是他就靠着课堂所学,连猜带蒙地从日文的色彩学文献里找到碎片化的线索。当然,中国美术学院一直有“读书养心,劳作上手”的传统,于是他就一边模仿着实验,一边继续追寻规律,从传统中国色彩又追索到了包豪斯的色彩教育,再追到了现代色彩科学技术体系。从大二开始,宋建明就利用了所有的课余时间边琢磨边实验,慢慢地勾勒出了一个设计色彩学的 “云团”。也正因为他这种钻研的劲头,被系里的领导和老师们看中,毕业后他留校继续研究色彩。
1985年,学校决定选派宋建明等人去法国学习。临行前,前来讲学的赵无极先生告诉他,法国最好的设计学校就是他任教的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以下称装饰艺术学院)。因此,抵达巴黎之后,他与同行的王雪青商议,一同放弃法方为他们安排的马赛美术学校,设法进入装饰艺术学院。但这个学校的录取门槛非常高,是教授治校,必须有法國教授接纳才行。人生地不熟的宋建明,只好硬着头皮“硬闯”,看情况再议。
到了装饰艺术学院里,宋建明怯生生地走进一间教室旁听,授课的正是创立“色彩地理学”的著名色彩学家、色彩设计大师让·菲力普·郎科罗。课间,郎科罗教授发现了一张陌生的东方面孔,便特别感兴趣,原来他年轻时去过日本留学,宋也能够用日语与之交流,按照宋建明的说法:“就是缘分!”郎科罗教授当场就在宋建明的推荐书上签了名,从而使得他顺利入校开始了西方色彩学体系的学业。郎科罗教授可谓是他的“贵人”,引领他进入他的“3D色彩工作室”实习,让他对法国乃至欧洲时尚色彩及其设计的方式、方法和规律有了直观的认识。在欧洲留学期间,宋建明走过很多城市,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拍了几千张幻灯片。
在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听到西方教授倡导文化的身份,这开启了自我色彩文化身份的辨识,于是,宋建明结合东西方乃至更多元的色彩文化体系进行了解构、比较和创新的理解和认知,从而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色彩之路。
在现实语境中创新色彩体系
1990-1993年,宋建明再次应装饰艺术学院邀请前往做色彩研究与讲学。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如火如荼,而大拆大建、对色彩的漠视、建筑品质的平庸等隐忧也开始凸显。回国后的宋建明做了很多讲座,针对现实状况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虽然很多人包括许多地方领导听了都说好,但却没有人去找他做顾问来进行建筑群落的色彩规划。
直到1998年,杭州的湖滨地区要进行城市改造,感觉细腻的杭州建设者发现了城市片区中还有色彩问题需要专项的处理,于是找到了宋建明。当时的他似乎“已经不太有信心了,认为中国找不到专门关心色彩问题的人”。现在有了机会,宋建明自然要抓住机会小题大做,把在西方所学的“屠龙”技术都充分地用在这个小项目上。这个今天看起来很短时间就能做好的事情,他花了很多的精力,热身的同时,借题发挥,由此慢慢让很多人对城市色彩规划有了了解。
到了2003年,学习城市规划出身的时任龙泉市市长梁忆南找到了宋建明,请他做龙泉市的色彩规划。这是新的机遇,同时也是新的挑战,因为此刻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宋建明采用了正宗的 “色彩地理学”方法来应对这9平方公里的龙泉城市,心想一定顺利,可现实恰好相反,他怎么也组织不出龙泉城市主色调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与分析,他发现了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非常大的不同。西方城市肌理形貌非常稳定,历史脉络清楚,而中国城市形态非常复杂,既有明清民国流传下来的老片区,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老城区,还有改革开放后的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城市早已失去了所谓恒定的主调色。
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办法,宋建明开始思考,既然这种情况下主调色的理论不成立了,那就创立一个主旋律理论。“城市问题总是复杂的问题,如果把它理解成凝固的交响乐,可解释的话语就比较多了,主旋律、副旋律、背景音乐、华彩乐章、主调、复调、单调等,正好可以对应现在的城市问题。”宋建明就从龙泉找到了三段主旋律,即明清、老城、新城。导师郎科罗教授也非常肯定他的這种想法,因为他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只有在中国才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提倡“我的办法就是创造办法”的郎科罗告诉宋建明:“你应该用你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你面临的问题。”
“文化是一种由认知到体验再到思考的过程,它涉及传承、琢磨、把握与创新等等方面。我和团队应邀进入任何一座城市或者乡镇,我都时时告诫我的小朋友要如履薄冰、诚惶诚恐地对待城市色彩问题,凡事须先静下来,琢磨此地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条小巷,以及土壤、气候、植被、人性,找到这里边的乡愁。”这种态度,也许是宋建明创造他自己方法的一个法门吧。
从“杭州灰”到“水墨淡彩”的背后
当宋建明的色彩主旋律理论产生并成功实践后,就像是一个拐点,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城市色彩规划。2005年,杭州市政府邀请宋建明对杭州市进行整体的色彩规划研究。宋建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对杭州形态了如指掌,然后提出了方案。公示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当时有两个课题,一个是东南大学的城市轮廓线,一个是宋建明团队的城市色彩。虽然轮廓线比色彩更重要,决定着城市的基本形态,但色彩对普通人来说比较新鲜,因此后者格外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
备受媒体追捧的宋建明在采访时说,杭州是由若干组细腻的灰色系组成,然后就有媒体以“杭州灰”为醒目的标题进行了报道。如此一来,很多公众对“杭州灰”表示不理解,进而非常不滿,为此,杭州市规划局专门组织了市民代表和宋建明进行沟通交流解惑。当宋建明从学理到调研再到规划的过程进行解读后,特别是当市民代表了解到,新的城市色彩规划是通过调研拍摄的两万五千张涵盖杭州各个角落的照片进行认真分析后作出的,公众理解了。
事情虽然解决了,但给了宋建明很大的触动。“我是来自美术学院的人,说到灰色系,美院的人都很清楚,但是没有考虑到普通民众对这个概念的模糊。也因此理解到,学术话语和公众话语不是一个话语体系,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是为人民服务,那就要让人民认可。怎样让人民认可,就要用公众话语。”当宋建明重新用杭州水墨淡彩进行表述后,公众的激情再一次被点燃,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杭州色彩规划大获成功之后,宋建明更是声名鹊起。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色彩的重要性,而宋建明和他的小伙伴到目前也已经做了60多个城市和片区的色彩规划。“我们已经对中国的6000平方公里编制过色彩规划。这个过程是不断遭遇问题,60多个城市、60多种城市性格、60多种状况,包括要接触到地方政府官员、文化名流、原住民、游客、投资人、产业人等所有与之相关的人。而且每一个地域里的历史渊源、产业特征和发展策略都不一样,城市色彩的策略也不一样。”宋建明说,“遭遇的问题复杂,思考自然要更深入,创新也持续着。这样下来,到今天基本完成了一个基于中国城市现实的色彩规划与营造实践的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