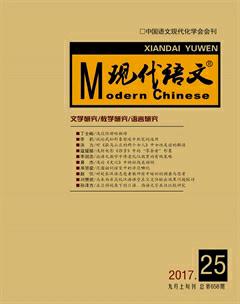《死水微澜》中邓幺姑人物形象浅析
摘 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女性意识一直被束缚在传统道德的观念里。《死水微澜》讲述了清朝末年四川省会成都及其近郊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历程,展现了小镇上一群普通民众的悲欢离合,塑造了性格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邓幺姑这一形象贯穿始终,是一个“多面体”的女性主体形象。在历史更迭的交界处,她挣脱封建社会的禁锢,追寻心底的理想生活,凸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文章将基于该作品的人物形象、对封建社会女性意识的传统定义进行初步探究。
关键词:死水微澜 蔡大嫂 女性意识
一、生命本体的跃动——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
《死水微澜》叙述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的七年时间里,成都郊外的一个不起眼的天回镇里林林总总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具体展现了这个“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中潜在的重重危机,故事情节中融入了一定时代的特质和“沧桑”变迁,呈现了历史轴画中引人入胜的部分。小说从小视角切入,阐述的问题仅仅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所在。与此同时,那段飘忽不定的历史年代被重现,中国靠礼教维持的封建社会即将走向土崩瓦解,而资本主义利欲熏心的企图也在扩张,中国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小说里,许多男女形象被描绘得各具特点,然而,最成功的还是对邓幺姑(蔡大嫂)的人物塑造。
小说中塑造最为成功的“典型人物”是邓幺姑(蔡大嫂)。她本是一个生活在小村庄极为普通的姑娘,但她在小时候便散发出一种有别于一般村姑自我执拗的个性,连她的父母也束手无策。邓幺姑的性格内蕴丰裕而繁杂,并且热情如火,近于放纵轻浮;利落能干,心地善良又不乏势利;面对需要处理的事情,她敢于通过哭、闹、说、笑、骂的方式去表达,却又始终把个人利益置于首位;放荡不羁,泼辣豪爽却也不乏温柔似水,四川女性之“辣”完全融入她的性格中。光明与黑暗、叛逆与贪欲、泼辣与善良巧妙结合在一起,成为她生命中矛盾又独特的精彩历程。
从传统男权文化角度来看,农活,农田,农村和她有着天然和必然的联系,似乎她也要同农民一样被束缚在田垄之间,一辈子也不会有大的改变,随着时间推移会为人妇,为人母,成为男人背后价值极高的“辅助用品”,“这种‘附庸身份和地位似乎是祖祖辈辈传统父权社会中女人必然的生命轨迹。”[3]而蔡大嫂却与之截然相反,她无所畏懼男权统治下的身不由己,并且做出了不同现实情况下自己命运的巧妙转变,似乎她拿着自己的生命之笔在自由描绘。她小时候的名字叫邓幺姑,父亲在她半岁的时候就与世长辞了,之后随母亲改嫁到成都近郊的农户邓家。继父对她甚是喜欢,不舍得让她做一点儿粗活,而“细路活”却成为她的拿手活儿。她倔强有主见,心高气傲。作为农村女孩儿本是不需要裹脚的,她却坚持裹脚,痛得整夜不能睡安稳,母亲看着女儿遭受这样的疼痛,劝阻她不要继续缠下去,幺姑反倒生气:“你管得我的,为啥子乡下人的脚,就不该缠小?我偏要缠,偏要缠,偏要缠!痛死了是我嘛!”[2]生动的言语和形象的动作,使邓幺姑的个体形象被刻画得恰到好处,既体现小孩子的童真,也不失其个性。她甚要强,这与她饱受生活苦难的母亲遵从隐忍的人生价值观截然相反。她倔强,有本能的自主反抗意识,可惜的是,她的这种竭力反抗正好反映了她思想上的“世俗”,裹脚不仅是残害身体的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健全,是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在人的思想上打下的深深烙印,是女子不公平地位的印证。“她顶喜欢听二奶奶描绘成都,尤其令邓幺姑神往的,就是讲到成都一般大户人家的生活,以及妇女们争奇斗艳的打扮。”[4]二奶奶说:“幺姑,你有这样一个好胎子,又精灵,说不定将来嫁给城里人家,你才晓得在成都过日子的味道!”[2]从此,她不再甘心作一个乡间默默无闻的普通少女,“成都的幻影,在邓幺姑的脑中,竟与她所学的一针一线,一天一天地进步,一天一天地扩大,一天一天地真确。”[2]
她对于未知的将来同《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相似,充满了对繁华都市上流社会生活圈子的向往和渴望。所以,韩二奶奶的突然离世,除了带给她伤心欲绝的悲痛,还使她的那颗对于成都生活充满渴望的幼小心灵不知所措,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邓幺姑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指导者,也是带她走进繁华新世界的“领路人”,正是韩二奶奶对成都繁华的细致讲述,才使得一种物质生活方式被一个不谙世事的乡间少女所倾慕与寻求。
二、爱情欲望的迸发——女性主体意识的成长
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是抑制个体的,且崇尚禁欲主义。周华说过:“由于历史的机遇,现代文学史上每一位作家都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冲突中生存和创作。”[5]李颉人便是典型的例子,他身上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巴蜀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化的碰撞才赋予蔡大嫂独特的性感,个性,理性。如果她能像千千万万的传统中国妇女一样,一生守妇道,不知情为何物,只懂得吃穿二事,傻乐呵一辈子,痛苦何来?可是她漂亮,性感,叛逆,这些却成了她的过错。文中女性原始的不驯服性情和生命力度恰恰讽刺、嘲笑了父权文化的正严颜色和对女性个体的生命压制,闪耀出女性特有的生命魅力和对个体价值的找寻。蔡大嫂未能嫁到成都大户人家,勉勉强强地接受了规规矩矩在乡镇上做一个掌柜娘的身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的蔡大嫂产生了对平淡生活的厌恶,生活的基本保障和安逸是“婚姻”可以带给蔡大嫂的,而这种恬淡是暂时的,因为,这种作为一个人对于“情”和“欲”的需求却被婚姻遮蔽了。她的男人蔡傻子根本给不了她这些,而罗歪嘴却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在作品中,“他是一个而立之年的老光棍儿,方圆八九十里,只要以罗五爷一张名片,尽可上下吃得通。”[6]
小说里把蔡傻子和罗歪嘴塑造成两个极端的男人,一个少言寡语,一个能摆龙门阵;一个孤陋寡闻,一个见多识广;一个贪财吝啬,一个仗义疏财;一个唯唯诺诺,一个浑身是胆;一个了无情趣,一个富有情趣。总之,蔡傻子憨厚实诚,罗歪嘴精明有余。两者相比较,蔡大嫂心中的矛盾油然而生。丈夫对她的爱不能满足她,她也不会全然感知,她爱的男人却在婚姻殿堂之外,这是她的苦楚,她该如何是好?她只向罗歪嘴说了一句:“花露水的香,真比麝香还好!”不过几日,罗歪嘴准给她从省城买回。其余的吃喝穿戴,只要她看见了,觉得好,无论多么贵,总在几日过后,如愿以偿。罗歪嘴洒脱自由的人生态度与蔡傻子的实诚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在比较中,她无所畏惮地爱上了罗歪嘴——丈夫的表哥,而厌弃木讷老实、一心只知道经营店铺、拨弄算盘的蔡傻子,从此开始了一场漫长与短暂并存的情欲放纵与满足。
“而在这场情欲的追逐过程中,引起她的情欲梦想中的女性意识发芽的则是一个敏感又多情的风尘女子——刘三金。”[3]蔡大嫂觉得比不上刘三金,一是自己才学疏浅,二是自己未曾真正爱过,三是没有得过别人的情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她的实际生活中,缺乏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为了幸福,她随时可以对婚姻道德表示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蔡大嫂在这个“榜样”的指引之下,将心底渴望的爱欲抽离想象,直接转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所在。他们都住在了彼此的心里,在他眼里,蔡大嫂通情达理,又不野,“很合口味”。“他们竟然能将私情公之于众,旁若无人地去赶集、逛青羊宫,在人们的面前眉来眼去,没有遮遮掩掩,他们的这种赤裸裸的、如火如荼的相爱方式对于世俗的社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也得到了男人对她的恭维和赞不绝口。”[3]罗歪嘴的体贴,以及缠绵,更是她从未想象会成为的真真切切的事实。被爱者也是爱人者,于是“她从心底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和爱慕,所以用又温热,又热烈,又真挚,又猛勇的爱情来报答他,烘炙他”。
蔡大嫂同《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爱玛有着相似之处,她们的个体生命热力得到了极大张扬。从少女的纠结和青春的憧憬,到成为掌柜娘蔡大嫂后的婚姻的幻灭与不安于现实静如止水生活的内心狂躁,又到成为罗歪嘴的情人,她的感情轨迹在不断变化着。存在主义认为,“当一个人从社会的各种“角色”中退出,直面自己的时候,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自由的人。”[1]据此来讲,蔡大嫂和罗歪嘴之间的爱是世间最寻常也最不寻常的爱。在世界发生突如其来的变化时,爱情被冲击之后,一贯特立独行的蔡大嫂的女性自主抉择意识再次在关键时刻显现出来。
三、逆流而上——突破传统的女性主体意识
《死水微澜》中蔡大嫂的性格有泼辣、野性的一面,她的一系列举动在男权社会看来都是不守妇道,违背社会的,是封建卫道士眼中的“世道不同了”的行为。而同时,她的每一次转折都是巧妙借助男性来完成的,并非是脱离男性而彻底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主。这与她农村出身未受教育的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她的独立意识是挣脱世俗世界而独立存在的。在文中,她的选择无不与男性世界相关,因为蔡大嫂是凡俗中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蔡大嫂将物质和情爱欲望的双重实现变成了对现实的把握,而当这一切都被她满足了之后,在新的“外力”的助推之下,生成了她生命之中又一轮欲望和追求的循环轨迹。
顾天成,不仅是大粮户,且是吃洋教、有钱有势的人,因借洋教势力报复罗歪嘴,罗歪嘴不得已背井离乡,兴顺号被一扫而空,无辜的蔡兴顺被抓走,蔡大嫂被兵丁打得头破血流,要多惨有多惨,和往日光彩夺目的她形成鲜明对比。在回娘家养伤期间,蔡大嫂变得呆板,冷漠,不愿意讲话。于是,权势的重要性被失势的蔡大嫂重新认识:要想蔡傻子能得救,自己的富足生活能够长久,金娃子的似锦前途能保障,有权有势是最重要的条件了。于是,她再一次有了对权势的追逐心理,不惜以自己的婚姻作交易。
一个未见过面的生人能一见就爱吗?这次的选择于她而言是自我的大胆尝试。在与顾天成的数次“交易”中,她以自己的容颜为诱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追求权势救丈夫与情人。“怎么使不得?只要把话说好了,可以商量的!”商量的结果是:蔡大嫂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白纸黑字的成文条件,且除了顾天成加盖脚模手印外,还需要其他人担硬保。她也不许顾天成和罗歪嘴记仇恨,同蔡兴顺也要有日常来往,协调缓和了三个男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证明,蔡大嫂不可能再有任何反抗,只有现实层面的自我救赎罢了,因为,她已经由一个认真追求个人幸福的人而蜕变成一个老练世故的妇女形象。面对这么刻薄的条件,生性好色的顾天成竟满口答应了,足见蔡大嫂的个人魅力之所在。而她呢?“她仅仅答应了一件:在蔡兴顺出来以后就嫁给他。附带的是,仍然要六礼三聘,花红酒果,像黄花闺女一样,坐花轿,拜堂,撒帐,吃交杯,一句话说完,要把事情打响!”她那执拗倔强、不安本分的欲求从这些言谈举止、思虑谋划中被表现出来,这欲求是她的生命动力,是她野性性格特征的表达,是她改变自己命运的奋斗之源。她对于自己的选择有着正当的理由:“哈哈!只要我顾三奶奶有钱,一肥遮百丑……怕哪个?”蔡大嫂的三次婚恋,经历了妥协——反抗——妥协的过程,好像完成了生命的一个轮回,似乎是失败了,而她光彩照人、魅力四射、风情无限的女性形象也终于如雕塑一般屹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长廊中,被世人借鉴。
四、结语
“传统的情爱书写往往将女人置于非人的地位,女人只是非本质的存在。在女性成长过程中,获得本质特征需要一个肯定的过程,男人的承认和肯定是女性被认可的重要仪式,男人是女人成长中的导师和引路人。”[7]在文中,蔡大嫂的三次婚恋转折中足以显现出三个男人对她的“引导”。上天总是公平的,关闭一扇门时,总会打开另一扇窗。她泼辣的性格里少了些许浪漫主义色彩,而在遇到事情时,却可以具体分析,能变通事实,能遵循内心去反抗,能用理性大于感性的方式去处理,能用最合理的方式得到想要的一切。
自古以来,姑娘便只有静听父母做主的了,要姑娘本身出来有所主张,这似乎也是骇人听闻的大事。蔡大嫂改嫁顾天成,冲击着传统道德观,放荡不羁,无耻卑鄙等一系列“品行太差”的评价标签被贴在她身上,我们不应该以最传统的视角局限这一个充满顽强抗争力的鲜活时代女性的抉择。她的改嫁也是对传统的妇女道德观的全新阐释,是她多面性格中闪烁光芒的一面。父母实在不理解,而她为了心底荣华富贵的蓝图,做出了自己最“恰当”的选择,体现了蔡大嫂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這是李颉人受到“五四”新文化影响后,将新文化的“新”集中在独具特色的蔡大嫂身上,有着跨时代的先驱意义。蔡大嫂泼辣直爽的性格,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她穿越世俗,逆流而上,在“死水”般的天回镇激荡起阵阵“微澜”。
正如郭沫若所说:“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凭借着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世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8]李劼人是一个缄默、严肃的写实主义者,他总是一贯严格地要求着自己缜密地、生动地、具体地描写他看到的、感知到的现实生活,历代被众人所瞩目的帝王将相和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李劼人笔下少之又少,反而一些社会边缘地带的边缘人物在他笔下熠熠生辉,有了新的活力。他赋予蔡大嫂这个女性生命以张力和热力,大胆挣脱男权统治的禁锢,生成一个独立自主、勇于驾驭自己命运的女性形象,在男权社会里占据一方天地,使女性现代意识被重建。在当代社会中,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校秋林:《试论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小人物形象》,文教资料,2015年,第7期,第8页。
[2]李劼人:《死水微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李彦凤:《冲破男权统治的藩篱——论<死水微澜>中蔡大嫂的女性主体意识》,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9年,第8期,第109页。
[4]李直飞:《龙门阵里面的“死水微澜”——<死水微澜>中龙门阵文化的探析》,当代文坛,2011年,第z1期,第69页。
[5]周华:《李颉人文化心理的形成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
[6]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7]杨永忠等:《论女性主体意识》,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9页。
[8]张中良:《李劼人的辛亥革命叙事》,当代文坛,2011年,第z1期,第19页。
(刘畅 内蒙古包头 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 014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