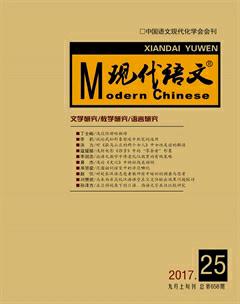明清时期《香囊记》民间舞台演出研究
摘 要:《香囊记》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很重要的一部戏曲作品,自问世以来,学界对其思想性及艺术性多有指摘,就《香囊记》文本而言,这些指摘是中肯的。但由于朝廷的戏曲政策及部分文人的推崇,《香囊记》仍然在民间舞台上搬演了300余年。文章将考索明清以来《香囊记》在民间舞台的演出,并探究其流传因素,以求对《香囊记》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明清时期 《香囊记》 舞台演出
《香囊记》是明代较为重要的一部戏曲作品,一出世便饱受争议,其中以批评居多,例如明代徐复祚在《曲论》中说:“《香囊》以诗语作曲,处处如烟花风柳。如‘花边柳边‘黄昏古驿‘残星破暝‘红入仙桃等大套,丽语藻句,刺眼夺魄。然愈藻丽,愈远本色。”[1]不过也有文人对《香囊记》表示赏识,吕天成在《曲品》中称赞它“选声尽工,宜骚人之倾耳;采事尤正,亦嘉客所赏心。存之可师,学焉成套……词工白整,尽填学问。此派从《琵琶》来,是前輩中最佳传奇也。”[2]并将其放在了妙品一列。《香囊记》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与《琵琶记》这类一流作品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不过它仍然在民间舞台上流传了300多年。
到目前为止,《香囊记》的研究虽比不上荆、刘、拜、杀这类经典作品,但从1980年吴国钦的《八股戏<五伦全备记>与<香囊记>》到现在,林林总总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论文,没有研究专著,有些戏曲史或文学史中会有涉及,内容都是简单介绍作者及戏曲情节,然后评价一下这部作品,评价之语一般都不超徐复祚、徐渭的观点,批评《香囊记》的文辞及思想。论文中研究较多的是《香囊记》的语言,例如马琳萍的一系列文章《<香囊记>与八股文关系之研究》《从<香囊记>中的传注语看程朱理学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影响》《从用典看<香囊记>对八股文的模仿与借鉴》,张仁立的《<香囊记>的语言特征》、张宇芬的《试论邵灿与其<香囊记>》及一些研究骈俪派文章中的部分内容。另外关于《香囊记》的作者、创作时间的文章也不少,如吴书荫的《<香囊记>及其作者》、黄仕忠的《<香囊记>作者、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马琳萍、侯凤祥的《邵灿生平及<香囊记>创作时间考辨》等。王良成的《明清时期的<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接受考论》与其他研究不同,是从戏曲选本的角度考察《香囊记》的传播。不管是作家、作品还是选本的研究都是文本的、上层的研究,本文将对《香囊记》在民间演出这部分作一个探索,以求对《香囊记》的研究有所补充。
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到:“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3]“三吴俗子”,是指那些依仗家室豪富,故弄风雅的人,《香囊记》通过他们家班的搬演,一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明代小说《金瓶梅》中有不少戏曲演出的情节:西门庆令后边取女衣钗梳与他,教书童也妆扮起来。共三个旦、两个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记》……蔡状元又叫别的生旦过来,亦赏酒与他吃。因分付:“你唱个《朝元歌》‘花边柳边。”苟子孝答应,在旁拍手唱道:“花边柳边,檐外睛丝卷;山前水前,马上东风软。”[4]这段内容中的《朝元歌》出自《香囊记》第六出“途叙”,这虽是小说情节,但也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观照一二,可以看出《香囊记》在民间演出中还是有一定空间的。以下是笔者所见明清时期《香囊记》民间舞台演出的情况,现大体按时间排序并简单说明。
1.潘之恒在《鸾啸小品》卷三中记载:“金娘子,字风翔,越中海盐班所合女旦也。余五岁时,从里中汪太守筵上见之……试一登场,百态轻盈,艳夺人目。余犹记其《香囊》之探,《连环》之舞,今未有继之者。虽童子犹令销魂,况情炽者乎?”[5]潘之恒生于1556年,5岁那年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当时汪道昆从襄阳知府任上回乡徽州省亲,请了一个海盐班演出,班中有位叫金凤翔的女演员,在《香囊记》和《连环记》中的表演十分出色,可见《香囊记》在徽州的演出情形。
2.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中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月初四记载:“做《香囊记》,黄昏散。”[6]《玉华堂日记》是潘允端卸职回到家乡上海的一系列活动的记录,其中有大量戏曲活动的内容,演戏场所主要在潘允端为其父建的豫园中,几乎是“无日不开宴,无日不观剧”,当时流行的剧目几乎都有上演。
3.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中记载:“初八,晴……玄静主人相陪正筵,就座已迫暮色。吕三班作戏,演《香囊记》。席散,夜已半矣。”[7]根据凌濛初年谱对照得出,冯梦祯是万历三十年(1602)十一月初八到凌濛初的家乡晟舍,同观吕三戏班演出的《香囊记》。
4.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记》中记录了许多他的戏曲活动,祁彪佳分别在北京和绍兴观看《香囊记》演出3次:崇祯五年十月初九日“再赴刘汲韦席,同席皆越中亲友也,观《香囊记》”[8];崇祯六年二月十五日“观《香囊记》,客散,已鸡鸣矣”[9];崇祯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观《香囊记》”[10]。通过对其《日记》中观看剧目的统计,《拜月剧》《彩楼记》《绣襦记》《西楼记》《双红记》《浣纱记》观看了4次,接下来就是《香囊记》《百花记》《连环记》《花筵赚记》《石榴花记》《红拂记》《鹣钗记》各3次,其他还有91部作品观看了1次或2次不等,从频率上也可以看出《香囊记》在当时较为流行。
5.明代崇祯八年(1635)刊刻的陶奭龄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记载:“如《四喜》《百顺》之类,《颂》也,有庆喜之事则演之;《五伦》《四德》《香囊》《还带》等,《大雅》也;《八义》《葛衣》等,《小雅》也,寻常家庭宴会则演之;《拜月》《诱襦》等,《风》也,闲庭别馆,朋友小集,或可演之。至于《罢花》《长生》《邯郸》《南柯》之类,谓之逸品,在四品之外,禅林道院,皆可搬演,以代道场斋醮之事。若夫《西厢》《玉簪》等诸淫媒之戏,亟宜放绝。禁书坊不得鬻,禁优人不得学,违则痛惩之。亦厚风俗、正人心之一助也。”[11]由此可见,当时士绅的家庭宴会中《香囊记》几乎是必点之目。
6.在徽州乡村楹联手抄本中有关于《香囊记》演出的记录:“小小香囊包藏一家孝义,巍巍使节把持万古纲常。”[12]“手抄本封面有‘大清国江南徽州府休宁县和睦乡轻财里磺川忠具字样,看来抄录的时间应在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设立安徽省之前。”[13]所以这本楹联手抄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康熙六年之前徽州乡村的戏曲演出情况。王玉瑜的《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演剧》中对徽州乡村楹联手抄本中涉及的戏曲作品进行了统计:“目连”联102副,“苏秦”联23副,“伯嘈”联58副,“蒙正”联36副,“刘智远”联33副,“班超”联19副,“韩信”联15副,“孤儿”联15副,“荆钗”联14副,“冯京”联8副,“窦滔”联6副,“姜诗”联8副,“董永”联6副,“阂损”联6副,“王祥”联6副,“商格”联8副,“裴度”联6副,“范唯”联3副,“香囊”联9副,“朱弃”联21副,“武王”联7副,“昭君”联9副。[14]《香囊记》的楹联有9副,这个数量排在中等,楹联的数量不代表演出次数,不过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当时戏曲的演出情况。
7.清代文学家褚人获的《坚瓠集》卷二有“剧目诗”一节,记载:“辛未夏日观女优演杂剧,亦集成四律”[15],其中第三首是“《金雀》衔环《义侠》奇,《赠书》《双捷》报家知。《香囊》拟贮《珊瑚块》,《玉合》还藏《琥珀匙》。《孔雀》屏开《三桂》候,《芙蓉影》畔《四贤》祠。《锦衣归》第《满床笏》,《吉庆图》成《题塔》时。”[16]《坚瓠集》首集完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后面的逐年完成,最终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全部编成,《香囊记》也是作者所观剧目之一,所以清康熙年间《香囊记》仍在上演。
8.陆萼庭根据创刊清同治十一年的《申报》以及《字林沪报》等旧报上的戏目广告整理编写了“清末上海昆剧演出剧目志”,其中就有《香囊记》“看策”一出。另外《上海昆剧志》一书中整理的“传统剧目演出表”中也记录了《香囊记》“看策”这出的演出。现将《上海昆剧志》中“传统剧目演出表”的一部分摘录如下:
9.连台大本戏《岳传》(亦叫《搬金牌》)“朱仙镇”一折中的“老鼠告猫”便出自《香囊记》。《岳传》最早在何时何地由何戏班演出,这还有待查考。“据许多老艺人回忆,清光绪年间至清末,恩施的江湖南剧班‘天福‘同庆班,以当家生角何五、张玉福为首,会同‘天元‘连升科班的出科艺人袁天魁、费连喜、费连和等,先后在来风、鹤峰、咸丰、恩施、建始等地演出过《搬金牌》。”[17]所以光绪至清末年间,《香囊记》随着《岳传》的搬演而在民间流传。
上面的9条《香囊记》演出材料记载中,前5条都是明代时的演出记录,第6条徽州乡村楹联手抄本,抄录的时间是在清代,但那些楹联创作的时间无法确定是明代还是清代,或者两者皆有,所以这条材料记录的演出时间不定。最后3条材料是清代时《香囊记》的演出记录,从材料比例上可以看出《香囊记》在明代时民间演出较为流行,尤其是在文人圈内。《香囊记》文辞藻丽,以古诗、典故、四书五经入曲,其实不利于舞台表演,但这样一部不适合搬演的作品,仍然在舞台上搬演了300余年,究其原因主要有2点:国家政策引导、部分文人的推崇。
1.国家政策引导
明代关于戏曲的政令有不少,但对民间戏曲搬演内容有直接影响的只有一条:“凡乐人搬作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义及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18]这条禁令是明太祖于洪武六年二月颁布,洪武二十二年又将内容进行扩充写入了《大明律》,之后《大明律》几次增订,直到万历年间《大明会典》成书,该禁令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从禁令的内容看,“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不许搬演,但“神仙道扮义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止之列。由此可见,朝廷并不是想禁止民间演戏,而是想将民间演戏内容往正统思想上引。另外太祖还对《琵琶记》极为赞赏,“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19]朝廷推崇《琵琶记》,看中的是它的妻贤子孝,关乎风化。
这一禁一扬,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民间尤其是文人圈内的戏曲搬演,弘治末年许相卿倡乡约“歌舞俳優……戏剧烟火、一切禁毁。虽乐宾、怡老、娱病,亦永勿用”。[20]这类内容的乡约还有很多,可见将戏曲看作教化的载体成为明代许多文人的共识。在这种大环境下,《香囊记》的搬演在文人圈内大受追捧也是大势所趋。
2.部分文人推崇
古代文人一向视诗文为文学正统,视词曲、戏曲为小道,是对文学正统的侵扰。而《香囊记》不仅内容极具教化意义,而且文辞典雅。邵璨将应制时文融入戏曲,这些都是科举文人极为熟悉的内容,所以理解上不存在困难。又将历代儒者认为可以讽谏士、风妇德、美政教、敦人伦的《诗经》,以及饱含忠君爱民情怀的杜诗运用入曲。邵璨将戏曲创作视为文人才情的体现,于是以文言为宾白、以典故为对仗,试图从中反映出自己的才学。这种做法,在文辞方面符合了文人以雅为美的传统审美要求,以时文入曲来阐发议论、增强说教,符合文人在“道统”与理学观念指导下的艺术价值判定标准,文人群体的情趣、才识、思想均可以从中表现出来。所以《香囊记》被许多文人视为文雅,而且其中的曲词、宾白,普通百姓是听不懂的,观看《香囊记》的演出也可以彰显自己的才情。于是就像徐渭《南词叙录》所言:“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21]
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邵璨的《香囊记》虽然不是一流作品,在戏曲批评中也多受指摘,但不可否认,它作为教化剧的代表之一,在戏曲史甚至文学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明代文人圈中《香囊记》的频繁搬演便可见一斑。《香囊记》的艺术性、思想性、表演性无法与《牡丹亭》这类一流作品相较,但其民间舞台演出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这类教化剧的流传因素也可以从中窥探一二。
注释:
[1]徐复祚:《曲论》,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36页。
[2]吕天成:《曲品》,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28页。
[3][21]徐渭:《南词叙录》,见俞为民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486-487页。
[4]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505页。
[5]潘之恒:《潘之恒曲话·金凤翔》,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6]杨慧玲:《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7]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8][9][10]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第638页,第758页。
[11]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明崇祯八年刻本。
[12][13][14]王玉瑜:《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演剧》,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8页,第25页,第24页。
[15][16]褚人获:《<坚瓠集>第一册丁集卷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页,第483页。
[17]鄂西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鄂西文史资料>总第13辑》,恩施:鄂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年版,第36页。
[18]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19]徐渭:《南词叙录》,见俞为民等主编:《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第一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483页。
[20]许相卿:《许云村贻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王美玲 江苏徐州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