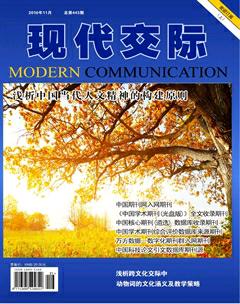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学科分类与人文教育
姚兴富

摘要: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伴随着知识的分科化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科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逐渐明晰。人文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运用规范性的方法、不回避价值判断、企望崇高理想。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批评意识、自治能力而又全面发展的人。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人文科学在当代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中的领地被收窄、作用被弱化。恢复人本主义的精神、重建人文教育的体系是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键词:西方文化传统学科分类人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1-0018-02
在人类文化的早期。并无明显的学科分类,所谓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都是杂糅在一起的。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不同领域知识的区分逐渐明显。学科分类也日益多元细密。其中人文知识是探究人的本质和价值等问题,应该说尤为根本和重要。本文梳理西方文化传统中学科分类的大致过程。旨在唤醒人们充分认识人文教育在促进人的完善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科分类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认为各种工艺都是低贱的、机械性的学习,这些并不是可以达到所寻求的那种善的学习。亚里士多德把科学(science)划分为三类:一是实践的(practical)科学,相关的学科有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二是生产的(productive)科学,此类学科有各种技艺和修辞学等。三是理论的(theoreti-cal)科学,都是关涉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包括物理学、数学和神学。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较之于柏拉图更明晰和更系统一些,但他们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学科分类的标准都是以某类学科与存在本身的亲疏远近关系为依归的。
到了欧洲中世纪,学科分类更加细密规范。中世纪的大学以神学、法学、医学为主导学科,在进入专门学习这三科之前,要接受从古希腊沿袭下来的“七艺”(文法、修辭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等核心课程的教育。“学生修完语法、修辞学及逻辑学‘三艺后,方可被授予学士学位。硕士和博士则是修完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四艺后,以及修完其他三科,才可获得执教的资格。”
19世纪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认真审视了自然科学(the natural sciences)与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的知识论前提。他认为这两种科学都是从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出发的。自然科学通过外部的观察和测量去建构一个客观的世界。而人文科学利用内在和外在的生活体验去定义一个历史的世界。19世纪中后期,“科学”一词的内涵变得越来越狭窄,仅指物理或实验科学。
1959年,英国科学工作者兼小说家斯诺(1905-1980)发表演讲并提出有关学科分类的“两种文化”(two cul-tures)的说法:一组是由文学知识分子组成,另一组是由物理科学家组成。四年后,斯诺发表了关于“两种文化”的第二次演讲,他承认忽略了“第三种文化”的出现。即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欧美的各大学中从事社会研究、应用研究、专业研究和职业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而他们的研究对象既不属于“人文”领域也不属于“科学”领域。
针对斯诺学科分类观点的缺陷和偏颇,美国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卡根指出。大多数知识活动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一,要有一套不容置疑的前提或假设,它使得某类特殊问题及其解答具有优先权。二,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针对所得证据的分析工具。三,要有一套精心选择的作为解释的核心概念。他认为,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比自然科学家拥有更多的前提假设、分析工具和概念术语。自然科学家强调物质进程,将历史文化背景及相关伦理价值的影响最小化。并且主要关注概念和一系列观察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抵制过多的生物学方面的影响。更倚重于语义学的网络系统。通常要追寻一个在伦理学上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卡根还列表系统地比较了三种文化各方面的异同:
卡根教授的划分严谨细密。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三大学科的本质特征,标志着知识发展和学科分类已进入成熟时代,人文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变得更加清晰。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区分明显,但也有交叉渗透、界限模糊的地方。比如,历史、人类学、心理学既可归属于人文科学也可归属于社会科学。而且当今有关性别、团体、族群等热点问题研究就属于跨学科的领域。不过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前者会更多地借用自然科学的物理语言或数字统计的方法去描述社会事实。而后者不回避使用隐喻性或象征性的语言去表达人的存在状态并作出道德的或审美的价值判断。
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都是人类创造或发现的,其目的是服务于人类自身的各种美好需要,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主要是解决人类物质和制度方面的外在需求。那么人文科学大致是要满足人类内在的心灵需求和精神方面的渴望。当代以色列教育家阿拉尼指出,人文教育有三大基本目标:一是让学生理解文化中的高质量因素。文化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描述性的或说中性的,指各种不同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堆积和累加;另一方面文化是规范性和理想性的,与野蛮、无知和鲁莽相反,它指向一种进步的、高尚的和精致的生活方式。人文教育就是让学生能够对高级文化和完美纯全有巨大的热情和渴望,但这种教育采取的不是非黑即白式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而是坚持避免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多元对话的态度立场。二是培养学生自觉的和批评性的思维方式。人文教育不是灌输、教化或洗脑,而是让学生养成理性的、批评性的和独立的质量风格,让学生成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主人,而不是受外在权威、社会习俗和迷信偏见所左右的奴仆。批评性的自觉自治是第一的或最重要的知识质量和美德,如果人们不去独立地思考和判断他们的父母、老师和雇主的想法,那么科技的发展、伦理和人权的进步是不可能的。三是教育学生实现并完成真正的自我。这一点与前面的批评性的自治不同。它并不局限于自觉的和反思性的知识活动,而是全方位的自我个性的充分展开和实现。自我的真实性不仅意味着“想自己所想的”(thinking for themselves),而且包括“做自己要做的”(being what they are),即对自己忠诚。这种人关注、尊重并忠实于自我的存在状态与独特本质,执著于内在世界与外在行为的统一和协调,而不是墨守成规、自我异化和装腔作势。
面对现代性的不断挑战,人文科学在当代高等教育的领地逐渐被收窄,其作用也不断被弱化。某些研究态度和方法的弊病在逐渐突显:首先是人类知识的碎片化。知识的分科化有利于专业性的深入探究,但却造成了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甚至壁垒森严的学术格局。专家学者们往往以自己的专长而垄断吹嘘、自以为是,常常以非自己的领域而规避责任。人文科学重视个体性和差异性,但其研究的视角必须是综合性的。它不能不考虑或参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这是其自身的超越性和理想性所要求的。其次是研究内容的数据化。这是受到了自然科学或数理统计方法的过度影响,有时,冰冷而枯燥的数据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性深层的存在状态。正如《文化中国》编辑子夜所言:“包括量化比较手段和数据至上观念。都是西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因素介入到人文学术研究。将会导致学术的变形和泡沫现象。”最后是学术成果的功利化。今天的人文学术研究已经很少是内在的“为己之学”,更多的是为外物左右的功利之学。这也是受无序的商业市场和僵化的意识形态所驱动的结果。在价值迷失的时代,恢复人本主义的精神、重建人文教育的体系是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编辑:杨国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