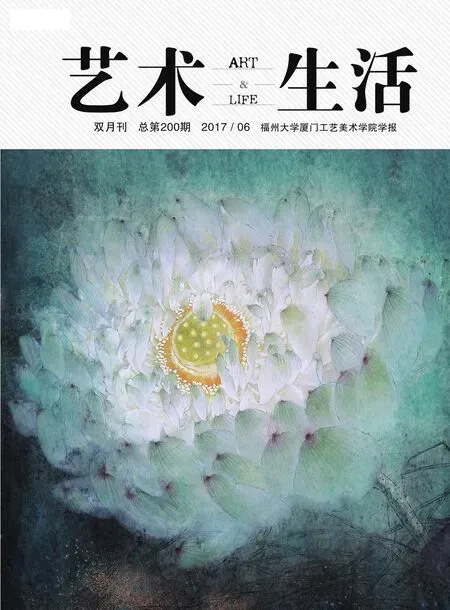文人画:一种精英阶层的重建策略
李永亮
(山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关键字:文人;文人画;宋代画论
文人士大夫是学者们在阐释文人画时必然提到的主体对象。以往,由于分析者总是站在艺术史的角度进行阐释,所以一切的资源和历史都似乎在为艺术服务,文人阶层的形成这一史实也成为文人画得以兴起的原因和背景。但是,如果从文人意识形态生成的社会视角重新审视文人画,就会发现对文人画的推崇其实是前者在形成和重建过程中进行文化博弈,社会改革以至最终营造程式化精英圈子的文化策略。文人对文人画的推崇固然顺应了艺术内部的发展规律,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重建并维系自身的文化权威。
一、文人画兴起前夜的宋代
众所周知,宋代的社会结构较之前代产生了重大变化。门阀贵族的败落和文人阶层的上升导致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发生转变。所以,院体画和文人画在此期间产生的分野就不可能仅仅是艺术内部规律的作用,更是文人阶层在与统治阶层对弈的过程中争夺文化话语权的表征。那么,文人阶层为什么选择后人称之为“文人画”的绘画类型,又是如何围绕它展开理论建构的?要回答这些历史性问题,我们就必须设法重构文人画兴起的本来境况。只有把历史重新在脑海中构建起来,文人画作为文人阶层的一种文化策略的作用就昭然若揭。所以,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文人画兴起之前的历史语境。
有鉴于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的历史教训,也为了证明自身“奉天承运”的合法性,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政治策略,以教育和考试培养阶层化的知识集团,建立制度化的文化支持系统,以重新确立思想秩序。[1](P151)印刷术的发达以及科举制度的成熟等一系列实质性措施使大批处于社会底层的文人通过科举成为宋朝官员的主流,也成为政治的最多参与者。①正如柳治微所言:“宋之政治,文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文士之手者,惟宋为然”[2](P516)。其实,在此之前,文人的意识觉醒就可以从唐末“逸格”的出现中表露出来,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允许,他们还没有能力形成巨大的舆论影响。而宋代所赋予的这种政治地位的提升为文人的意识觉醒提供了空间。
一旦从普通的“十年寒窗无人问”到“一举成名天下知”,巨大的事功之心成为萦绕在整个文人阶层中的共识。从松散的个体一跃成为阶层之后,内部会形成一种群体凝聚意识,文人所追求的对象也从个人的进退荣辱变成了社会和阶层的群体关怀。[3](P71)因此,为了证明自身的干政能力,也为了报答皇恩,这个时期的文人跃跃欲试:“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4](P225)。但是之后,在统治阶级和文人阶级的阶级对话和消解的过程中掌握政治资源的皇帝和官员逐渐垄断一切,而掌握知识资源的文人阶层则渐渐失去它的位置。所以,士人阶层在之前地位晋升的过程中形成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就与统治阶层的霸权产生分歧和矛盾。重建知识与思想的权威,确立士大夫角色,便成为这些失去皇权制约力量的文人群体的当务之急。因此,体现政治能力和重建知识权力的双重需要促使文人阶层开始构想自己的阶级话语,建构标榜自身审美的价值观。
问题是,文人阶层的这种重构知识权威的行为如何才能出师有名。此时,社会承平日久而来的普遍腐化渐渐浮现,经济状况更是日益令人担忧。《燕翼诒谋录》中载:“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寖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5](P166)面对令人忧患的社会风气,变革声浪日高。在变革的社会浪潮中,如很多时代一样,革新儒学成为社会变革的主流,进而出现疑经和疑古的现象,“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大行其道。其中,以蜀学的怀疑精神最甚。蜀学传播于蜀地一带,为苏洵所创,后经苏轼、苏澈进行发展,追随者还有黄庭坚、张耒、秦观、李公麟和米芾等文人学士。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道家思想的流行以及地方民风的影响,蜀学一直充满怀疑精神。在这之前,蜀学被象征正统的洛学和新学视为异端邪说,但在疑经、疑古的社会风尚下它开始大放异彩。这些认可蜀学的文人频繁地发表言论并且进行雅集活动,最终形成有共同思想基础与学术倾向的学派——元祐文人集团。对于蜀派的盛况,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写道:“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6]由于这一群体中的文人都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再加上蜀学的学说性质符合社会的改革需求,所以以元祐文人集团为代表的蜀派对当时整个文人阶层的价值观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追求和建构的审美趣味继而上升为整个文人阶层的趣味。最终,这种趣味在建构文人画的美学原则的过程中成为社会圭臬。但在这之前,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注意到文人画。
二、“形似”与“常理”:文人画的话语策略和学理依据
对文人阶层而言,要想建立代表自身的价值观,不仅要对社会进行质疑,更需要在质疑之后提出改革措施,在改革中开辟文人士大夫的语言阵地。这样,他们面临的头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改革对象。由于社会华靡风气的蔓延和统治者的号召,对文学文体进行改革被首先提上了士人阶层的日程。
宋初的朝廷注重文学,但是文学的文体沿袭的是唐末五代辞藻瑰丽的骈文,在统治者看来,这种浮夸绚烂的辞藻之作简直就是靡靡之音,给整个社会带来流弊,根本不适合传播正道。所以,宋仁宗曾下诏要革除文风之弊:“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趣向,而比来流风之敝,至于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曼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礼部其申饬学者,务明先圣之道,以称朕意焉”。[7](P166)以古文来取代“浮夸靡曼之文”从而“明先圣之道”,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在这种社会语境中开始展开。他在力倡古文之美的同时,提出“文与道俱”的观念,认为应该通过“文”来获得“道”:“孔子之言道曰:‘道不远人’;《中庸》者曰:‘率性之谓道’,又曰:‘可离非道也’……凡此所谓道者,乃文人之道也。”[8]这里,欧阳修已经把“道”从玄虚深奥的抽象之物转换为文人的行为准则和人格理想,巧妙地将文人的自我建构放在整个社会理想的建构基础上,将文人的追求塑造成衡量社会的标尺。这种标尺的衡量范围在塑造文人阶层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将逐渐扩大。

(北宋) 郭熙 《早春图》
与此同时,书画领域的发展规律暗合了文人阶层改革的要求:一方面,在统治阶层的偏好下,社会上书画盛行。据记载,在杭州的商业街有专门的店家出售院体风格的扇面。每当宋徽宗作一扇面,别人就会立刻复制一本,有时同一作品可以有上百个副本。[9](P28)另一方面,宫廷生活为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奢侈的样板,社会上奢靡之风盛行,有人曾针对杭州同乡纵情于奢华,争奇斗富的状况写道:“不惟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后宫朝有服饰,夕行之于民间矣”[10](P28。所以,此时社会上大量的绘画作品都是为了薪酬所作,获得金钱而非塑造精品成为创作的主要动力。为了革除社会的流俗风气,也为了同时将文人的追求一以贯之,广受统治阶层甚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绘画领域自然就成为文人标尺所衡量的又一对象。

(北宋) 王诜 《渔村小雪图》

(北宋) 米友仁 《潇湘奇观图》
文人阶层选择了文学文体和书画两个对象进行改革,但方式却不同。针对文体的改革选择复古,而针对书画的改革则选择了创新的形式——在院体画之外发现文人画并将其建构为文人阶层甚至社会所应追求的审美趣味。何也?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文学本就是士大夫阶层的产物,学习古圣先贤改造当下,本就体现出文人阶层的文化传承性和合法性;而绘画自诞生之日起就代表着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专门用于图绘帝王宫廷生活,文人阶层要想建立标榜自身的价值追求,就必须采取或隐或显的对立态度,寻找不同的审美标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画史上某种新概念新理论的出现,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概括解释新的现象,宣扬新的主张,同时还往往夹杂着对某些流行现象的排斥,甚至或多或少带有党同伐异的倾向”。[11] (P45)
文人作画并非宋朝所独有,但是在书画品鉴中“文人画”的趣味自觉与批评话语却在宋朝开始凸显。从晋到唐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文人作画和工匠作画在画面效果上并没有产生太大差异,关键是对作画的文人是否应该有一种不同于工匠的评价标准才是一直被争论的事情。不管是从庄子的“真画者”还是“由技入道”,都体现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对天、地以及人之大道的关注。在文人心中,绘画如果脱离了对这种大道的表现或者“中得心源”的感悟,即使作画者身份再尊贵,也会感觉“躬斯役之务,辱莫大焉”[12]。这种将书画的创作活动同中国文人的精英情怀联系到一起,赋予文人作画以体现“借物以明理”的作用,正是导致以苏轼为首的元祐文人集团在宋代建构起不同于宫廷和世俗画工之艺的文人画大旗的文化史逻辑。
随后,为了快速清晰地表明自身审美趣味的立场,苏轼等文人更是直接提出了具体标准。例如,苏轼在《书郡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中直白地说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13](P1525-1526)。这一说法历来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中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说:“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此老不能工画,故以此自文”[14]。邹一桂以创作原则的角度批评苏轼,认为他是在避短。但从历史语境中看,苏轼的主张显然是美学原则而非创作原则,是为了区别宫廷院体画和世俗画而生产出的话语策略。这一策略一方面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促进文人画尚古拙而规避技巧的发展趋向。那么,形似是否可以成为衡量文人画和非文人画的美学价值的核心标尺?我们稍微回忆一下那些被标榜为生产了文人画代表作的文人的普遍特点,比如李公麟、徐熙、顾闳中、郭熙以及周文矩等人本身大多是宫廷专业画师或逃遁山林的隐士,均在创作上投入了职业化的精力和时间,而并非是所谓的“墨戏”。因此,苏轼虽然以“形似”切入了文人画批评,但是他的目的却是通过贬低形似将“诗人之清新”的品鉴关怀,在绘画批评价值论中凸显出来。例如其在《又跋汉杰画山二则》中提到:“观文人之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15](P76)由此看来,视觉差异并不是根本区别,根本区别在于“这些人的作品于无形中显示出文人士夫所有的气质、素养、情趣”。正如有的学者认为文人画理论的核心不是“形似”与否的问题,是超越“形式”,而不是反对“形似”。[16]
如果说“形似”是文人画批评的话语策略,那“常形”“常理”就构成了批评的学理依据。苏轼在画论中说道:“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13](P3)。正是在“常理”的标准下,苏轼才提出“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的赞叹。在“常形”和“常理”的辩证关系上,他指出如果“常形”丢失不算完全失败,但是“常理”如果不存于画,“则举废之矣”。这就通过为文人画建构“常理”的意趣将其推崇到了至高的正统地位。进一步,苏轼通过形与理的比较引出了各自的主体——工匠和高人逸士,以高人逸士可以辨别画中之理的说法将文人阶层的优越性鲜明地建构出来。

(南宋) 马远 《踏歌图》

(南宋) 马远 《山径春行图》
三、以诗入画和以人品画:从创作到欣赏的双重建构
文人带着政治使命介入文人画始自宋代,而介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介入。换言之,文人介入绘画创作的有力武器和优势是文人首先要考虑的。上文中“形似”是在与院体画对比的情况下实现的话语策略,而单独对文人画进行塑造则是另一项工作。在此过程中,文人以重建权威为目的,将最能代表阶级水平的文化现象融入绘画,并不断使其成为画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对象就是诗词。对于从小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而言,诗歌已经成为其生命和身份定位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这是其能介入绘画创作的文化背景,也是诗画在之后融合过程中,意象之间可以深入互文,互动和相互渗透的基础。[17](P132)张法对文人阶层“以诗入画”主张的目的说得更直白:“引诗入画,诗又是用书法写的,实际上就是引诗书入画。从文人画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即区别于画工和画院来说,这是很成功的。画工,画可以画得好,但书法不一定行;画院中人,书法可能行,但诗不一定写得好。而诗书入画又不仅是诗随便写入,而要成为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位置上有一个构图的问题,在艺术上有一个书画笔墨统一的问题,这都提高了绘画的深度”[18](P186)。反过来说,提高了绘画的深度就意味着提高了创作主体——文人的社会地位,而这也是他们所预想的。
如果说文人对创作的完美介入是在戎马征战中开辟江山,那之后的欣赏则更像是打下江山之后的守护和治理。守护所遵守的法律法规就是勤劳不倦的文人在宋代发明的赏画的法则。宋代画论较之于前代画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增加了赏画的法则。前文指出,苏轼认为对于画中的“常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辩”。其实,这种观念广泛流行在宋朝的审美批评当中。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19]。又如欧阳修所说:“画之为物尤难识,其精粗真伪,非一言可达。得者各以其意,披图所赏未必是集笔之意也”,“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从文人阶层的角度看,这种认为赏画是件困难事的“先抑”是为了“欲扬”文人阶层赏画的优越性,是文人阶层为了让社会更迅速地接受这种阶级话语所采取的另一手段,是文人阶层在文化博弈中为掌握话语权所采取的文化策略。
文人们在历代创作标准的基础上建构欣赏标准,以期在引导审美潮流的过程中获得拥护地位。譬如刘道醇在《圣朝名画评》中提出:“夫识画之诀在乎明‘六要’而审‘六长’也”。[20](P3)他的“六要”和谢赫的“六法”以及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的“六要”有直接关系,但是刘道醇的“六要”却把后两者的创作之法转换成了审美之法。
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鲜明地把文人推上前台,他们开辟了“以人品画”的批评方法视角。这一视角在帮助文人和文人画走上前台的过程中赢得了文化合法性的重要作用。另外,儒家尚道德人品、社会地位的观念,也为这种批评策略的成长提供了话语合法情境,将一个文人画批评所力求“为文人直接参与绘画活动(而不是一般的欣赏)制造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的批评策略逐步上升为绘画批评的文化价值论标准。换言之,正是因为儒家思想长期为社会灌输君臣父子以及以人品论高低的秩序观念,才会使得统治阶层优先选择与工匠相区别的文人批评标准,才使得文人阶层在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中获得更多身份权力。
“以人品画”的滥觞应该开始于唐末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他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鄙贱之辈所能为也”[21]。虽然提及到的是人品与创作而非欣赏的关系,但却设立了“逸品”的画格。一百年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设置了神、逸、妙、能的品格。与其他三格不同的是,朱景玄在“逸格”中明确使用了“以人品画”的批评视角:“张志和,或号曰烟波子,常鱼钓于洞庭湖。初颜鲁公典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深得其态。此三人,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22]。北宋初,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开始将“逸格”提升到品格的首位,建立起以“逸格”为最高的批评标准。正如其所言:“画之逸格,最难其俦”。从《益州名画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黄休复“以人品画”的原则,例如他在论及孙位的时候写到:“禅僧道士,常与往还;豪贵相请,礼有少慢,纵赠千金,难留一笔。唯有好事者时得其画焉”[23]。除此之外,宋代另外两部重要的画论著作《图画见闻志》和《画继》也都赞同“以人品画”的最高审美准则。南宋以来,文人阶层在维系自身特殊地位的过程中对这种人品和画品的关联不断深化,“以人品画”走入审美批评中心就意味着文人阶层又重新建构起了文化与思想的权威身份。
至此,文人阶层从创作和欣赏,作者与观者的双重视角对文人画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建构。文人身份的优越性使文人画的创作和欣赏具有一种垄断性质,进而形成越来越封闭的文化交流圈,文人画也成为一种程式化的艺术。这种封闭的程式化特征注定了文人画是小众的,而文人正是在对小众交流圈的维护过程中重建并保证了自身阶级的文化话语权。由此可见,文人画的兴起固然有艺术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但更是文人阶层重建知识权威的文化策略,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文人画而恰恰是文人阶层本身。
结语
文人阶层利用书画重建文化和思想权威,却无意中辨识和建构出了在后世长盛不衰的文人画类别,以至于后人过多地关注后者而忽略了文人画背后文人阶层的话语操控。以宋代画论为线索,我们可以从中察觉文人意识形态的形成,更可以发现后世对于文人画的推崇,其实质是对旧式文人的审美理想的追慕。所以,以此反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文人画的批判,就会发现那不单是艺术审美之间的争端,更是新时期知识分子对旧式文人的批判。
注释:
①据统计,《宋史》列传的北宋1533人中,以布衣身份入仕者约近845人,占据总数的55%。
以上资料引自寿勒泽的《北宋蜀学与文人画意识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