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视域下的萧红与曼斯菲尔德
孙可佳
萧红(1911—1942)和曼斯菲尔德(1888—1923,英国女作家)的女性意识的形成,都与她们自身不幸的婚恋经历有着很大关系,其中更因战乱、漂泊、贫病、孤独而加深了这不幸。
萧红的一生正值中国最多灾多难的岁月,而她并不是个坚强而有勇气的新女性。近代的新秩序至少在理论上倡导男女平等,青年一代以全部身心投入这所谓的现代化之中——然而,对于身心方面都欠缺准备的人,特别是女性,必将付出艰辛痛苦。萧红在保守的封建家庭中长大,自幼缺乏母爱,天性敏感、不更世事,成年后又置身于一个极不健全的环境中。我们从她的写作和友人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她虽渴望自持自立,却又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她总令自己陷入极端困境中,然后选择最困难的出路;她很少听从那些关心她的女性朋友的劝告(如许广平、池田幸子),而总依顺于男人的需求和索取。
萧红初中毕业后被许婚汪氏,继而出逃,与人同居后又遭遗弃,回到哈尔滨时潦倒困顿、怀有身孕,被萧军解救,与其结为伴侣。然而与萧军的遇合正是她不幸婚恋与女性意识萌生的开始。
萧红的敏感、柔弱、缺乏自信、犹豫不决,与萧军的健壮、粗暴、刚愎狂妄形成了鲜明对比。据萧军自述,他性格粗暴、酗酒、好打斗,萧红在与其同居的经历中,不仅为其管理家事,还要忍受拳打脚踢甚至是感情不忠。萧红自己曾写道: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良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巳经太久了……
萧红开始不时流露出对自身女性角色的反思。她曾向聂绀弩这样说: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此时的萧红,正处在和萧军、端木蕻良的三角恋情中,她想要脱离困境,却又流露出强烈的自怜情绪。她性情温柔,“说话时声音平和,很有韵味,很有感情,处处地方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好主妇”,但是“她的温柔和忍让没有换来体贴和恩爱,在强暴者面前只显得无能和懦弱”。对此她自己在《呼兰河传》中有一段叙述,可看作对自身和中国女性的深刻洞察:
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性很不好……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个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就是好欺负的,告诉人快来欺负她们吧!
……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萧红女性主义观点的形成,也与萧军的性别地位观念(大男子主义)有关。与萧军在一起的这段时期,萧红在《生死场》等诸多作品中都流露出“反男性”的态度。她常常刻画女性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的可悲地位和悲剧命运,引起人的共鸣。譬如《生死场》中的王婆、金枝、月英,她们是在丈夫的权威下忍声吞气,忍受肉体的折磨;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如同工具和奴隶,更无法获得应有的理解与尊重。
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之后,其悲剧命运并未扭转,女性意识仍然强烈。从前是身体伤痛,此后是精神冷暴力。她曾跟聂绀弩抱怨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靳以也认为“端木是个自私、矫饰的懒虫,他好像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梅志曾叙述萧红和端木在重庆北碚之时,两人看起来如何冷淡,萧红的模样如何颓唐。端木的冷漠是显然的。1938年夏,日军转向武汉三镇,7月间端木计划由武汉入川,8月和梅林、罗烽坐小船去了重庆,却未带上萧红。萧红在汉口的最后一个月里写下了短篇小说《汾河的圆月》:一个和小孤女相依为命的老瞎女人,儿子战死了,媳妇也出走了,最终老瞎女人疯了,汾河边的月夜下,她依稀听到爱国宣传队在演戏。其实这正是当时萧红沮丧心情的写照。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对团圆媳妇、王大姑娘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以及《小城三月》里翠姨向往爱情却无法挣脱封建束缚的悲剧,说明她已认识到根深蒂固的封建积弊对女性的残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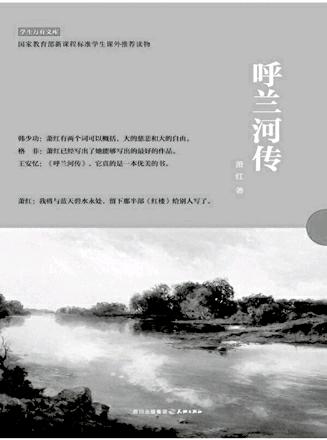
到了香港,多年在饥饿边缘挣扎、一再被打击的萧红终于病入膏肓,战乱之中又染肺病。此时的她仍然是被女性解救的——史沫特莱送她到香港玛丽医院,供她衣服和金钱。萧红去世后,骆宾基和端木蕻良又因萧红发生冲突:骆拿出一封萧红痛骂端木的信,并透露自己和蕭红约定等她康复后共结秦晋之好。据孙陵回忆,骆宾基于萧红生前记下了有关她作品版权的遗嘱:《商市街》给她弟弟,《生死场》给萧军,《呼兰河传》给骆自己,端木一无所得。尽管骆宾基事后否定孙陵的回忆,称冲突与版权无关,但这些足以证实,萧红一生所遭不幸确是屡受男性的欺凌所致。正如她临终前那句:“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endprint
萧红的痛苦与不幸大半是为遇人不淑及所处时代所牵连,而非其天性反叛使然。曼斯菲尔德同样历经了几番恋爱的失败和婚姻的痛苦,在战乱与贫病中萌生和发展了女性意识——但她的每一次痛苦挣扎都是源于自由浪漫的天性和坚定的自主选择。
曼斯菲尔德的家庭环境对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启蒙作用。曼斯菲尔德生在一个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哈罗德是银行家,母亲安妮是家庭主妇。母亲的全部时间都在“拯救他(曼的父亲),照料他,使他安静下来,听他说自己的事”,“与其说是温柔忍耐,不如说是无精打采,得过且过,她关心丈夫的需要,但对孩子疏远冷淡”。为了生儿子,安妮连续生下4个女儿(一个夭折),身心俱疲,但却并不爱自己的孩子——这正是一种试图逃离女性传统角色的表现。在曼斯菲尔德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能找到母亲安妮的影子。
1906年,曼斯菲尔德从伦敦皇家学院归来时,放弃父姓,改用外祖母娘家的姓“曼斯菲尔德”,并开始使用笔名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不想让自己陷入传统家庭里,于1908年7月独自前往英国,开始了文学生涯,并走上反抗“维多利亚传统家庭中女性所扮演的传统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的道路。
曼斯菲尔德的家庭经历与萧红极为相似——同样在传统父权家庭长大,缺乏母爱,与祖辈亲属要好,接受教育后便摆脱了封建家庭。如许广平所说,“她(萧红)喜欢像鱼一样自由自在的吧,一个寻求解放旧礼教的女孩子的脑海,开始向人生突击,把旧有的束缚解脱了,一切显现出一个人性的自由……可怜的是从此和家庭脱离了,效娜拉的出走!从父亲的怀抱走向新的天地,不少奇形怪状五花八门的形形色色的天地,使娜拉张皇失措,经济一点也没有。”萧红、曼斯菲尔德,都是各自时代环境中的“娜拉”。
曼斯菲尔德是个早熟且热烈追求爱情的女子。她13岁时爱上了小提琴手加纳特,18岁时第一次真正恋爱:在返回惠灵顿的途中与一位英国板球运动员相遇,“我想激怒他,在他心底唤起奇特的感情,他见过那么多世面,这真是一种征服”。恋情在她父母的监控下不了了之。回到惠灵顿后,曼斯菲尔德经历过短暂的同性恋。在伦敦,20岁的曼斯菲尔德与大她11岁的声乐教师波登一见钟情,结识数周便举行了婚礼。但结婚当晚她就不辞而别,去利物浦追随小提琴手加纳特,并以加纳特妻子的身份成为合唱队的一员,不久怀孕。此后,她客居比利时和德国,在巴伐利亚时不幸流产——这是她一生唯一的孩子,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她在1909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
将来如有一天孩子问我:“妈妈,我是在哪儿生的?”我便回答:“在巴伐利亚,亲爱的。”我想那时我会重新感到今天的寒冷,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寒冷,心里的,手上的,灵魂里的寒冷。
将近十年后,曼斯菲尔德将失去孩子的痛苦写进《巴克妈妈的一生》中,“她感到难以独自忍受失去孩子的痛苦,她渴望有一个孩子可以照料”。
挣脱了传统家庭,历经各种恋爱失败的曼斯菲尔德此时已有了显著的女性意识和大胆看法。她在1908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

我刚读完伊丽莎白·罗宾斯的《来找我》……我确实已经意识到妇女在未来的世界上能发挥多大的能量,尽管这一意识还有些模糊。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她们还从未得到任何机会来发挥自己的能力。还说什么“开明的时代”,“解放了的国家”,纯系一派胡言!我们被牢牢地套在自制的奴隶枷锁中。是的,我现在认识到这些枷锁是自制的,所以必须自己去把它销毁。
总之,我所需要的是力量、钱财和自由。有一种令人感到乏味的理论认为,在世界万物之中历代妇女真正继承下来的只有爱情。这种理论严重地妨碍了我们前进。我们必须逐走这个可怕的妖魔,然后,然后就会得到幸福和自由。
1912年,曼斯菲尔德结识了《韵律》杂志主编约翰·米德尔顿·默利,他们坠入爱河,后来一直同居。1918年,凯瑟琳的名义丈夫波登提出了离婚申请,默利才与凯瑟琳正式结婚。同默利在一起的日子给了她不少幸福。但后来随着曼斯菲尔德的肺结核不断恶化,他们辗转于欧洲各国进行治疗,曼斯菲尔德感到默利对自己疏于关心,时常觉得孤独、恐惧,两人之间的感情也不断出现危机。
和默利在一起后,曼斯菲尔德笔下有了更多女性意识的直接表达,且充分体现了她的性格特点。1913年夏她在给默利的信中写道:
我想我是个很不合格的家庭主妇。如果没有适当的方法,理家就會占去许多时间……我讨厌做这些事,讨厌得很,讨厌极了,而你呢?跟别的男人一样,认为由女人伺候理所应当。我来当女仆的态度是不会太温和的。没有其他事可干的女人干家务没有什么……而你却说我是暴君,夜晚我累了,你还要感到奇怪。像我这样的女人面对的难题是无论如何我也忘不了手头的工作……然而,我爱你。我既感到骄傲同时又感到屈辱。你不理解我,然而却爱我,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她和萧红一样不喜欢做管家主妇,但她显然没有萧红那样温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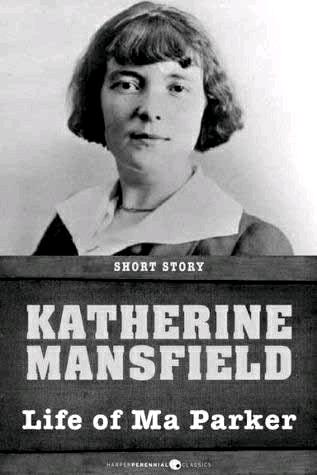
1920年曼斯菲尔德评论D.H·劳伦斯《失去的女孩》时,表达了她的一些女性写作观点:
他说他的女主人公是非凡的,不同于一般。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呀!但是看看她。譬如她年轻的时候——她高兴地和医生们一起做粗鄙的、喧闹的游戏。他们可能是互相冲撞的野兽——仅此而已。再譬如男主人公把她推入厨房,与她发生关系,然后她又唱着歌继续洗碗。这是耻辱。再譬如那个干活的妇女邀请那个意大利人到她的卧室去,一场腐化、肮脏的丑剧。全都是虚假的。一派胡言!
1913—1915年间,曼斯菲尔德来去奔波,同默利的关系从热恋到疏远,并与法国作家弗朗西斯·卡尔科互写情书。1915年2月,她直赴卡尔科的部队驻扎前线格雷城,月底才回到默利身边。
曼斯菲尔德与默利的分合一直持续到她去世前。1920年12月至1921年5月是一个纷乱的时期,曼斯菲尔德再次病倒,同时由于默利与贝白丝科公主(牛津区伯爵的女儿,其丈夫是罗马尼亚贵族)的友情关系,他们发生误解。1922年6月,曼斯菲尔德同默利一起回到瑞士。由于二人对曼斯菲尔德病情治疗的分歧,他们分居了:默利住在朗东,凯瑟琳则住在山另一侧的谢尔。他们每天通电话,并且默利会在周末看望她。曼斯菲尔德向他保证“我非常地爱你”。这期间曼斯菲尔德反思过自己的“任性”:“我的唯一忧虑是约翰。他应该同我离婚,和一个真正快乐、年轻、健康的人结婚,生儿育女,而让我做他们的教母。我根本做不了妻子。” 8月7日,她写下给默利的遗书。在遗嘱中她把所有手稿都留给了丈夫,并希望默利再婚,还将自己的小珍珠戒留给了继任者。
萧红和曼斯菲尔德所处的时代,一个是新旧交替、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思潮东渐的中国近代,一个正值西方女权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之时。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成熟,与二人相似的婚恋经历密切相关,当然也脱离不开家庭环境的影响:生于传统父权家庭,缺乏母爱,青少年时代冲破家庭羁绊,历经婚恋的挫折与丧子之痛,得不到丈夫足够的关怀,在贫病孤独中英年早逝。她们在短暂的一生中逐渐形成了女性意识,并深刻地体现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中。尽管她们都没有像弗吉尼亚·伍尔芙那样,形成系统的女权主义理论,甚至从未自称过女权主义者,但是她们以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并书写人类诸多苦难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流露出深刻的女性主义思想。endprint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研究》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