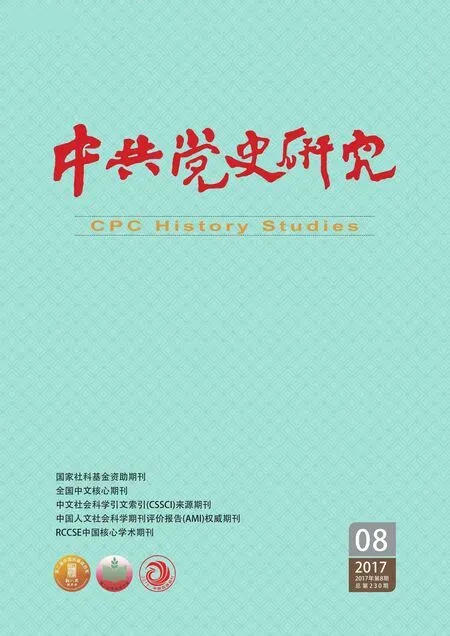上海市解放后三次争肥事件考察
·地方党史研究·
上海市解放后三次争肥事件考察
肖安淼
上海市解放后,受城乡互助政策、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运动影响,先后三次出现农民大规模进城争粪的风潮。市政府没有采取强力措施阻止农民进城,而是尽可能地化解由此引起的工农冲突和农民内部冲突。本文拟对农民进城争粪的原因、过程,以及上海市的应对措施加以考察,进而展现城乡关系的复杂性。在城市面前,农村并非总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经济决策的需要。
粪肥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城市卫生
Abstract: After liberation, influenced by the mutual-aid urban and rural policies, agrarian cooperation, and the “Great Leap,” there were three incidents of farmers struggling over manure in Shanghai.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did not take strong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farmers from entering the cities, but it tried its best to resolve the worker-farmer and farmer-farmer conflic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asons for and the process of farmers fighting over manure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hereby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The rural areas were not always disadvantaged and passive in the urban-rural structure, but their situation was dependent on the needs of national economic decisions.
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关注城市清洁卫生。城市粪便的清除,则是城市清洁卫生的主要内容。起初,上海的粪便清除方式是农民清晨进城收集城市居民和铺户的粪便(互不收费)。这一方式有效减少了粪便变为粪肥的成本,但农民根据农事多少和用肥需求自行安排进城清粪时间,不能保证城市环境常年清洁卫生,以致市内时常爆发流行性疾病。为此,1863年,上海公共租界设立负责马路环境卫生和处理垃圾废物的秽物清除股。1867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与粪便承包商订立承包合同,规定承包商必须将租界内粪便按时全部清除出去,农民则被禁止在租界内清粪。*《上海环境卫生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39—140页。此后,这一制度逐渐推广开来。到解放前,招商承包的范围已经大致扩展到整个上海市区*参见《日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关于招商承办清洁捐》,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R50-1-343。。
招商承包制度的建立显然对上海郊区及周边县市的农民不利。上海人口众多,是粪肥供应最多的城市。民国时期,除原英租界、法租界地区采用抽水马桶,利用污水厂或化粪池处理粪便外,其余地区每天的粪便产量已达到12000车左右(每车约440斤)*《市政关于卫生局签呈招商承办清除粪便一案》(1947年1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7-494。。据检测,当时上海市每日排泄物中,可收复的氮素约136万斤以上,磷酐22.7万斤以上,氧化钾31.8万斤以上*朱家珏:《改进上海市人粪尿管理计划书》(1936年2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7-494。。如此丰富的粪肥资源当然要加以利用。但是,承包制度建立起来后,农民进城收集粪便不再免费,而须向承包商主办的清洁所*清洁所原为商办,1945年改为官商合办,上海解放后由上海市卫生局环境卫生处负责指导具体工作。1956年11月12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清洁总队、清洁所和卫生局清洁科,合并成立上海市清洁管理所。1958年2月,上海市清洁管理所被并入上海市肥料公司。参见《上海环境卫生志》,第49—51页。缴纳“肥料变价费”*《上海环境卫生志》,第139页。,最终被排挤出城市,转向承包商未涉足的城乡结合地区。有时,农民的不满甚至会引发流血冲突*参见《上海环境卫生志》,第140页;徐峰:《1943年上海浦东区清洁纠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
解放后,随着农业生产被逐步纳入计划轨道,城乡二元对立关系越来越明显*参见武力:《1949—2006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白永秀:《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视角:形成、拓展、路径》,《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在这种城乡结构下,一般来说,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包括肥料在内的生产资料则由供销合作社供应,因而很少出现大规模进城的情况。然而,1949年至1954年上半年、1955年下半年至1957上半年,以及1958年下半年至1963年,上海三次出现农民进城争粪的风潮,后两次的规模还比较大。对于二元对立结构下的城乡关系而言,这种现象是比较少见的,值得深入考察。本文拟以上海市档案馆藏卫生局、农业局等部门档案为主要史料,还原上海三次争粪风潮的历史过程,进而展现城乡关系的复杂性*现有关于城市粪肥处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民国时期,几乎不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针对上海这个极具典型性的城市的研究则更少。研究者大多关注城市卫生整治和卫生职能的现代性等问题,城乡关系一般不在论述范围内。参见杜丽红:《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苏智良、彭善民:《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以近代上海为例》,《史林》2006年第3期;彭善民:《商办抑或市办:近代上海城市粪秽处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韩〕辛圭焕:《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3—182页;徐峰:《1943年上海浦东区清洁纠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崔德卿:《明代江南地区的复合肥料:粪丹的出现及其背景》,《中国农史》2014年第4期;任吉东、原惠群:《卫生话语下的城市粪溺问题——以近代天津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唐何芳:《商办抑或官办:试论近代广州粪秽处理变迁》,《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3期;曾德刚:《北平市整顿粪业研究——以1936年为核心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任吉东:《沦陷时期天津社会底层行业变迁——以粪溺业为中心》,《南方论丛》2015年第5期;等等。。
一、“城乡互助”与第一次进城争粪
解放初期,城市被批判为“消费城市”,面临着自身改造的问题。194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大城市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完全依靠剥削乡村”,“造成了乡村和城市的敌对状态”,提出今后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日报》1949年3月17日。。作为全国最大的,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浸染”最深的城市,上海市原来的粪便处理无疑体现出统治阶级对工人和乡村的剥削、压迫。这种剥削和压迫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粪肥经营制度方面,实行承包制度后,政府不仅向承包商收取“清洁捐”(即承包费),同时还对公厕征收“公厕捐”,对拥有粪车的车主征收“粪车捐”,对店铺和居民征收“垃圾捐”。承包商则依靠贩卖粪便谋取利益。后因粪肥经营范围广、数量大,承包商又按清洁地段和粪车分包给“二包”“三包”“四包”*按照当时的划分,“三包”大部分不劳动,而是雇工;“四包”大部分是自己与雇工一起劳动。参见《上海市解放前后粪便情况》(1955年11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1-2-421。。在这一经营制度下,农民进城收集粪便须缴纳“肥料变价费”,上海市区居民和店铺则需要按月支付一定的“倒桶费”(又称“清洁费”“月规费”“月费”等)和“垃圾捐”。1946年4月,国民党政府接管清洁所,将粪肥经营改为官办,但并未改变之前的经营制度。从“革命”的视角看,这种制度是对农民、清粪工人和城市居民的层层剥削。
其二,粪肥运输方面,主要由私人粪船代运,包商控制的粪便码头负责“排档”,即安排运送的“档期”顺序。农村需粪量具有季节性:在旺季,粪码头通常会往粪肥中加约30%的水再出售给粪船,粪船又加70%的水卖给农民;在淡季或恶劣气候时期,粪肥滞销,大量粪便被倾倒进黄浦江、苏州河或阴沟里*《上海市卫生局1950年工作总结》(1950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53。。加之上海滩帮派势力强大,负责“排档”的人,甚至整个粪肥处理行业都受到帮派势力影响。私人粪船通常要受到负责“排档”的人的刁难,“生活极为贫穷,船只破陋无力维修,沉船事件时有发生”,剥削、压迫关系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长期生活在水上,大量粪船船民患有血吸虫病。上海市1955年至1958年的调查显示,血吸虫病历年阳性人数占历年抽检人数的20.9%*《血吸虫病患者及治疗人数(1955—1958年)》(1958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82。;而在粪船船民中,却有40%以上的人患病*上海市肥料公司:《上海市的生活垃圾、粪便处理工作——解放后十四年总结》(1963年1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2-72。。
其三,清粪人员方面,大小包商和清洁所雇用的清粪工人分为“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即独立劳动者,需购买清除地段和粪车使用权,自己劳动。他们的收入来自“倒桶费”,但需要定期向上级承包商缴纳一定费用。“短工”则受雇于大小包商甚至“长工”,只出卖劳动力,收入通常很少(每月只有三斗至五斗米)。*上海市肥料公司:《上海市的生活垃圾、粪便处理工作——解放后十四年总结》(1963年1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2-72。另说每月只有两斗米的报酬。参见《上海市解放前后粪便情况》(1955年11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1-2-421。清粪工人中存在大量陈规陋习,例如随意增加“倒桶费”,向市民索要“迁入费”“红马桶钱”“年关费”“开关费”等;但另一方面,要获得某一地段的“倒桶权”,他们需要向帮派“拜老头子”“找靠山”“塞钞票”“送花礼”“拜寿”“打秋风”*上海市肥料公司:《上海市的生活垃圾、粪便处理工作——解放后十四年总结》(1963年1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2-72。。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清粪工人既是“受压迫最重、革命性最强”的工人,又具有较强的封建落后性。
粪肥运到农村后,只有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地主、富农等)才买得起,这同样是剥削的表现。总之,按照革命意识形态,上海粪便处理的各个环节无不体现出统治阶级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压迫。
卫生清洁行业存在的剥削问题固然严重,但对于刚刚解放的上海而言,最紧迫的任务是搞好城市清洁卫生。早在没有进城之前,中共中央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刘晓向南下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清除垃圾、粪便是个大问题,如果垃圾堆集,粪便乱倒,阴沟堵塞,整个城市就会臭气熏天,上海的生活秩序就混乱了。国际上许多人就看着共产党是否能治理好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接管上海》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245页。陈毅颁发的入城公约、守则及纪律等命令,都规定“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打扫街道讲卫生”等*《上海环境卫生志》,第50页。。
1949年6月,上海新政权接管国民党政府保留下来的粪便清理管理机关,除了废除该行业旧有生产关系、加强领导外,并未对其进行大的变革,以免影响社会秩序稳定。原有成员除罪大恶极分子外,都保留了清粪、运粪的资格。*上海新政权甚至没有在粪便清理行业内部进行镇反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以至于1954年发现,“工会常委十三人中逮捕法办的占十人,其他30个码头委员会的主席三分之二不纯”。参见《上海市解放前后粪便情况》(1955年11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1-2-421。对清粪工人来说,组织制度的“变革”似乎只是更换了上级领导,收入来源和结构则未受太大影响。也就是说,清粪工人没有被纳入财政拨款编制,能够收集多少粪便、清理出多少粪肥仍是其收入多少的决定性因素。清粪工人肯定不希望农民进城争粪,但上海郊区及周边县市的农民又确有利用上海市粪肥的传统,这就为城乡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长期的农村革命经验使得中共在动员农民方面得心应手,解放后确立的统筹兼顾的基本经济方针也要求城市和乡村之间加强交流互助。早在1948年8月,张闻天在第一次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农民要拥护城市,城市也要欢迎农民……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张闻天文集》第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7页。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同时指出:“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随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城乡互助”确立为国家经济建设根本方针的重要内容。
废除粪肥承包制度后,面对粪便清理人力不足和农村急需肥料的情况,上海新政权很自然地想到运用农民的力量。上海市不仅打破了实行承包制时对农民进城清粪所设立的限制,而且在运输方面制定了多项优惠政策,如农民不需要“排档”,优先取粪,并保证“相当数量直接配售给农民协会介绍的合作社或农民”*《上海市粪码头船户登记暂行办法》(1949年11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56。,开放给农民取粪的粪码头也从12个增加到17个,且以“每天出粪总量的七分之二优先供给农民”,农民购粪享受九折优惠,等等*《上海市委市郊工作委员会关于粪肥问题的情况材料》,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1-2-5。。
由于运粪船只不足,上海新政权积极鼓励农民组织供销合作社。1949年8月22日,上海《文汇报》介绍了老解放区合作社的经验,认为“没有运输工具,才不得不受‘粪贩子’‘粪头’的‘中间剥削’”,而组织供销合作社可以减轻农民在运输上的困难和负担*程准:《合作社与合作经济》,《文汇报》1949年8月22日。。年底,中共上海市委提出在市郊建立供销合作社,认为如此可以“消除中间剥削,支持农业生产”*《市郊农民运动当前的方针和任务》(1949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1-2-5。。
上海市郊及其周边农村原来有资本购买粪肥的只有地主和富农,但在新政权多种政策支持下,对于一般农民而言,资本已经不成问题。中共接管上海后不久,上海市出现了第一次农民进城争粪的高潮。据报道,洋泾区钦仰乡的永宁三村“第一次运到了大粪后,农民情绪高涨”,立即又组织13条粪船。“龙华虹桥乡分配在南码头、日晖港两处运粪。最初每天运160车粪,组织了40多条船;后来粪量增为每日320车,粪船扩大组织了84条;第三次粪量又增为每人420车,粪船也增为97条”。*《从大粪说到农运——为什么在短短六个多月中,郊区农运这样蓬勃的开展? 为什么农民的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会提高得这样迅速?》,《文汇报》1950年3月14日。此次农民进城争粪情况,还可以从上海市清洁所编制的统计数据中得到印证。1950年,上海市郊及周边农民全年“配粪”的数量为503876车,而到1951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1060216车,占粪便处理总量的比例也从15%上升到27%*《上海市卫生局二年来城市工作简要工作报告》(1951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281。。随后几年,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升高(见表1)。

表1:1949年至1954年上海市清洁所粪便清除量统计表(单位:车)
注:1950年的数据与其他档案略有误差,但由于差别很小,不进行修正。
资料来源:《上海市解放前后粪便情况》(1955年11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1-2-421。
1949年下半年开始,上海郊区各农民协会陆续与市清洁所订立购粪合同。所谓“配粪”,就是按合同约定“分配”粪便。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于之后供销合作社与上海市订立的供销合同,这时的购粪合同更具自发性。按照合同,农协以八五折购买一定数量的粪便,但需保证无论淡旺季,都到指定码头将粪便如数运走*《上海环境卫生志》,第157页。。这一方式有效地消除了清粪工人在农民需肥淡季和运粪船只不够的情况下将粪便冲沟的现象。从表1可以看出,1951年起,上海市的粪便冲沟现象基本消失。
解放初期,上海市有私人粪船3300多只,但随着农民粪船日益增加,到1954年4月,私人粪船数量减少到3011只。从表1中可知,私人粪船的运输份额也受到农民粪船极大挤压,从解放之初的91%降到1953年的不到40%。1953年,上海郊区大粪每天供应4500车,“与农民需求相差很大”,粪价上涨,导致高桥、杨思、龙华等区发生了农民围攻合作社要求解决肥料问题的情况*《上海市郊区工作办事处致刘副市长》(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46-1-61。。中共上海市委认为,“自由粪船‘抬头望价’”,导致粪肥价格波动,因此决定将全部粪肥交给上海市合作社联合社统一处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改进粪便清除与粪肥供应工作的意见的批复》(1953年11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46-1-61。,并于1954年4月将3011只私人粪船悉数转交上海郊区供销合作社管理,准入证件亦由清洁所颁发的“掺粪证”*“掺粪证”即一种运粪登记证件,记录粪船运粪日期、航程等信息。参见《上海环境卫生志》,第157页。,变为郊区供销合作社的“代运证”。当年,农民运粪比例由上一年的62%上升为91%。私人粪船的管理“提高一步”后,统一的计划与调配起到了整合运输体系的作用。此后,粪肥主要依赖供销合作社按计划供应,农民进城争粪现象大幅度减少。
总之,1954年以后,供销合作社取代农民的“自由粪船”,成为处理上海市粪肥的主要力量。在上海市的粪便清理体系中,周边农村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允许农民进城清理、运输粪便,虽然有支援农村、“城乡互助”的意涵,但更多的是立足于上海城市清洁卫生的需要。
城乡关系的“紧密”与“紧张”时常相伴而生。这一时期,上海市实际上将粪便运输工作转交给了农村。此举固然有利于摆脱沉重的粪便清理负担,但也失去了对粪便运输的掌控。粪肥供应能够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供销合作社尚且可以对农民进城争粪加以限制,但随着农业增产计划的不断攀升,农村对粪肥的需求越来越大,合作社的控制作用却显得越来越小。此外,清粪工人的收入主要依赖粪便清理和粪肥售卖,受粪肥售价和供求量的影响较大。由于农民在是否进城清粪的问题上获得了主动权,便会出现淡季粪肥滞销、旺季农民进城争粪的状况。这无疑损害了清粪工人的利益,容易引发冲突。
二、农业合作化推动下的第二次争粪风潮
1955年7月,毛泽东严厉批评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尤其是浙江省的“坚决收缩”方针。随后,全国各地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上海市及其周边的浙江、江苏两省亦不例外;至1956年春,三省市入社农户比例均达九成以上*参见《上海农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99页;《浙江省农业志》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320页;杨颖奇主编:《江苏通史》,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129—130页。。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供销合作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促进小农经济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22页。。因此,一定程度上说,此时的供销合作社对小农负有“领导”责任,表现在农村粪肥问题上,即对粪肥的供给有支配权。但是,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大多数农民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从落后的小农变为社会主义的一分子。供销合作社开始立足于“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从意识形态上失去了限制“社会主义的农民”到上海争粪的“资格”。此外,按照当时的宣传,初级社优于互助组,高级社又优于初级社;而所谓优越性,直接体现在粮食增产上。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各初、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增产指标也不断提高,农村需要粪肥的数量随之大幅增长。
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办公室和江浙两省省委、上海市农业局负责人,根据“先近后远”“先蔬菜、苗圃,后一般农田”“照顾历史上的使用习惯”等原则,商定了上海粪肥供应比例:上海郊区45.52%,江苏40.44%,浙江14.04%*上海市动员积肥农民回乡临时办公室:《关于挖掘肥源支援农业生产和处理外来农民来沪积肥问题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按照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粪肥指标还要在此基础上逐级分配到各地农村,而农村只承担部分运输任务。可是,在合作化高潮到来以后,之前的比例安排以及由供销合作社有计划地供应粪肥的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农业增产的需求。为了在计划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粪肥,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直接派农民到上海争粪。其中一些合作社甚至实施了奖惩制度。有的严格规定农民出来运粪的时间,运粪船上备有预计时间的口粮,超过时间则要挨饿和扣除工分,如昆山县陈家塘村三星社规定,来回上海以七天为限,每天七分工分,逾期扣分*上海市卫生局:《关于农民来沪取粪的混乱严重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877。。也有合作社采取鼓励措施,如宝山县繁荣、富强两社不仅给运粪农民记工分,还为每车补贴0.3元至0.4元,有的农民每天可收十车,收入颇丰,甚至在上海租了房子作为站头*《农民积尿取粪的情况》(1957年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又如,常熟规定每担人尿补贴0.2元至0.25元,每担含有半担黄粪(即居民马桶粪便)的粪肥补贴0.4元,并且当场付给。因此,农民进城运粪受到清粪工人和运粪工人阻止时,经常与后者发生纠纷和冲突,有的农民甚至以跳河自杀相威胁。1957年春,常熟有40多个乡社干部住在上海旅店,暗中指挥农民争粪。*《上海市政工会清洁所委员会葛友森致陈丕显信件》(1956年4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2-76;上海市肥料公司:《关于外县农民来沪积肥严重影响市容等问题的紧急报告》(1957年3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
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上海市迎来第二次农民进城争粪风潮。1955年11月,上海市公安局、市水上区人民委员会多次报告常熟、昆山等地农民来上海积粪的情况*参见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为农民船来沪积肥情况及其提出初步意见函告你局迅速处理》(1955年11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59-2-45;上海市水上区人委会:《报告农民来沪积肥情况》(1955年11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59-2-45。。最严重的时期是1956年上半年,“全市给农民倒去的粪便每天平均约8800担左右”*《上海市政工会清洁所委员会葛友森致陈丕显信件》(1956年4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2-76。,每日来船四五千只,分散于街道里弄,挑运杂肥的农民在1万人以上*上海市肥料公司:《上海市的生活垃圾、粪便处理工作——解放后十四年总结》(1963年1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2-72。。农民进城争粪的工具,除了宝山县用车外,其他均使用粪船。这些粪船来沪的方式有三种:其一,装运建筑材料、农产品或稻草入沪,进港前表示不搞粪尿,但入港后进行活动。其二,持有供销合作社介绍信来沪搞猪屎牛粪及其他杂肥,但往往兼搞粪尿,有的甚至来专搞粪尿。其三,空船入港,即先在港口外集结成一群,趁着潮汐一起冲入港内,不听把口人员劝阻。*《农民积尿取粪的情况》(1957年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
大量农民被鼓动进上海争粪,产生了下列问题:其一,许多农民深入里弄叫喊倒便,乱设小型粪码头和倒便桶,乱挖化粪池和阴沟,强抢公厕粪池粪便等,影响了“城市环境卫生及国际观瞻”和居民的生活秩序*上海市卫生局:《关于农民来沪取粪的混乱严重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877。。其二,大量农船涌入上海,导致航道堵塞、事故频发。1957年1月至5月,在苏州河内,农船发生翻船、阻塞等海事事故220起,情况严重时一天发生10余起,因事故死亡的农民共有20多人*上海市动员积肥农民回乡临时办公室:《关于挖掘肥源支援农业生产和处理外来农民来沪积肥问题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其三,农民“乱设”“乱挖”等现象造成严重的城市交通隐患。由于阴沟盖等大多没有及时盖上,小孩、车辆掉入阴沟的事故频频发生*上海市卫生局:《关于农民来沪取粪的混乱严重情况的报告》(1956年4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877。。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大规模来上海争粪,与清粪、运粪工人产生了利益冲突。当时,上海依靠运粪为生的工人有13000多人(含家属),以清粪为生的清粪工人约4000人*上海市动员积肥农民回乡临时办公室:《关于挖掘肥源支援农业生产和处理外来农民来沪积肥问题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如前所述,这部分人的收入名义上被政府“包下来”,实际上仍旧来源于“倒桶费”和出售粪肥。农民进城争粪后,抢占了不少工人的清粪量。很多市民因可以免去“倒桶费”而更愿意农民进城“倒桶”,如此自然严重影响了工人的收入。据1956年3月统计,闸北区大洋桥码头清粪工人每人每月减少收入20多元*《上海市政工会清洁所委员会葛友森致陈丕显信件》(1956年4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2-76。。1957年2月,张家浜码头清粪工人的收入比1月平均减少7元左右;长宁区廖某原来每月收费60元,此时仅收7元至8元,马某原收25元,现收6元*上海市清洁管理所:《邻县农民在沪取粪积尿情况》(1957年3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3月,虹口港、沙泾港的船民因粪量减少而影响收入,甚至计划停运粪便,向肥料公司送交请愿书*上海市卫生局:《为邻县农民在沪搞肥情况混乱请示》(1957年3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与正常时期相比,3月21日,上海市卫生局收集的黄粪减少3700车,少收运费3700元,按此折算,当月减少收入或超10万元。船民合作社1月收入53万元,2月只有46万元,当时估计3月不到40万元。因此,有的社已向政府请愿。*上海市肥料公司:《关于外县农民来沪积肥严重影响市容等问题的紧急报告》(1957年3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由于工人的收入影响家庭生活,所以与农民发生冲突的,有时甚至是整个工人家庭*虹口港肥料船运输合作社(汉阳路、顾家湾、辽宁路):《船民为生活逼迫,发出最后的呼声》(1957年3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仅1957年春,由争夺粪肥引发的斗殴事件就造成30多人受伤*《上海市委会关于加强粪便、垃圾和其他杂肥管理工作的通知》(1957年6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54-2-199。,之前更有1人因斗殴而死*上海市动员积肥农民回乡临时办公室:《关于挖掘肥源支援农业生产和处理外来农民来沪积肥问题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此外,不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之间也时常因争粪而发生冲突。又由于争粪风潮的出现,原有的肥料分配计划受到影响,地区之间的矛盾也加深了。
大量农民进城争粪,对上海市政府而言,最大的冲击是打破了公共卫生秩序。单以此点而论,上海市完全可以采取强制性措施阻止农民进城。然而,出于避免冲突的考虑,上海市政府没有将隔绝农民进城作为首要目标,而是表现得相当温和,甚至做出了牺牲,尽量对工人和农民两方加以安抚。
处理好与农民关系的关键,是处理好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关系。农民大规模入沪争粪的主要推力是合作社,甚至有不少合作社干部到上海直接指挥争粪。既然是组织之间的问题,就可以通过“组织渠道”解决。江浙两省相关部门若能说服教育各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将会有效避免冲突的发生。基于此,1957年4月,上海市通过中共中央上海局办公室约集江浙两省相关负责人开会,商讨如何调整三地粪肥供应比例等问题。由于来上海的主要是距离较近的江苏农民,三方协商决定,自5月1日起对分配比例做出调整:上海郊区由45.52%减为40.52%,江苏由40.44%增为45.44%,浙江数字不变。三方还决定,自5月起,计划以外增产的粪便,76.4%分配给江苏,23.6%分配给浙江,上海郊区不再增加。当时估计1957年粪肥产量将多于计划数,于是根据已知的1月至6月的产量,推算出全年粪肥增产数量,进而将其按比例分配给江浙两省,最终得到1957年全年的分配比例:上海郊区36.83%,江苏48.75%,浙江14.39%。*上海市动员积肥农民回乡临时办公室:《关于挖掘肥源支援农业生产和处理外来农民来沪积肥问题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
会后,上海市与江浙两省组织约400人的干部队伍,对将要和已经来沪争粪的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使大多数人“了解上海杂肥的计划分配情况和农民来沪积肥所带来的危害”;同时,上海市请求江浙有关地区党政领导对乡社干部和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劝阻其来沪积肥,使他们意识到“上海肥源基本上都已利用起来,潜力已经很少。如果无组织的来搞,不过是你挖我的,我挖你的,除了增加混乱以外,总的来说并无好处”。在前述会议上,上海方面做出了让步,以免与江浙两省入沪争粪农民产生直接冲突。但是,分配比例的下降使得部分上海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粪肥不足,不得不减少蔬菜的复种次数,乡社干部对此“思想不通”。有关部门对其展开思想教育,“说服他们照顾邻区的困难,因而坚持执行了改订的分配办法”。*上海市动员积肥农民回乡临时办公室:《关于挖掘肥源支援农业生产和处理外来农民来沪积肥问题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
上海市应对第二次争粪风潮的另一个举措是弥补工人的损失,以缓和其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1956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等相关领导要求市卫生局通盘考虑清粪工人的编制问题*《上海市政工会清洁所委员会葛友森致陈丕显信件》(1956年4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2-76。。若能将清粪工人的收入纳入财政拨款范围,当然可以有效消除其与进城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此事牵涉人数太多,最终被搁置。不过,上海市已经注意到应该给工人以适当补贴。当年12月,市卫生局报销了参与劝阻进城农民的清粪工人的“车膳杂项费用”*上海市清洁(管理)所:《清工参加劝阻农民取粪工作所需费用准予支销》(1956年12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1-1-1021。。次年3月,市肥料公司在一份报告中透露,针对受到影响的清粪工人,“有10万元福利金补助”,以便“不要影响工农联盟”*上海市肥料公司:《关于外县农民来沪积肥严重影响市容等问题的紧急报告》(1957年3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
此外,为避免工人与农民发生直接冲突,上海市决定:原先由运粪、清粪工人承担的“劝阻”任务改由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内河港务管理处、航运公安局领导,工人仅负责“协助配合”。被扣留的粪便“由肥料公司作价付款向农民收购,另由肥料公司统一分配”,以减少农民因利益受损而不听劝阻的情况。*《为劝阻农民取粪工作请示办法》(1957年2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
为增加粪肥供应,上海市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增加化粪池的清理次数,“在不太影响粪肥质量下”,使粪便清除量大为增加,同时动员全市重视粪肥收集,减少粪便冲沟等浪费。另一方面,加强对肥料种类的开发。据1956年调查,上海市杂肥不下70种。随着争粪风潮的出现,其中许多种原先不用的种类纷纷被利用起来。*上海市郊区供销合作社:《“1955年生产资料供应工作年度总结”的报告》(1956年3月2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01-1-191。例如,尿液原本不是上海市粪肥收集的重点,但1956年,全市在里弄中和近郊区修建蓄尿池2216个,1957年又增建了1500个*上海市动员积肥农民回乡临时办公室:《关于挖掘肥源支援农业生产和处理外来农民来沪积肥问题的报告》(1957年9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
上述措施出台后,进城争粪的农民数量大幅减少*1957年10月4日,上海市卫生局表示:“我自今年三月份参加市人委临时办公室工作,动员来沪积肥农民回乡,至八月份已经结束。农民船从4000余只降低为数十只。问题就目前来讲,已得到基本解决。”参见上海市卫生局:《致函》(1957年10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21。,上海市解放后第二次农民进城争粪风潮得到有效控制。纵观此次风潮,虽然上海市在其郊区的粪肥配额方面多有让步,市内清粪工人的收入也受到影响,但在处理这种有关城乡关系的问题时,该市总体上仍以城市为立足点,着眼于保持市区清洁卫生。正因为如此,尽管上海市卫生局从1957年初起即在“支援农业生产”的名义下,提议将清洁所(后来合并为清洁管理所)划归农业局领导下的肥料公司*上海市卫生局:《建议成立专门机构管理粪便、垃圾及肥料问题》(1957年3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03。,但市政府方面直到1958年2月才予以批准*《上海市人委会关于将卫生局所属清洁管理所和农业局所属肥料公司合并的决定》(1958年2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03。。
三、“大跃进”中的第三次争粪风潮
1957年冬,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运动之初,上海市仍希望粪便清除工作主要为城市自身清洁服务,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方面,加大自身清除粪肥的能力,尽力满足农村肥料需求。1958年2月11日,上海市同意将清洁管理所划归肥料公司,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3月21日,市肥料公司将其在郊区的三个办事处划给郊区供销合作社管理,以集中力量“挖掘城市肥料”*上海市肥料公司:《为将我公司所属三个郊区办事处划给三个郊区供销合作社的报告》(1958年3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45-1-227。;4月2日,上海市同意市肥料公司的要求,决定将全市15个区的清洁管理站交其直接领导,以加大收集粪肥的力度*《人委会关于肥料公司报告指示》(1958年4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2-1-1003。。另一方面,坚决抵制外来农民进城清除粪肥。1958年2月4日,上海市颁布《关于处理农民盲目挑运本市人粪尿和垃圾的暂行办法》,在对农民来沪所得粪便的处理方面,一改之前的“购回”补偿政策,转而实行无价“收回”,且“对继续擅自在沪挑运人粪尿和垃圾的农民,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应予以适当的处理”,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逐步杜绝农民盲目在沪积肥”*《关于处理农民盲目挑运本市人粪尿和垃圾的暂行办法》(1958年2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45-1-227。。
然而,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推进,上海市清除粪便的主要目的从保持城市清洁卫生转为服务农业生产。上海市自觉提高了“挖掘城市肥料”的指标。1958年7月30日,市肥料公司制定《1959年什化肥供应规划》。其中,市郊区耕种面积只有170万亩,但计划用肥量惊人:每亩施杂肥6000担、化肥100斤,计划共需各种杂肥102亿担,其中“发动群众冬季挖掘河泥解决81.6亿担”,全市1959年计划收集人粪尿9645.78万担,比1958年增加118.33%*《上海市肥料公司1959年什化肥供应规划》(1958年7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0-2-56。。相比市郊区夸张的用肥量,这个收集量翻一番的要求看起来已算“保守”了。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风潮中,农民进城主要是为了粪肥,“大跃进”时期,农民进城运输的肥料则包括河泥、垃圾、尿等新开发的肥料,粪肥所占比例不大。可以想见,此时的肥料生产量比之前大了很多。然而据统计,1958年上海市清洁管理所在册人员只有946人,另有各区清洁管理站职工5066人*《上海市清洁管理所填报城市公用事业职工人数及工资情况表》(1958年2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31-2-563。。这样的人力显然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为弥补劳动力不足,上海市除发动群众性的送肥下乡运动外,不得不将好不容易挡在门外的农民又“请”回来。1959年6月,上海市肥料公司召集青浦、南汇、松江、川沙、金山五县肥料方面的负责人开会,提出有垃圾肥料15000吨,钢渣磷肥、钙镁磷肥、过磷酸钙等3000吨支援晚稻,但川沙县以“质量差、成本高、运费大、群众不欢迎”为由,拒绝派船运输*《市肥料公司致市农委报告》(1959年6月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2-2-100。。与此同时,“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农村的积肥指标也在不断攀升,相关部门有意来沪积肥。一拉一推,农民入沪争粪的第三次风潮很快掀起。
从收集粪尿的情况来看(见表2),1959年至1960年农民进城收集粪尿量明显低于1961年至1964年。其中1960年最低,仅占总量的1%,原因可能是此时农民进城主要是收集其他种类的肥料。不过,粪肥比其他肥料的肥力大,因此1961年以后,农民进城积粪尿的比例再次上升。整体上看,从1959年到1964年上半年,农民来上海市或城市边缘地区收集粪尿量占总产量的9.2%。这一比例虽然不能与第二次风潮相提并论,但若加上运输河泥、垃圾等杂肥的农船,进城的农民数量仍然十分巨大。

表2:1959年至1964年上半年上海市人粪尿收集量统计表(单位:万车)
资料来源:《上海市环境卫生局汇编三五规划(提供的历史资料)》(1964年10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56-2-186。
事实上,由于此次风潮积肥的种类多,农民进城所造成的损失比以往更大。农民“有组织地入城积肥,引起了更多农民自发地入城寻找肥源”。由于无法管理,结果再次产生了“乱搞计划肥源,乱占岸线,乱设码头、坑池,乱埋粪缸,乱停粪车”,以及“捞粪坑不冲洗,不加盖”等情况;同时,还发生了农民贿赂清粪工人以争取肥源,扭打劝阻的清粪工人,半路拦截下乡的粪船、垃圾车逼迫交易等情况。*上海市肥料公司:《上海市的生活垃圾、粪便处理工作——解放后十四年总结》(1963年1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2-72。
这次争粪风潮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现象。一是原来没有被利用的化粪池和下水道中的粪肥受到重视。1958年,上海市约有90万人使用抽水马桶。这部分人每天产生的粪便量估计为1300余吨,经过管道长距离输送到污水处理厂后,只剩下约一二百吨黑粪。为了充分利用这部分粪便,上海市曾在虹口、杨浦、闸北、静安、黄浦、长宁、普陀等七个区污水管的分支管或进水口窑井中设置去水截粪装置1058处,每天捞粪肥约700吨至800吨。在此背景下,农民为了挖掘污水管里的粪肥,随意破坏沟管,导致污水漫溢。实际上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因为水管内的粪便水分很多,粪肥质量很差。
二是随着供求关系日趋紧张,出现了粪肥交易的黑市。如前所述,1958年3月,市肥料公司为了集中力量收集城市肥料,放弃了三个郊区办事处。由于行政管理薄弱,城市边缘地区黑市泛滥。1960年,上海市政府对粪肥的定价为0.6元一车*中共上海市肥料公司委员会:《关于1958年大跃进以来、城市下乡肥料部分质量不好及多计黄粪数量增加、农业成本需要退还农村款项初步核算的情况报告》(1960年12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2-2-356。,但黑市价格一度涨到6元一车。闸北区中山北路五号桥一带从1953年11月起就有倒卖肥料的活动,当时有粪担十多副、私设的粪码头一两座。到1958年,由于该地区养猪单位增多,以猪粪出售或换取饲料的情况普遍存在。1963年下半年,宝山、青浦、松江、昆山、太仓等5个县13个公社承包了该地区88户养猪单位3664头猪的猪粪和牛棚户78头奶牛的牛粪,每日粪便产量约3600担,共使用劳动力115人,其中农村派出劳动力31人,雇用倒流人口6人、职工家属49人、一般居民29人,私设粪码头达32座。*上海市肥料公司:《上海市的生活垃圾、粪便处理工作——解放后十四年总结》(1963年1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2-72。
三是随着粪肥价格高涨,不少市区单位开始参与牟利。原先需要缴纳“倒桶费”的人们发现,此时不但不需要交费,反而可以从中获利。许多市区单位在利益驱动下拒绝清粪工人清粪,转而自行清理,进行交易。据1963年3月调查,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公园、剧院、工区、幼儿园、里委会自行处理粪便的有108个单位。其中,普陀区五一中学以本校人粪尿为交换条件,要求昆山县周市公社代为养猪、提供猪苗和饲料,饲养、劳力全部由该公社负责。有的养猪单位以索要青饲料和“保暖草”为名,将猪粪包价提高到每头每月0.7元、0.8元,甚至1.2元。长宁区周家桥街道有16名居民索性从事垃圾贩卖活动,与农民交换粮票。*上海市肥料公司:《上海市的生活垃圾、粪便处理工作——解放后十四年总结》(1963年1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2-72。
“大跃进”运动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上海市仍然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约束农民进城争粪。相反,为了完成“支援农业”的任务,作为一种应急之策,该市主动选择让周边农民进城取粪。在这种情况下,争粪风潮只能随着“大跃进”运动的结束而逐渐退去。
1962年8月,上海市组织了由831名城镇居民组成的积肥队伍,“顶替”进城积肥的农民。1963年,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又同意组织生活困难的3000名城镇居民参加环卫工作。*《上海环境卫生志》,第398—399页。10月,上海市决定成立环境卫生局,同时将市肥料公司划归该局。这些举措表明,上海市已经将粪便清理工作的目标回归到维护城市自身卫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氨水作为肥料被应用到农业,上海郊区农村化肥供应量迅速翻番。技术革新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用肥结构,也逐渐结束了农民进城争粪的状况。从上海市各县化肥供应量来看(见表3),1963年相对于前一年的增量几乎全部来自氨水,之后几年亦是如此。就这样,上海周边农村的施肥方式从使用粪肥为主变为以化肥为主。化肥因其高效而在与粪肥的竞争中胜出,从而让农村对城市粪肥的需求大大降低。

表3:1950年至1972年上海市各县化肥供应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农业生产统计资料汇编(1949—1972)》,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45-4-160。
四、结 语
解放后,中共试图通过建立工农互助、城乡互助的新式城乡关系来打破城乡之间的对立。对于上海市的粪便清理和周边农村的粪肥供应而言,这一思路在某些方面契合了传统的城乡协作关系。借助农民的力量,上海市一度顺利解决了相关问题。不过,农民进城收集粪便也给城市清洁卫生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满足农民对粪肥的需要与保持城市清洁卫生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这种张力使得原本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涌入上海市,也使得上海市在三次农民进城争粪风潮中,不断在支援农业与保持清洁之间调适。
三次风潮中,上海市政府均未采取强力措施阻止农民进城,而是尽可能地解决农民进城争粪所带来的问题,化解其与城市清粪工人之间的冲突。从结果来看,政府似乎更加“偏向”农民——上海市及其清粪工人在三次风潮中都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农民却从城市中获得了更多的粪肥。这表明,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并非只是单一的领导与被领导、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是更为复杂多样。
从根本上说,城乡“二元”服从于经济“一体”,是国家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解放之初,上海市周边农村的粪肥供应主要服从于上海城市自身的卫生需求,仅就这一方面的城乡关系而言,城市显然占据主导地位。随后,国家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在城市清洁与粪肥供应问题上,上海市与周边农村关系的基调逐渐转向城市服务农村、支持农业生产。最后,随着“大跃进”运动的结束,上海市清除粪便的核心目标又回归到保持城市清洁卫生。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3级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赵 鹏)
AStudyofThreeIncidentsofFarmers’StrugglesoverManureaftertheLiberationofShanghai(1949—1964)
Xiao Anmiao
D232;K27
A
1003-3815(2017)-08-009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