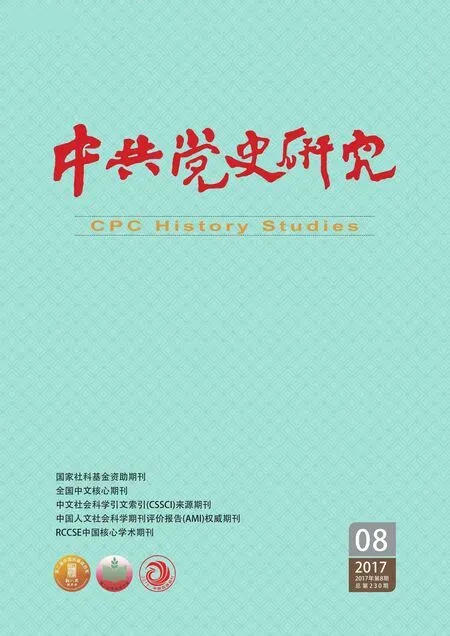《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材料来源考
——兼谈1921年“三月会议”是否存在
·史实考证·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材料来源考
——兼谈1921年“三月会议”是否存在
黄爱军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以下简称“张太雷报告”)是一份重要的党史资料。其中提到,1921年中共一大前召开过“三月会议”。不过,自从20世纪80年代报告节译本在国内公开发表*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52—555页。,学者们就对这次会议存在与否各持己见,虽经长期讨论,仍未达成共识。
众所周知,张太雷早在1921年1月即离开中国前往俄国,并于当年3月抵达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东方局(或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中所涉及的1921年1月以后中共创建的内容,显然并非出于张太雷的亲身经历,而是另有材料来源。因此,与其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张太雷报告是否准确可信,不如说材料来源决定了报告的准确性。
一、有关张太雷报告材料来源的几种说法
张太雷报告虽被冠以张太雷之名,实际上关于起草者,尚有一些不同说法。不少学者通过对张太雷报告与瞿秋白、李宗武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的比较研究,认为张太雷报告是张太雷与瞿秋白合作撰写的*参见叶孟魁:《一篇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王毓钟:《光辉的历史文献——读〈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张太雷研究学术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页;钱听涛:《中共早期历史上的双子星座——瞿秋白与张太雷》,《瞿秋白百周年纪念——全国瞿秋白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6页;郝赫:《太空惊雷——张太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丁言模:《秋白协助张太雷修改〈报告〉吗?》,《张太雷诞辰110周年纪念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9—190页。。李玲则认为,报告是由张太雷独立完成的,因为瞿文俄文打印稿第一页上有眉注:“摘自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1年”。而时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的舒米亚茨基在1928年撰写的纪念张太雷的文章中也回忆说:“张太雷同志到了伊尔库茨克以后,收到了共产党任命他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的委任,并要他担负准备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这一任务。接到指令以后,张太雷同志便全力以赴地干了起来。”*李玲:《关于〈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作者——与叶孟魁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其实,瞿秋白是否参与写作,对报告准确性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离华赴俄的时间比张太雷还早,同样需要依靠其他材料来讲述1921年3月中国国内的情况。所以,起草者之争本文存而不论,姑且假定只有张太雷一人。
那么,身在苏俄的张太雷通过什么途径了解中国的情况呢?石川祯浩提出了一种假设:张太雷在入俄以后从中国得到了新的信息。但考虑到当时中俄间的通讯状况,石川祯浩随即基本上否定了这一假设,表示“一时难以相信”。*〔日〕石川祯浩著,王士花译:《〈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一九二一年中共三月会议关系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冯铁金认为,是杨好德(杨明斋)提供了“国内情况方面的重要内容”,“其他人也可能提供过内容”,如维经斯基*冯铁金:《中共1921年“三月会议”新考》,《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叶孟魁、赵晓春认为,相关信息系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创始人之一俞秀松所提供。俞秀松于1921年4月下旬抵达伊尔库茨克,与张太雷会合。*参见叶孟魁、赵晓春:《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代表团人员考》,《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1期。上述两种观点缺乏文献材料支撑,同样难以令人信服。此外,石川祯浩还有一个推断: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另外两位中国代表俞秀松、陈为人,以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均有可能为张太雷提供材料*参见〔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9—220页。。其中,对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提供了材料的说法,笔者极为认同,但对于材料来源于俞秀松、陈为人的观点,笔者并不同意。
二、来源于俞秀松等人的可能性很小
按常理分析,晚于张太雷赴俄的杨好德、俞秀松、陈为人等,因肩负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或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任务,很可能带有国内建党、建团工作的新材料。张太雷与他们在伊尔库茨克或莫斯科会合后,获取这些新材料亦不困难。但如果仔细分析张太雷报告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小,至少张太雷报告中没有引述杨好德等提供的材料。下面以俞秀松为例,对此加以说明。
1930年,俞秀松在《自传》中记载,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引者注)的全部工作”。作为临时书记的陈独秀,则“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俞秀松没有指出四个城市的具体名称,但稍后参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活动的周佛海却在上世纪40年代留下的回忆材料中,明确列出了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四个城市。他写道:“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指成立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周佛海:《往矣集》,古今出版社,1943年,第27页。张太雷报告又是如何介绍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状况的呢?报告指出:截至1921年5月1日,中共已经有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北京组织、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汉口组织、上海组织、广东组织、香港组织、南京组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53—554页。。这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前中国存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是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以及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更重要的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计划推动建立党组织的长沙,未被写入张太雷报告之中,而不在上海组织计划之内的天津、香港和南京等地却赫然在列。如果俞秀松为张太雷报告提供了材料,一般来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俞秀松此次莫斯科之行,是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的。所以还有一种可能,即俞秀松为张太雷报告提供的其实是青年团的材料。考虑到当时党团不分、党团一体的特殊情况,不排除张太雷报告将团组织当作党组织来看待的可能。苏开华就认为,“三月会议”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一次改组会议*参见苏开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苏开华:《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性质辨析》,《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5期。。可是,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文件记载:“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88页。相比之下,张太雷报告中多了天津、香港、南京三个地方。按理说,俞秀松赴莫斯科开会,应随身带有较完整的团组织的材料,其本人对各地团组织的情况也极为熟悉,如果张太雷报告实际介绍的是青年团的情况,且俞秀松提供了新材料,那么报告与实际情况的契合度似应更高一些。
这里有一个问题:尽管张太雷报告的材料大约并非来源于杨好德、俞秀松、陈为人等,但不可否认,张太雷原本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他们那里获得有关中共创建的新材料。假如一定要推测的话,张太雷更有可能得到了这些材料,但没有用在自己的报告里。何以如此?笔者推断,应该是因为他手上有自认为更权威的材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能够享有如此权威地位的非共产国际莫属。加之中共创建者们深知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当时人们一般认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援助,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张国焘回忆:“陈先生(指陈独秀——引者注)向我说到我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性。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他又提到,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96—97页。,赢得共产国际的信任与认同,显然比材料本身更重要。
三、来源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可能性很大
1921年6月,张太雷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1921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次克,为了与东方书记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8页。7月,在“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议”上,舒米亚茨基通报了共产国际三大和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情况,其中讲得更加明确:“我作为远东书记处的领导人,和张太雷同志起草了一份报告……我们写了这个报告,为的是将其纳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之中,使其成为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并以此证明共产党的成熟。”*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3—154页。如果身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的舒米亚茨基确实参与了张太雷报告的起草,则相关材料几乎必然来源于远东书记处。将张太雷报告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有关档案材料进行比照,可以发现,二者的契合度非常之高。
首先,组织地点基本一致。张太雷报告介绍说,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5月成立,地点在上海和北京。而在共产国际看来,维经斯基在华活动取得的最初成果,就是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参见《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29—30页。。张太雷报告写道,截至1921年5月1日,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和南京七地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维经斯基则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提到,在中国,已经建立或准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有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汉口等地。随后,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增加了南京。这样,与张太雷报告相比,远东书记处的材料中仅缺少香港一地。*参见《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29—33、40页。
其次,组织名称基本一致。张太雷报告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称为“省级地方党组织”,而且他在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中特别注明,这些地方组织“均有选设的委员会”*《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44页。。类似地,维经斯基在华建立的组织被称为“革命委员会”*又译“革命局”。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1页。。1921年1月21日,舒米亚茨基在致科别茨基的信中说:“事实上我们上海的那个三人小组——革命委员会才是领导机关。这个革命委员会目前领导着中国六个省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规模相当的五个中国青年团组织。”*《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92页。舒米亚茨基这里所说的六个省的共产主义组织,当与上述维连斯基报告一致。
再次,工作内容基本一致。张太雷报告中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活动情况的说法,如通讯部向中国报刊提供关于苏维埃俄国和工人运动的消息,组织部在一些大城市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出版部出版《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周刊,印行《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等小册子、传单,皆与维经斯基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出版、宣传、组织等部门的工作内容相类似*参见《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29—30、41、83—84页。。沈海波在将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信中谈到的上海革命局的工作内容与张太雷报告进行了一番比较后指出,“它们在很多方面的记载是基本相同的”,只是由于后者的形成时间较晚,所以记载的内容更详细一些。由此,沈海波认为,张太雷报告可以证明,所谓革命局就是中共早期组织。*参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3—217页。这种分析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忽略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张太雷报告取材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提供的材料,其中自然包括维经斯基信中提到的情况。二者来源基本相同,无法相互印证。
此外,处于争论焦点位置的“三月会议”或许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张太雷报告的材料来源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一方面,在各种文献资料和个人回忆录中,均找不到“三月会议”的蛛丝马迹。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无论是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3月确实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何以与建党、建团有密切关系的俞秀松、施存统、周佛海、李达、袁振英、张国焘、陈公博、毛泽东、董必武、包惠僧等人均不曾提及?难道这些建党时期知名人物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无论如何都讲不通。另一方面,张太雷报告中的这个“三月会议”,却能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材料中得到印证。具体来说,1920年10月14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负责东方工作的全权代表冈察洛夫和东方民族处处长布尔特曼致电共产国际,指出:东方民族处打算召开一些远东国家革命团体和共产主义团体的“一系列预备性代表会议”。12月24日,东方民族处要求“不迟于三月初”召开该代表会议。*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页。1921年1月21日,舒米亚茨基在给科别茨基的信中写道:“中国定于3月下旬举行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我将派遣专人前去指导。”*《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93页。当然,这些材料不能证明随后确实召开了“三月会议”,对此加以“确认”的是舒米亚茨基在《远东人民》1921年第1期(出版时间大约是1921年5月*参见〔日〕石川祯浩著,王士花译:《〈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一九二一年中共三月会议关系考》,《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上发表的《共产国际在远东》一文。舒米亚茨基写道:“不久前在中国的中心(城市)举行了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会议”,会议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是“组织和集中群众斗争的力量,以使它的打击力量日益强大”,为此,要建立“拥有统一中心机构的强大的产业工人工会”和“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政党——共产党”*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第17页。。一些学者将上述材料作为证明“三月会议”确实存在的重要证据*参见王述观:《中共一大前曾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冯铁金:《中共1921年“三月会议”新考》,《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殊不知张太雷报告的材料来源正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甚至就是舒米亚茨基本人。
四、正确解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提供的材料
既然张太雷报告的材料来源极有可能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里有必要对共产国际档案文献的某些特点进行分析说明。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不知是出于信函联系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信息传递偏差,还是出于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共产国际的档案文献中,一些原本是工作计划、目标的东西,在随后的信函中直接被描述成已经取得实效的工作成果。其中,有关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情况就是最明显的一例。
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东方民族处的信中对其在华工作进行了展望:“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倾向革命的大学生组织起来,建立一个集中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该青年团的代表届时就可加入我们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革命委员会了。”“近两个星期以来,有我们的人参加,举行了上海、北京、天津的一系列学生代表会议,会上讨论了把所有思想激进分子的小组联合起来的问题。”“今天正在北京举行(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所大学的学生代表会议,以最终解决联合问题。因近几天来我就此问题同参加此会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团进行了接触、会商,所以在今天的会上,要求联合起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呼声应该是非常强大的。”*《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31—32页。信中写得很明白,截至8月17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未成立。更何况众所周知,青年团的成立时间是8月22日。然而,几个月后,在东方民族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维经斯基所展望的目标被描述成了已经完成的工作。该报告指出:“由于我们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里召集了一系列学生的代表会议,结果于8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这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刚刚建立的青年团的代表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第84页。。
考虑到共产国际档案文献的这种特点,我们是否也有理由怀疑,所谓“三月会议”其实只是一次停留在工作计划层面的“会议”呢?
综上所述,张太雷报告最主要的材料来源并非其他中共创建者,而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远东书记处的材料则主要来自维经斯基的各种信函、报告,这些材料既包括实际工作成果,也包括对工作的展望。因此,笔者认为,报告中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实际上主要反映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华开展活动的情况,包括维经斯基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所开展的活动。至于“三月会议”,则很可能并未召开。
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华开展的共产主义活动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及其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共产国际代表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与中共早期组织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前者由俄共(布)党员组织和领导,吸收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和其他各类社会主义者参加,是具有社会主义者同盟性质的组织;后者则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例如,受维经斯基派遣到广州组建革命委员会的米诺尔,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共产党组织”,这与人们熟知的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没有关系。由于工作卓有成效,尤其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斗争,各地中共早期组织逐渐取代了革命委员会的地位。随着1921年初维经斯基离华,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先后终止,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积极推动的“三月会议”或许未能付诸行动,取而代之的是随后由各地中共早期组织派出代表参加的中共一大。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希望通过召开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的方式宣告中共成立的建党思路,以另一种形式圆满完成。
(本文作者 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蚌埠 233030)
(责任编辑 赵 鹏)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共创建关系研究”(13YJA77001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