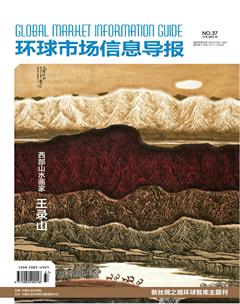音乐教育哲学中的“身体”审视
张业茂 韩林彤 王坤庆
当今,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方兴未艾,在实践逻辑的推动之下,与哲学从“意识”向“身体的转型相呼应,音乐教育哲学也开始转向对“身体”的关注。这既是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深化(从“心”向“身”的延伸),又是身体哲学在音乐教育中的实践应用,即从身心合一主体角度,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及启示。
哲学中的“身体”
对“身体”的理解,自古以来,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在意义、概念、用法等方面呈现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一般可以分为日常语境和学科语境两种理解路径。在日常语境中,对“身体”的解读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也很多。例如:王庆节归纳为“身三体五”。郭祥超认为日常语境有三种解讀。在不同的学科语境中,对“身体”的理解随着学科视角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在西方哲学视域中,对“身体”的理解,从自然和医学、理念与感觉、现象学、社会学、美学等角度可以归纳为七方面。西方哲学对“身体”的理解,正如倪为国在《身体的历史》三卷本中译版《关于身体“造反有理”的历史》(代序)中所言:“一部身体的历史,就是一部身体的‘造反历史,确切地说。或从根子上说。就是身体造‘精神反的历史。”
在中国哲学视域,对“身体”的理解颇有深意。哈佛教授杜维明先生在阐发儒家独特身体观的基础上提出过“体知”、“同心圆”等概念。台湾学者杨儒宾教授有专著全面论述“儒家身体观”。香港学者王庆节提出的“身体人心互动”和“情感感染”为核心的儒家身体观。在内地,李泽厚先生提出儒家有个“情感本体论”,蒙培元先生也曾多次论述儒家哲学的本质是奠定在心身合一的存在论基础上的隋感哲学。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对身体的理解,大致可归纳为三个层面,分别是作为哲学本体的身体、作为表达主体的身体和作为展现场所的身体。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身体观有“十个面相”不管如何,身体,作为世界上最精致、最完美、最脆弱的艺术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和性别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述说着不同的故事。
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
一般认为,西方哲学已经经历了四次转向,即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及当代的“身体哲学转向”。身体哲学(Philosophy of body,Philosophie du corps)或肉身哲学(Phil osophy of flesh,Philosopie de la chair),相对于意识哲学,诞生于西方传统哲学的“身体”转向,而其萌芽于心身问题。心身问题是哲学中最古老、最纠结问题之一。到西方近代,经笛卡尔的本体论阐述,身心二元论得到确立。也开启了整个近代思想对身体的遮蔽。笛卡尔以身心割裂、对立的二元论,奠定了现代性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石,精神/物质、心/身、主体/客体、本质/现象、内容/形式、价值/事实等二元判定成为现代哲学的主调。当现代性越来越陷入危机之时,当代的思想者又回溯到笛卡尔,以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批判展开救赎,而“身体”因此也成为当代哲学视域的焦点,身体的转向成为西方思想转向的主要标识。大有对意识哲学的彻底翻转乃至颠覆之势。从方法论上讲,“身体”研究超越了诸多的二元对立,身体达到了一种超越,它作为一种模式为其他复杂的系统提供了象征的源泉。甚至有学者认为,20世纪哲学最终实现了身体哲学的普遍化。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中叶,以美国贝内特·雷默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正式出版为标志。在此之前的音乐教育哲学知识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哲学,二是美学。如“唯理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音乐教育的哲学原理”,以及“所指论”、“表情论”、“形式论或绝对论”的“音乐教育的美学原理”等就是代表。雏形期的音乐教育哲学,沿袭了意识哲学的传统。正因如此,雷默的音乐教育哲学被称为了“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在全球音乐教育领域的兴盛,不仅使音乐教育就是审美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且也点燃了学界对音乐教育哲学关注的热情。音乐教育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开始了自己的快速发展。不仅形成了许多学术共同体,集聚了大批研究人才产生了丰富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许多新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20世纪末,随着哲学研究从“意识哲学”向“身体哲学”的转向,世界范围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在百家争鸣中也悄悄开启了新的进程——“身体”的转向。
从“心”到“身”——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作为音乐教育哲学中“意识哲学”的典型代表,经历了一个重“心”轻“身”到“心身”兼顾的过程。
重“心”轻“身”——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早期形态:从雷默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建构过程可以看出来,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早期形态是重“心”轻“身”的。雷默在找寻其理论基础过程中,探讨了思辨主义及形式主义哲学的优劣,认为“绝对表现主义的观点似乎最适合民主社会的大众教育;最忠实于我们时代所考虑的那种艺术的本质;最能萌发音乐教学以及各方面教育计划中的其他艺术教学的指导方针。”接着,通过对比绝对表现主义与思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异同,得出其核心观点就是“艺术体验与感觉相关”,而这种感觉“是一种心智的体验——是一种仅仅或者主要同纯粹的形式所给予的特殊情绪相联系的体验。”正因如此,雷默音乐教育哲学也可以被理解为“情感的教育”。雷默在肯定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审美教育时也认为,审美教育“是殖民时代以来第一次试图用充分一致的原则综合论述实践的有效性,论述并明确了音乐教育领域长期以来隐含的直觉知识(implicit intuitions),同时也试图满足哲学对批判和分析的需要的运动。”以雷默为代表的“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不仅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的审美教育运动开始的标志”,而且使得音乐教育中“关于审美教育的定义成为了最为流行的定义,很快被音乐教育的政策接受了,即对事物的审美品质的感受力的发展。”endprint
由此可见,雷默注意到了音乐与身体的关联,而且十分强调感觉在音乐教育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它的理论基础是近代以来的康德学说尤其是新康德主义学说”,使得他的哲学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哲学”烙印。尽管雷默的“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的思想在西方音乐教育史上具有“变革性的”意义。这种变革,把音乐从对人和社会的外在价值中解放出来,试图回归音乐对人的内在价值,但因音乐内在价值与人身心关系问题上的游移,最终把其理论归于“心智”而非整个“身体”,使得“审美音乐教育”哲学早期形态具有浓厚的“扬心抑身”特点。
“心身”兼顾——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当代发展:从《音乐教育的哲学》第二版(1989)开始,雷默虽然坚持了其美学立场,但引入了卡尔·荣格(Carl G.Jung)、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mheim)、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等人的认知心理学的成果,对审美认知模式进行了细致论述。这标志着雷默开始对其“意识哲学”,向着“身心兼顾”的方向进行改造。其理论建构也仅仅围绕“体验”——一种身体性的关照而展开。因此,他认为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们观察事物所体现出来的具有表现力的品性,并对那些品性的内在意义作出反应的能力。”“审美教育的任务是影响人们得到审美体验的能力。”因此,在音乐教育实践中,“选择音乐的标准在本质上与历史是无关的,要有充分的技巧性、感受力、想象力和准确性,足以加深所教学生的音乐体验。”并且把这种审美体验或情感经验与人的生命体验相关联。其中所透射的生命哲学意蕴,表明了其“身体”转向的趋势,但他把这种转向仍然局限在身心二分的哲学语境之中。他认为“如果艺术经验对人的生命有意义,那么,这种经验必须是审美的”,而且,这种审美的经验或体验是“与世界的一种思想的、心灵的互动,与其他互动具有显著区别”。把体验局限于“思想”和“心灵”,虽然是对“身心二分”的坚持,但也体现出了“身心兼顾”的特点。
这种“身心兼顾”的特点,在《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2003年版)中得到了全面体现。第三版中雷默试图调和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其他音乐教育哲学的矛盾,尤其是为了缩小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鸿沟,隐退了“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全面推出“基于体验的音乐教育哲学”,牢牢抓住情感体验中的身体性和意识性,并且围绕“音乐体验的感觉尺度”、“音乐体验的创造尺度”、“音乐体验的意义尺度”、“音乐体验的情景尺度”展开详细论述。在后现代音乐教育哲学特别是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种种诘难中,以一种“融合”的态度,开始了由“意识”向“身体”的转向,最终体现为“身心兼顾”的哲学立场。
身“体”力“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意蕴
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不仅仅是因为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质疑而产生的,其时代背景就是哲学的“身体”转向。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以實践的身体载体为主体,全面展开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中“扬心抑身”弊端的批判与反思,建构其音乐教育的“身体哲学”。因此,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具有“身体哲学”的诸多内涵和特征。
音乐教育“实践”强调身“体”。“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坚持认为,音乐不仅仅是声音、乐章的存在,其本身就是一种多样性的人类行为。因此,人与音乐之间不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取消了主体客体对立状态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人不是要去对音乐进行审美,不是持一种高贵的态度和情感,而是要参与、要融入。音乐不再是是一种客体,它就是我们的行为。”由此可见,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主体已经转向了身体主体。虽然表面看起来,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主体好像都是身体,但本质性的差别在于,审美音乐教育的“身体”实际上是“意识”——一种主要涉及大脑的思维活动;而实践音乐教育的主体强调的是身心合一的“身体”——整个身心都需要参与、融入。从而使得音乐教育的“实践”强调的首先是身心主体对音乐的“体”,包括埃利奥特所说的音乐创造之“体”与音乐聆听之“体”,这种“体”具有四个维度。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体”,不仅强调音乐创造之“体”,而且是反思之“体”、身心合一之“体”。这首先缘自于对音乐教育现实的反思。美国音乐教育史家马克认为,19世纪开始尤其是20世纪以来美国音乐教育没有创造出具有音乐能力的美国公众,而使“美国成为了一个听众的国家。”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对审美聆听的强调似乎加重了这种倾向。针对这种现象的反思与批判,随着国际化与多元化时代的来临变得更加激烈。在此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以1993年5月1日成立的“五月组”为代表,就旗帜鲜明地认为,应该用批判性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音乐教育的目标和实践,“因此,任何音乐技能、知识和理解的正规教育都应该同时是批判性的、反思的而非不加思考的、流于表面的音乐制作。”这说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是在兼容“意识哲学”的反思性基础上展开其“实践”的,也表明其身“体”是一种身与心同步参与的“体”,而非其一。同时,身“体”的创造性必然体现为一种“行”。
音乐教育“实践”旨在力“行”:“五月组”认为,音乐性行为对其结果极为关注,它不仅是音乐制作的必要条件,也是有效进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条件。作为最早的“艺术实践观”(Praxialview ofart)提出者,阿尔佩森认为“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会把音乐性的和道德性的辩证关系作为一个严肃的学习目标”。应当承认,由于“实践”(praxls)一词的源头意指…正当结果(right results)的伦理标准下的‘行为(dolng)。”这种行为是建立在伦理标准(实际是一种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因此,不同的人对“实践”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在音乐教育中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把实践看作“单纯的听赏”(just listening),认为在听赏中激发情感体验是其最终目的;二是把实践看作技术、技巧,认为音乐教育的目标就是提高音乐技能;三是把实践看作在一定语境中的行为,因此它包括着对行为结果进行判断的智慧。endprint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中的“实践”是立足于第三种理解。里吉尔斯基认为第三种观点“包含了对‘正当结果的智慧判断,即什么是对人类的需求、愿望、目标、价值和意义是‘有益的,而这些是远远超乎传统的审美理论所具有的视野范围内的”。韦恩·鲍曼认为:音乐实践是有思想的行为;对音乐实践的学习或描述必须密切关注人们音乐行为中的各种细节;音乐实践来自于人们多种多样的同时又是具体的社会活动和互动,并被其影响;音乐的社会文化是决定音乐本质的因素之一。埃利奥特在1995年出版的《关注音乐实践》一书中更是明确表示:名词“Praxis”从动词“Prasso”而来,意指“行动”或“有目的的行动”,“Praxis的意思体现了特定情境中的行动,并对行动作出回应和反思。”
所以,音乐教育“实践”旨在力“行”。这种“行”是反思基础上的“行”,是身心合一的“行”,是知与行的统一。
对音乐教育哲学“身体”转向的思考
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实际上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末,达尔克洛兹就开始思考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许多学生有非常高的演奏技巧,但缺乏乐感以及对音乐的情感反应,无法感受和体现音乐的美感,一些学生对音乐中的节奏理解只能停留在数字式的机械反应,无法感受音乐的流动性等。对此思考的结果在1902年及1906年分别出版的《实用音准练习》及《达尔克洛兹体态律动教学法》两本书中得到集中体现。达尔克洛兹认为,人类通过身体将内心情绪转译为音乐,人的身体运动包括了对音响和情感反应的一切基素。在大脑与活动着的身体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直接发应,任何乐思都可以通过身体表演出来。卡尔·奥尔夫在吸收达尔克洛兹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奥尔夫教学体系,即一种新的节奏教育一一元素性的教学。奥尔夫教学法要求最求音乐的“原本性”,即音乐与动作、舞蹈、语言緊密相结合,此时的音乐是一种人们必须亲自参与的音乐,不再只是听众而且是演奏参与者。奥尔夫强调“原本性”音乐是接近自然的、机体的、能为每个人尤其是儿童所接受的。因此,他从节奏人手,强调身体的全面参与,这也是身势节奏的本意。同时,奥尔夫乐器和即兴创作也是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它要求参与者全身心地投入,集中思想地体验、感觉,编码于脑中,再解码、分析,输出指令肌肉运动,成为动作和演奏。其他的许多音乐教学法上的探索层出不穷,也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音乐教育中的“身体性”。
音乐教育哲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因成长于社会变革与转型异常复杂的20世纪,也使得自身的理论建构处于变化发展的不稳定状态。“两千多年来,即使不总是在实践中也是在理论上,身体和感官一直被看作心灵和理性的对立面,并且在任何有关人类特征的讨论中都被降到次要的位置。”而且这种“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固有的二元论——精神一肉体、客观一主观、形式一内容——在美学中已经和在哲学的任何其他分支中一样根深蒂固,因而确保艺术是非身体性的这一信念得以延续下来。”但是,随着“意识哲学”向“身体”哲学的转向。音乐教育哲学的整体发展趋势也正在实现“身体”的转向。也就是理查德·舒斯特曼从身体美学角度所提出的一种“以身体为中心”的学科构想:身体具有本体论、认识论的重要地位,在伦理学一政治学中也具有基础地位。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各种范式之争已经见证了音乐教育哲学从“身心对立”逐步走向“身心合一”的发展趋势,也预示了音乐教育身体哲学时代的来临。
应该承认,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也得益于音乐人类学的发展。音乐人类学研究成果除了提醒我们音乐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之外,还对音乐的“生命性”、“整体性”给予了高度重视。对人的“音乐性”的“生命”与“身体”内涵的充分挖掘,也进一步促进了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对非洲人来说,音乐最有效地象征着社会分享和社会参与……当我们将非洲音乐囊括进音乐教育和研究中时,那些建立在西方传统的主体与客体、身体与思想二分法基础上的模式以及代表原子式个人主义的模式都应该被抛弃。”印度萨朗基音乐再次证明:“印度音乐能够在建构美学的界说中贡献出许多有用的因素。印度在寻求声音的音质、音色的丰富、声音的圆满方面没显出多大兴趣。……通过印度音乐生命节奏的直接效果,节奏模式发挥着更直接的、更动人心弦的影响,超过旋律模式,它导致了恍惚的状态,将人们引入联系微妙的实在,而不是在节奏模式自身中追求美。”
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也引导音乐从技术向“身体”、“生命”、“生活”回归。音乐教育哲学视域的“身体”转向,在音乐教育领域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面对几千年,空泛说教制造的虚假人格,抽象理性编织的虚幻主体,后人类社会的人们将极力消除意识和精神的异化,积极倡导回归被一些狭隘的理性疏离了的身体;要人们普遍信仰身体、重视情感、悦生轻死,以恢复人的真实本性。”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以身体为准绳,不是以陈旧的灵魂或伦理道德为基准,将是一种令人惊异的思想和举动。”过分的解读必然带来身体的重新分裂,即重视“身”而轻视“心”的问题。目前,音乐文化领域的“娱乐至死”,音乐教育领域的媚俗现象等,特别是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至上的今天,音乐教育特别要警惕打着“身体转向”的旗号,把音乐教育身体哲学引向极端,从而走向“扬身弃心”的窘境。美国学者戴奇沃迪在《身心合一》中认为,身体是一本活生生的心灵自传,人的身体与思维、个性、品质、情感、生存能量、感觉知觉和自我意识之间天生就合而为一。同时,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历经几千年的延续和发展,在身体哲学领域与西方哲学殊途同归,也是音乐教育哲学的中国化建设重要的思想源泉。
基金项目: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CCNUl5A060151)。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