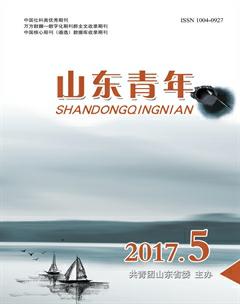书法创作中的美术倾向
陈若冰
摘要:书法创作从广义上说,主要是书家通过择取特定的文字内容,在宣纸上通过笔墨语言的表达来进行的创作。整幅作品的呈现是以宣纸和墨汁所构成的黑白空间,墨虽分五色,主要的成分还是以黑白调子为基础,色泽上比较单一。但是书法创作蕴含了书法创作者的审美情趣与方向,其中有一定程度和意义的美术倾向。
关键词:书法创作;美术倾向
书法创作是一项书法艺术家统筹全局的综合创作活动。书法创作包括了物质材料的择取,书写内容的挑选,章法形式的布局等。这个过程里有部分反映了书法创作的美术倾向。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法创作最基本的考量,首先是用纸。现在书法用品市场的纸类产品有很多,广义上说,有生宣、熟宣、半生半熟宣;细细分類,从纸面花纹看,有各式各样的彩宣,印制的花色、图案都有别;还有人为做旧的仿古宣。每一种类的纸张所带来的墨色变化不尽相同,生宣比较容易产生墨色的分离,朦胧的视觉效果,熟宣就使得墨色比较凝固呆滞,而不同色泽、不同花色的宣纸更能带来不同的视觉感受。因此,在纸张的选择上,空间和余地是很大的。书法创作者出于对创作效果的考虑,一则以墨色表现的不同要求来选择生宣或者熟宣,二则可以通过纸面的色泽或者图案来选择是何种宣纸纹样。因此,书法创作者在作品创作时,既然选择了某一既定的纸来写,就有其特定的美术倾向。北宋时期,流行使用皮纸。一来,其做工精良成熟,二来,经过研光后的皮纸,其色泽呈现出自然的斑点状痕迹,有低调的锋芒。北宋米芾所写的《苕溪诗卷》就是用经过研光后的皮纸,纸张为浅灰色,且有纹路,也为其增色不少,在这样的纸张上写字,墨色变化是很明显的,同时,字也显得飘逸有致。
再者,书法创作中的美术倾向存在于章法布局的考量。无论尺幅的大小如何,书法创作所选取的内容,正文和落款,都必须安排在一张纸上,通过字距与行距的排列,黑白关系是很明显的。选择留白的多少,对于整篇作品的风格表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留白多的作品,行气上比较舒朗,一般也比较清秀雅致,好似杨凝式的《韭花帖》,此帖在字距上拉开,布白也比较多,加之带有王羲之笔意,董其昌说其“萧散有致”,在整幅作品中,前两列的字距还相对紧凑,后面则愈加舒朗起来,此外,字内空间的留白,最经典的是“實”,这一字的宝盖头与下面部分的距离之空,堪称大胆,妙在留白之多。留白比较少,章法上比较密集排列的作品,自然显得比较严谨,风格上也不那么轻松。在金农的“漆书”作品中,字距和行距都比较紧密,加之,结体的紧结,行笔有折而不转,周围的留白也不多,给人逼仄的感觉,章法上就大气磅礴,给人浓墨黑沉,厚重的视觉感受。除了字距和行距的排列,同时还需要兼顾到内容与落款之间的位置安排。尤其是字数比较多的作品,在哪个位置落款,正文内容需要安排几排几列比较合适,这些都影响到最终作品的视觉效果。安排得当,那么作品就显得充裕有形式感,没有安排,最终作品的效果就事与愿违了。
在书法创作的收尾阶段,也就是落款处,从印章风格的选择以及印泥颜色的深浅程度来看,也有一定的美术倾向。书法创作者在气势雄强,表现力十分丰富的作品中,宜选择刀刀见骨,随性变化的汉印来呼应;在比较秀气的小楷类作品中,印章自然应当选取比较规整细致的小印。而且印泥的颜色与纸张的底色调也要配合协调,在一些浅色的宣纸上,选择太过艳丽的印泥,作品的基调也变得轻浮起来,深色的印泥自然在色彩上更能产生一定的对比,因此这些细微之处都是美术在书法创作中产生的小小作用。
当然,除去这些,书法创作作品不乏有一些形式上的加工改造。比如对于纸张的二次加工,做旧、染色,以及不同颜色的纸张进行拼贴,这些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美术效果和意义。在现今的各级书法展览中,对于纸张的二次加工改造,以及形式的拼贴,都很常见。单一的白宣显得单调,在形式上的变化,丰富了作品在展厅所呈现的视觉效果,对纸张的拼贴做旧,显示了创作者在不断尝试中寻求最契合创作内容的形式感的探索成果。在形式上有思考,同时下一定的工夫,增加了入展胜算,在最终展厅的效果呈现上,也有一定积极的意义。这也体现了书法创作者对于作品的二次创作能力,只要不过分追求形式感的加工,还是值得提倡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考验了创作者基本的甚至严格的美术审美能力。首先在做旧上,要考虑到做旧的程度,在色泽上要为作品的基调增加古意,否则就适得其反。在染色上就必须有清楚的美术意识,何种颜色,更能使得作品的表现力更强,更有感染力。在拼贴上,同样要照顾到色彩的对比,或者协调,哪几种颜色的纸张能相互映照衬托。这些美术功夫都难以小觑。
书法创作中的美术倾向,是书法家个人审美的选择,本来无可厚非,不过难以否认,好的审美起到了一定的锦上添花的作用,毕竟世人多爱王羲之,书法创作选择素雅清净的风格总是要讨巧许多。但不能太过夸大书法创作中的美术倾向。毕竟书法创作的主体还是笔墨线条语言,技法仍然是主要的。脱离了这个主体,而大肆地在形式上做文章,这样的书法创作是虚有其表的。古人在形式感上比今人要弱化许多,大多都是信笔。今人在纸张的选择、尺幅、内容编排、以及形式感的加工上花费了很多的力气。古人书写,是在比较自然的状态下,因为毛笔是日常书写的工具,不带有目的性。在自然的状态下,技巧能够无拘无束的发挥,有很多书法家如王羲之、米芾,即使尺幅如此小的信札仍然能够流传后世。他们不考虑形式感,他们只考虑技巧、情性动人。当然,如今,写字的人多了,比赛多了,竞争也多了,一张白宣随意书写,或者是信札,已经毫无分量,不能满足现在紧张的赛事,这是时势所趋。不过,拼贴成风,对形式感的大肆强化,同样不可取。
在此前的国展中,就有不少在形式感上大做文章的书法作品。最常见的是,以尺幅的过分巨大来博人眼球,尤其是部分小楷作品,通常都是鸿篇巨制,行距字距都密不透风,大有逼仄的气势,却只是虚张声势,有数量而没有质量,因为如此庞大数目的书写难免导致创作者眼力与笔力的配合不周,精力疲竭,线条质量不佳,小楷还是要小而精。行草作品也在体例上追求“大”,以长线条居多,以示绵延不绝的张力,这都是为了能够在评选中有突出的视觉优势,不过长线条多了,未必都是好事,反而暴露了笔力软滑的弱点。甚者,在纸张上采取了过度的制作,故意夸张地残破,用茶叶来做旧,以求纸张有年代感,有古意,创作者忽视了作品的古意来自于作品风格的整体气息,而非在形式感上妄下太多的工夫。此外,在展览中,有不少作品存在印章的过多使用。古人作品中的印章往往是收藏家所盖的专属标识,而今人作品里,却将印章作为形式的一部分。印章的数量有过分增多的趋势。一幅作品,到处都是印章的痕迹,超过三个,往往就觉得过多了,反而有适得其反的视觉效果。因此对于书法创作的美术倾向也要一分为二地去认识。
在现今的很多书法赛事中,对于作品的规格与装饰都有了严格的要求,大字作品一般不超过六尺,小字作品不超过四尺,对于过度拼贴装饰的作品也不予支持,这都是书协针对以往过度夸大尺寸与过分装饰的作品作出的应对。因此,书法创作作品,首当其冲的还是技法,书法创作是以笔墨语言为支撑的艺术。形式感也是必须的,它反映了作者的审美情趣,与创作者作品的气息风格有呼应,因而好的作品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书法创作中所反映的美术倾向,是书法创作者除却首要的笔墨创作之余的再创造,能够起到一定的锦上添花的作用。但它毕竟不是书法创作的主体,过多地夸大这部分,就是本末倒置,失去了书法创作中美术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书法美学 金学智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4
[2] 书法创作论 郭子绪年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0
(作者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