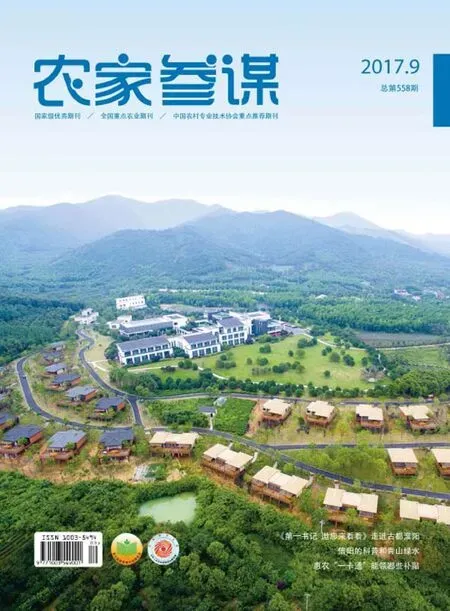乡下唱小戏的二叔
李中军
乡下唱小戏的二叔
李中军

生活在乡下的二叔为人和善、热情,会说书唱小戏。在我儿时记忆里,二叔那时候在周围十里八村有很高知名度,是当时的“明星”人物。二叔走乡串村说书唱小戏的一幕幕,至今还清晰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很小就从父亲那里知道了二叔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二叔童年时就天资聪慧,爱唱爱跳,那年代,大家都还靠工分吃饭,二叔跟着爷爷奶奶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是大家劳累之余的“开心果”。劳动休息时间,大家会让二叔唱段样板戏,二叔吼着童音,配着夸张的动作,会让大家笑得肚子疼。二叔最初是从公社广播里学会了《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后来渐渐长大的二叔参加了公社宣传队,直到人民公社大锅饭解散,二叔才领着同在宣传队的女友结了婚,不再唱样板戏。没有多长时间,乡下人家有了收音机,乡亲从“话匣子”里听评书、现代戏曲,二叔又跟着学唱起来大鼓书、坠子书,二婶当初也是公社宣传队骨干,拉一手好弦子,二叔夫唱妇随,开始在十里八村唱小戏。
那时,村里还没通上电,天一黑,什么活儿也干不了。村里乡亲们还很穷,极少看上电影,也聘不起剧团大戏,能让乡亲们消费得起的娱乐活动,就是请来唱大鼓书、坠子书的民间艺人唱小戏。二叔收费不多,没钱给点粮食也行,由各家各户平均摊对,还要管饭,一般都是村干部家管饭,也有全村各户轮着管饭的。乡亲们生活都不好,也是粗茶淡饭,多少有俩农家菜、自家酿制的米酒。
二叔唱小戏一般都是在乡亲们夏季农闲时节或冬闲季节的夜间,乡亲们会呼朋唤友相聚村中,热闹非凡,每户人家都喜笑颜开。二叔唱大鼓书、坠子书都是整剧本地唱,会唱上十天半月才结束剧本,要不,村里的戏迷不罢休。
那时,天一黑下来,早早吃罢晚饭的乡亲们已经围坐在村内空旷场地。表演舞台无非是一张方桌,几把木椅子而已,村内负责问事的叫作“会首”,帮着支起鼓架,将小鼓放到支架上,二婶忙着调试弦子定音,二叔将汽油灯调试得煞亮,将周围场地照射得如同白昼,照着每个人的笑脸。周围乱哄哄的人群,不到开戏是不会停止的。二叔唱大鼓书时,会一手高扬一对铜月牙形简板,一手拿一根细长的鼓槌,打起简板、敲响小鼓,一阵有节奏的“打闹台”开场白后,便可开始绘声绘色地表演说唱。如果是唱坠子书,那就打起一对长木简板,二婶会拉起弦子伴奏。每次,二叔都会按照行当传下来的规矩,先作首在我看来是乱七八糟的所谓的诗才开唱。
二叔唱戏吐字清晰、表情夸张,加上曲折的故事情节,听起来十分过瘾。有时,二叔唱到情深处,会声泪俱下,二婶也会将弦音伴奏得很低沉,悲从中来,听众也往往情不自禁泪流满面,替戏中人物命运担心。唱到高潮时,弦音急促,二叔就会慷慨激昂,手舞足蹈,场内听众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到了深夜,才能停戏收场,乡亲们恋恋不舍地讨论着剧情散场。我喜欢听二叔唱的坠子书《岳飞传》《杨家将》等,至今还能学着说上一段戏词。
就这样,二叔说唱了大半辈子,直到人们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电视机、电影时代到来,乡下人渐渐不再请艺人到村内唱小戏,二叔也老了,身子骨不硬朗了,声音也苍老无力了。如今,网络发达,想听什么样的戏、看什么样的节目,随手可得,也许没有几个人记得二叔这位民间艺人,而我却无法忘却儿时看二叔在乡下唱小戏的美好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