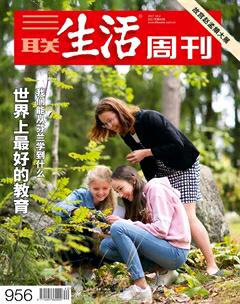假如莎翁的人物复活在400年后
蒲实
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能“翻版”到现代社会里吗?这些“翻版”如何对应和调整?
与我同时代的作家会如何改写莎士比亚的作品?这是“霍加斯·莎士比亚改写”系列这套书引发的最初好奇。“改写”听起来像是一个“移花接木”的工程,把400年前作品里的人物植入当下的生活里,在一个现代场景里“复活”古人的命运轨迹;又或者,像一套“变奏曲”,对一部经典戏剧在形式框架内做出微调,以此去审视和建构现代生活。
翻开书之前,我设想如果自己面对这项改写任务(显然自不量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摆在面前。简单列了一个单子,这些问题包括:
古代社会的皇室和贵族阶层在现代社会里对应着什么角色和身份?(比如《暴风雨》里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和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又比如《冬天的故事》里的波西米亚王波利克赛尼斯和他的童年伙伴西西里亚王列昂特斯。)
宫廷里的流言蜚语、窥测和信息传播方式,如何被现代媒体所替代?
与400年前相比,女性的角色、男女关系和婚姻观念所发生的剧变,如何能装进这类主题的框架结构里?(比如《驯悍记》里充满争议的对女性的驯服和男权主义。)
用在一些古代故事并不显得突兀且不可或缺,推动剧情向前的魔术、神化、精灵(比如《暴风雨》中制造电闪雷鸣的精灵爱丽儿)和传奇(比如《冬天的故事》里从雕像中复活的赫美温妮),如何在现代故事里被复制?
而核心的问题也许是,莎士比亚作品里的人物,真的能够在400年以后的时空里原样复活吗?400年前的剧中人穿越到21世纪,命运会在他们身上如何展开不同的轨迹?被预言或诅咒的命运如何在不再相信预言的现代人身上显迹?古代人命运中的必然,会成为现代人生活里的偶然吗?比如,《冬天的故事》里西西里亚王列昂特斯之子迈米洛斯之死,是特尔斐之神对列昂特斯嫉妒之心的诅咒,“终生无嗣”是神谕的应验。“神谕”像“如来佛掌”,充满了无法逃脱的必然性,它是一场事先的宣判(如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命运),或是一个绝对必然的条件式因果链(列昂特斯如果遗弃妻子所生的女儿,那么将失去儿子);所有逃离的挣扎最终也不过徒劳,反而成了回归宿命的“绕路”。但放在一个现代性的场景设置里,这样的确定性还能令人信服吗?如何用充满“不确定性”的偶然事件,替代莎翁剧里的“命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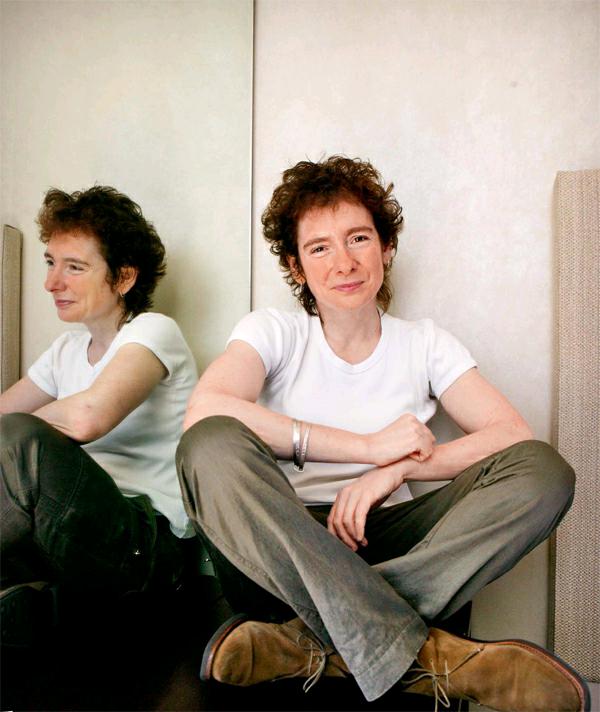
每一个作家都给出了自己的有趣回答。
《女巫的子孙》:复仇和喜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改写的《女巫的子孙》寻求一种和原剧较为严格的对应。它是一个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个剧情套着另一个剧情:极富才华的话剧总监有一个与《暴风雨》中主角普洛斯彼罗一样的复仇动机,打算在监狱通过排练《暴风雨》来实现复仇,最后通过复仇,呈现出《暴风雨》里普洛斯彼罗的命运。故事依旧是一个复仇和宽恕的故事,它与原作的密切对应关系,让《暴风雨》的剧本成为主人翁命运的暗示。一开始,现实里的普洛斯彼罗与《暴风雨》里的普洛斯彼罗就有高度重合的动机:被下级篡夺了权力(或管理岗位)和被放逐到孤岛(或自我放逐到荒野村舍)的人。400年前普洛斯彼罗的人生轨迹就像是某种先验的预言或诅咒,笼罩于400年后的普洛斯彼罗未来的悬念之上,唯一的问题只是:他将如何实现复仇和反转?尤其令人期待的是,他将如何在21世纪的现代场景下召唤在《暴风雨》中令人信服的魔力——实现复仇和推动所有后续剧情的关键因素,来铺陈自己的命运?
改编剧中对“普洛斯彼罗”的人物设置不同的是,话剧总监妻子生产死去,他独自带大的3岁女儿(叫米兰达,与莎士比亚原剧中的普洛斯彼罗的女儿重名)又不幸夭折(原剧中普洛斯彼罗与已经长大的女儿一起生活在孤岛上)。这是一条非常吸引人的线索:隐居在村舍的“普洛斯彼罗”在独居生活里,一天天、一年年开始出现幻觉,死去的女儿已经6岁了、9岁了、12岁了,他给她讲故事,她开始读书写字了,天天和他一起吃饭,与他交谈,他能听见她在窗外跑过时惊起草丛的响声和在门外歌唱的声音。这显然是一种幻觉,在现代人的生活里,更科学地说,可能是某种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的病兆。如果说莎翁笔下的普洛斯彼罗能够以法师的身份与超现实的魔法和精灵为伴,那么400年后,这种精神幻觉将如何展开就特别令人期待:并不真实存在的女儿,最终会以何种方式,在一个祛魅的理性世界复原莎翁原剧中的魔幻部分?
魔法的施展者作为暴风雨召唤者和幻象的制造者,是《暴风雨》中最重要的一场戏,推动着后面所有人轨迹的相交和命运的展开。阿特伍德首先将这种魔力转化为了现代技术。在新锐戏剧导演的解析中,“假如爱丽儿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许会把他称为特效师——灯光、音响、计算机模拟,所有这些。他就像一位数字技术专家,做的是3D虚拟”。在这样的背景下,舞台实施方案是一个技术解决方案,将“元素精灵”诠释为像气象网络那样的全息投影。然而,将要报复的仇敌从现实场景(作为戏剧舞台的监狱)驱赶到现实与戏剧重合场景(被困于一个监狱房间)的关键,并非这些3D虚拟,而是一声枪响和仇敌政治盟友的儿子被安排的失踪——他被安排与饰演米兰达的话剧女演员相遇并产生爱情,这与原剧情节产生了一些交错:一个现实中和那不勒斯国王的儿子相对应的人与一个在剧中扮演米兰达的人相遇相爱,在下一代人身上,复仇故事生发出喜剧的端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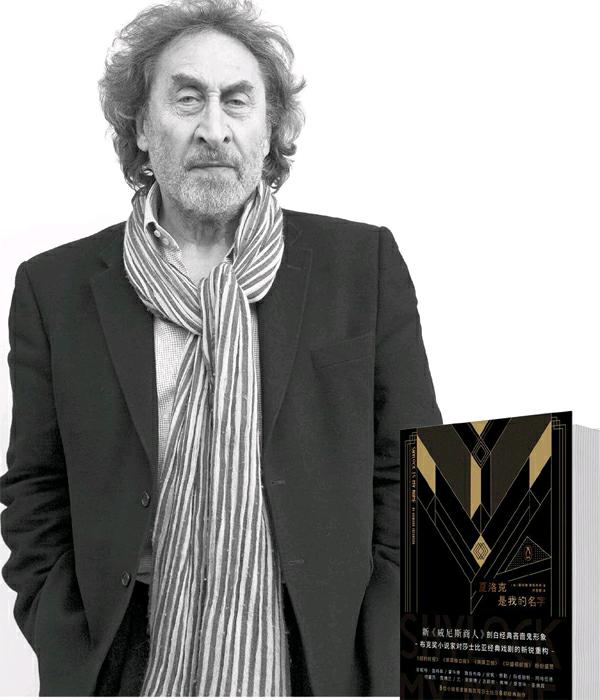
夭折的女儿米兰达最终并未对应本色出演(也不具有现代的真实性),而是扮演了精灵爱丽儿的替身,以声音幻觉的形式出现:当饰演普洛斯彼羅的现代“普洛斯彼罗”将作为道具的权杖举到空中,象征手腕通电,吟咏“来啊,我的爱丽儿”时,他的右耳畔传来了米兰达的声音,“充其量只是轻轻耳语,念着爱丽儿的台词。这是米兰达融入排练的角色——爱丽儿的替补,这一段只有他能听得见,其他人听不到”。在这里,阿特伍德也诠释了对莎翁原剧中爱丽儿这个角色的理解:作为一个精灵,为什么普洛斯彼罗可以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最后爱丽儿为什么离开了消失了?他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普洛斯彼罗的一种精神幻觉,在他不自由的时候尾随他,当他因宽恕而获得自由时,这种幻觉也就消失了?如果说这个幻觉具有它自身的生命,那么它也获得了自由。正如在解读莎翁文本时,监狱的业余演员问:“如果爱丽儿是一个投影,那么是谁投射给他的呢?是普洛斯彼罗吗?爱丽儿是从普洛斯彼罗的脑子里产生的吗?当普洛斯彼罗说‘你可以自由地回到空中,放爱丽儿走的时候,他就直接消失了,忽然间就没了。”endprint
《女巫的子孙》最后揭开谜底的方式,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但又不能不说精彩。复仇并没有在监狱的戏剧演出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联系,而成了一场戏剧中的一个具有戲剧效果的片断;这个片断因为预先设置的诡计,让现实中的人以一种抽离戏剧的状态(误以为监狱暴动),在戏剧的舞台上(全景式监控的监狱房间里)上演了一出事关现实(政治盟友间倾吐亡国和各自算计的谈话)的戏剧对白(与《暴风雨》剧情重构),这成了现实中“普洛斯彼罗”复仇的最关键转机,也是嵌套结构里莎翁戏剧和主人翁人生戏剧的一个交叉点。现实与戏剧的跨时空对应是短暂的,不过是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现实之人成了戏中人,戏里戏外的界限模糊了,400年前与400年后人物的命运像影子一样重叠在一起。
阿特伍德也像一个文学分析学者,在剧中插入不少对莎士比亚原著的理解。比如对莎翁剧中粗俗语言的幽默化设置(要求监狱囚犯在排演时必须使用剧中的脏话),对莎士比亚充满血腥和残忍情节的评论,以及对角色的现代疑问,比如“麦克白是个精神病患者吗?麦克白夫人是一直疯疯癫癫的,还是出于愧疚才变疯的?理查三世本性就是个冷血杀手,还是时代和他那个彻底堕落的大家庭促成了他的命运——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这些插叙,打破了“经典”和“圣洁”印象,莎翁的戏剧本就是极富粗俗市井气的生命力的啊!
《凯特的选择》:他人意志
安·泰勒的《凯特的选择》则有一个强烈的变革原作的动机。选择改写莎士比亚的《驯悍记》恰恰因为这是安·泰勒最不喜欢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它满是控制女性的观念,而且以此为荣。泰勒显然想为这部“裹小脚”的剧重新赋予两性关系以意义。相比其他三部改写作品,《凯特的选择》更接近当代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让人想到诸如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科尔姆·托宾的《布鲁克林》、理查德·耶茨的《革命之路》或伍迪·艾伦描写知识分子的当代作品,都有一种缺乏戏剧感的平淡无奇,却又在这平淡无奇中暗自堆叠着构成“命运”的一层又一层偶然。面对“命运”“人性”这些宏大主题,日常生活的细节、琐碎却非常真实的心理活动占据了上风——它是一个属于大多数人,甚至有一点平庸的大多数人的故事,现代生活似乎就是由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细节和平凡的情感思绪所构成的——连进入一个单身男人的厨房都可以引发一个女人无限的遐想和令她萌生爱意,就像刘若英在《对面男生的房间》里所唱的那样。
泰勒对女主角凯特感情世界描写的细腻,有一种爱丽丝·门罗的格调,从400年前那个描写并不算细腻的悍妇角色抽离。凯特显然是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女性,虽囿于家庭角色(母亲去世,自己未读完大学,照顾着父亲和妹妹),但又有不谙世事的直率和从不讨好别人的自我,这种“不讨好”大概就是现代的“悍”。阅读的人会禁不住一直追问,凯特的际遇和《驯悍记》里的女主人翁相比,真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了吗?依旧是一个似乎难以遇到合适恋爱对象的女孩(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再不结婚就被爱情毁了”似乎成了她的标签),一段父亲出于功利目的而安排的婚姻(想让自己不受重视的小实验室里有才华的研究人员靠婚姻获得长期签证),不想取悦任何人的、男孩子气的凯特虽然内心对这段被安排的关系有所不屑,但又无奈着、半顺从半抗拒着,依然准备好从对方身上发现令自己感动的东西,直到这人为“制造”的关系变成了“日久生情”。仅仅因为没有选择,她便可以爱上一个相当不错对她也有意思(但交往的目的性很明确)的男人吗?当凯特在约定的成婚之日在教堂等待“父亲之命”的婚礼开始时,她忐忑,没有明确反抗,但又充满不确定感,随着时间推移,新郎始终未出现,她的忐忑变成了另一种忐忑,慢慢转化成对新郎为何不准时来、还来不来的担心,到了新郎一边处理着实验室的失窃案一边十万火急出现的时候,他拉住她举行婚礼反而成了一件让她有点温暖的事。凯特所生活其中的社会心态也并非全然不歧视女性,看看凯特幼儿园的同事们得知她订婚时,那种不得不重视她的态度转变就知道了。
或许,泰勒本就是想从这样一种“被安排”、“有目的”、似乎不可能是真爱的场景出发,去描写一段现代人的情感吧。这在莎士比亚那里很容易自圆其说,女性本就没有太多的自由选择权,能撞上一个和自己情投意合的如意郎君全靠被动的运气;但这种场景放在当下,要自圆其说的难度就高了,现代人的爱情发生学早就把“自由”作为了“恋爱”的定语。《今日美国》如此评论泰勒的改写作品,“关于婚姻,她坦承完全幸福的结局并不存在,现实往往有酸有甜,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彼此磨合,努力走下去”。但我觉得这并非泰勒所要解答的关键难题所在。她面对的核心命题也许是:我们既然不相信自然发生的爱情必然能够通向幸福的婚姻,那么对于婚姻的幸福来说,自生自发的爱情(带有“命运安排”意味的邂逅,实质是一种浪漫化的偶然性——时空相交的缘分)还必须是前提吗?对凯特来讲,她幸而遇上了一个“可爱”的结婚对象,起初被强加的关系慢慢舒展成她的自由意志,也许“命运的安排”和“父亲的安排”并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这是一个现代人难解的谜题:我们可以听从看不见的“命运”(偶然性)的安排,但不可能服从于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类的父亲(他人意志)的安排。
《时间之间》:偶然事件
一个现代读者阅读同时代的当代作家改写400年前的经典,感觉如何呢?我最喜欢的作品是珍妮特·温特森改写《冬天的故事》的《时间之间》。它不仅是一个严格对应《冬天的故事》的文本,让与古代人同名的人物恰如其分地在当代复活,而且也将戏剧性的东西弱化成了小说。温特森将莎翁的文本理解为“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的联系”,她也非常细腻地描述了结下仇恨的过去与宽恕的未来,联结过去和未来的纽带是两代人的时间。她巧妙地把莎翁剧作中的王公贵族转化为由金融界人士、演员歌手这类名流所构成的现代上流社会,也巧妙地处理了莎翁原剧中的神化色彩(死去的母亲从雕塑中复活),将它变成一个精神状态的隐喻——塞纳河畔行尸走肉般的神秘疯女人最后光彩照人地复出于演唱会的舞台上。和《女巫的子孙》一样,这是一篇与原著高度重构的改写。但我初次读完,又觉得有一团自己也无法描述的迷雾潜伏在意识里。过了几天,这团迷雾开始呈现自己的轮廓:根本上,这是一个现代人如何会相信“命运”这回事的疑惑;莎士比亚原剧和《时间之间》里的人物命运如此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构成了一种戏剧性,而这似乎不应是现代生活里的东西。现代生活难道不应指向偶然、不确定和结局的开放吗?温特森仍然没有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将莎翁剧中的必然性转化为偶然性。在这本小说里,作为联结过去与未来、让失散的两代人的生活轨迹重新发生交集的关键,是列奥(对应列昂特斯)之女和赛诺(对应波利克赛尼斯)之子的相识并相恋——这是一个作者安排好的前提——但他们身处同一个城市(虚构的新波西米亚),又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交集的概率又有多大呢?在偌大的巴黎,隐居的咪咪(赫美温妮)就一定能够被好友找到,被劝服复出、重返舞台?温特森为《冬天的故事》里那个被特尔斐神谕诅咒而死的儿子安排了现代式的偶然死法——一场机场的车祸;但她未能给原剧所有暗含着命定前提的情节找到足够能说服人的偶然性。endprint
《时间之间》里,温特森借反派角色充满幽默感的对话,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关键、贯穿整个霍加斯经典改写项目的问题:俄狄浦斯情结和整个西方心理学理论与古代的“十字路口”和现代的“环形路”有什么关系?这位幽默反派人士富有哲理地说:“实际上,如果环岛早点儿被发明出来,整部西方文明史就会大不一样。俄狄浦斯走在小路上,迎面来了一辆战车,车上坐着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就是拉伊俄斯王,他坚决不肯给无名小卒让路,俄狄浦斯的脾气不太好,很像早期的民主党人,上了年纪也好、战车也好,他统统不放在眼里,也不肯让路。两帮人就打起来了,结果,俄狄浦斯把老家伙干掉了。这场悲剧发生在一个十字路口,对不对?三条小路指向同一条路。如果我们及时发明出了环岛,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惨案。你先走,我再走,明白吗?”如若这样,西方世界就没有了弗洛伊德,没有了精神分析学界最伟大的理论——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为了逃避弑父的诅咒而出走,后来却还是应验了弑父的命运。然后就是连锁反应——西方思潮中的重要理论,十亿个精神病人,一百万个心理医生和干亲娘的病人,文学理论,还有人对“前辈的影响带来焦虑”的诗论特别感冒。决定整个西方精神史的,不过是一个不经意的偶然:环形路尚未发明。那么,人性真的是永恒的吗?我们的选择和人生,究竟是不变的人性,还是变动不居的时代所造就的?
小说开头用第一人称做了独白,独白者是目睹车祸并捡到弃婴的人(原剧中捡到帕蒂塔的贫穷牧羊人)。60多岁死去的老人的身份(对应于原著中的安提格纳斯),成了一个勾连过去的悬疑线索,直至他在小说中以尚还活着的花园园丁的身份出现在列奥家中。也许作者开始有转换视角讲述《冬天的故事》的企图,把原剧中并不重要的两个平民人物放在更加中心的地位,让他们的形象更加丰满;但这种企图随着写作的进展被抛弃掉了,插叙之后,第一人称消失了,又都回到了第三人称,依旧是以列奥和赛诺为中心。
如果不是因为《冬天的故事》,《时间之间》毫无疑问将会是一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现代悲剧——在古代的帝王贵族那里,不过是宫斗生活的日常,不算稀罕,发生在普通家庭里,却有一种不能承受之重的感觉。但温特森成功地给这场现代悲剧罩上了一层梦境色彩,让它与《冬天的故事》一样,成为一个有些温暖的故事。她用一種独特的语言风格,营造出一种模糊的效果,断裂、不完整的短句就像印象画派的斑点式笔触,拼凑出并不特别清晰的轮廓。比如这句:“帕蒂塔怔怔地站着,看着那些冷火般晶莹闪光的尤物——地球的结晶。堆积的时间。钻石。”这样的句式不断出现,成了一种独特的消解线条凌厉之感的笔法,淡化了命运的悲怆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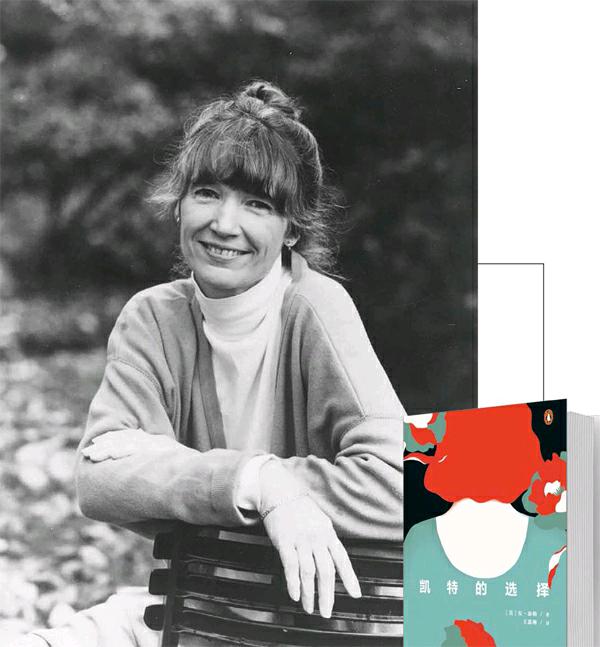
我很喜欢书中的这段话:“我们无从得知旁人的生活。除了我们能够掌控的琐事之外,我们也无从得知自己的生活。永远改变我们的事情总是会发生,哪怕我们无从得知它们即将发生。看似一如往常的时刻,却会是心碎或圆梦的时刻。时间如此坚定又稳当地疾驰,却是狂野疾驰在所有钟表刻度之外。改变一生只需那么一点点时间,领悟那改变却要耗费一生。”也许,生活本身虽是一系列偶然事件,但隔着一段距离去看,却又有着某种模式,就像从飞机上看到的田野、河流和房屋井井有条,但在地面上它们只是混乱与丑陋——如果你还相信有“命运”这回事的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