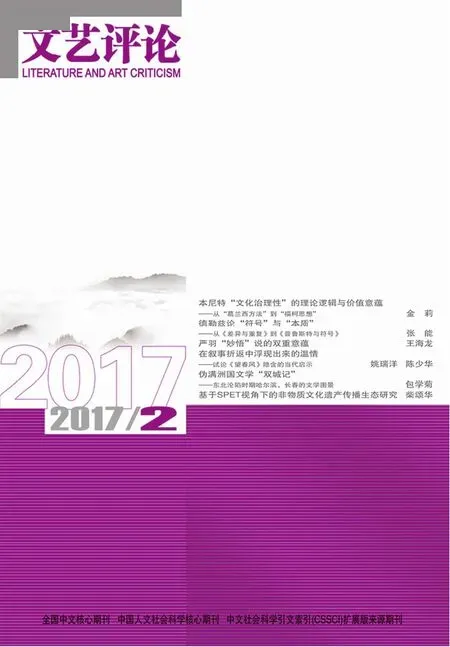魏晋以前的山水文学
○潘杰
魏晋以前的山水文学
○潘杰
在我们的印象中山水文学就是产生于西晋末、东晋时期的谢灵运手中,脱胎于西晋时期的玄言诗,是把山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象和审美意味的文学现象,这种观点起源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的“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①。那么我们需要有疑问了,难道只有把某种审美客体作为独立的文学审美形象,才能把这种文学叫做某某文学吗?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这是存疑的。那么山水作为文学的独立审美形象时才能将之称为山水文学吗?先秦那些描写山水景观的文学作品是否应该也被称为山水文学呢?
在谈及山水文学之前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很长时间。钱谷融说:“文学即人学。”这就是一种很好的解答,文学不正是我们人的情感和审美的表达艺术吗?南宋的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有心则有诗……”②,文学之为文学的存在就是人真性情的文字语言的表达,所以文学的产生是诗人内心的情感体验和感受,甚至我们可以说远古时期那时候的人们没有文字,语言也不健全,他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只好在那里高声“歌唱”甚至手舞足蹈,这其实就是文学的最早起源——诗乐舞都已经出现了,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去考证他们唱的是一些什么了。
那么我们说山水文学的产生是否就应该是山水作为情感之表达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或者是诗人借用山水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呢?在我们还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就暂且把那些文学叫做山水的文学。在上一篇文章中(《中国文人与山水》)我们说到的《礼记·郊特牲》中的一首诗叫《蜡辞》,其中说:“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③这是一首祈愿诗,说土啊你回到原处,水啊你就呆在你的沟里,昆虫啊不要来吃我的庄稼,野草丛木回到你的山野不要来祸害我的田地。诗中有山有水还有草木昆虫,应该也是山水的文学了,这其中的山水草虫虽然没有用来表达诗人的个人情感和审美意向,但是祈愿本身也是一种心理活动,是诗人主观的情感,并且在那种生存都还没有解决的时代,他们的审美情趣自然是停留在功用的、神的、生存的层面了。所以说这首诗完全是符合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审美意识和心理的,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不自觉的对山水文学的亦步亦趋的探索。这应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山水文学。
到了商周以后,尤其是周朝进入了农业社会,生存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他们对于山水的审美意趣不再像先前那样对待神一样的敬畏,山水开始成为人们笔下口中的个人情感审美意象。《诗经》是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诗经》当中有大量的上至风雨雷电水,下讫花鸟鱼虫草木兽的自然景观的描写,其中就表现出大量的诗人对山水的审美意趣。《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洪水芒芒……”,《大雅·韩奕》:“梁山奕奕……”,还有《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溱与洧,浏其清矣……”④,还有很多像《周南·关雎》《桃夭》《邶风·凯风》等等这样的例子,这难道不能够证明我们的先民对山水有一定的审美水平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诗歌中的山水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山水自然的景物是被后世学者称为“比兴”手法的形式存在的,而不是独立的山水审美意象和审美情趣。确实,此时的山水在文学中的存在还处于一种简单的山水描写,审美情趣也止步于山水景观的本身客观形象。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刚刚才从同天地、生存的搏斗中走出来,他们对山水的审美心理也刚刚从像对神一样的敬畏中走出来,纵然此时的山水描写还很简单,但无不表达了诗人观景时的主观感受。而且在《诗经》中已经可以看出此时的诗人对山水的描写有自觉的倾向了,这种山水的倾向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山水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如果说《诗经》中的山水审美还很幼稚,那时隔三百来年后的楚辞中的山水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相比于《诗经》,楚辞里的山水形象更加丰富,辞藻更加华丽,尤其是景物形象开始有了它自身的审美意义。并且在《诗经》审美意识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与自然的亲和和热爱,山水审美从山水的自然景观本身上升到了山水的精神审美上来,诗歌的艺术境界大大提高了。如《楚辞·九歌·湘夫人》当中的山水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⑤这其中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就是寓情于景,“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诗人开篇用洞庭山水之景象极力地营造了一种秋风萧瑟、凄凉哀婉的情境,光从这四句来看,不可不说山水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形象,只可惜这并不只是全诗的主旨意义,以至于后世学者并不把它当作山水诗来解读。诗歌后面在开头营造的气氛之下又表达了凄婉哀怨的爱情,“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我所约会的佳人还没有来,只得看着潺潺的流水永远不停歇地往天边流去。诗歌表达情感并不是直接高呼:女孩啊你还没来,我很焦急啊我很伤心。而是借用景物来表达自己的愁思,这种借景抒情的含蓄表达方法正是后世的中国文人所追求的。写景、有情甚至上升到了境的层次,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它当作山水文学来看呢?
先秦文学当中的山水已经从先民的劳动的“哼唷”发展到了楚辞的情境的审美层面,只是因为这些诗歌多多少少带了些功用,不是单纯地抒发自己的山水情怀而被排除在山水诗之外。事实上从中国古代对文学的认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来看,这些描写山水,用山水来表达情感或者山水景物引发了他们的情感而创作的以山水为艺术形象的诗歌,实在是应该称之为山水诗。
当然先秦时期的文学范式应该是只有诗和文两种,文也就是散文。先秦散文里面的山水景物描写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在《山海经》《庄子》这一类著作中,几乎每篇都有或多或少的景物描写,可惜在这一些作品当中山水景物大多并非是用来表达情感的。《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地理地质景观的描写,但是这些景物只是作者意念当中的客观描写,并非用来抒情或者是山水审美的。只有在《庄子》这一类诸子说理散文中或许还有一些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山水景物描写,庄子意图用游赏山水的方式来表达虚静的审美意识和超功利的山水自然观念,但是这种借用山水来表达哲学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功利做法。这段时间内的诸子山水哲理散文大多都是这样,因此先秦散文中的山水发展并没有诗歌的山水审美发展的那样健全。但是哲理思想作为一种自主意识也可以看作是作者自主的情感,由此山水哲理散文中借助山水自然表达哲理思想也可以看作是抒情的一种,只是这种情感是理性的罢了。所以这段时间内包括《庄子》这样的借助山水来表达哲思的散文依然可以视之为山水文学。
上面是先秦的山水文学,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汉魏时期的山水文学。为什么不谈秦朝呢?首先秦朝国祚很短,而且对文化的管制极为严重,文学和思想在这个朝代灭绝了,只有李斯《谏逐客书》这样的政论文。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文学很难有所发展,更不要说山水文学这种思想情感审美很强的文学形式了。汉魏的山水文学我们也侧重于谈山水散文,这主要是因为山水诗歌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依然是借助山水抒怀抒情,表达思想或者是用于“比兴”的。作为代表的是曹操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⑥全篇除了最后一句是直接抒怀的,其他皆是借用山水来表达自己情感和志向的,这样的创作就像《湘夫人》那样,把山水意象发挥到了极致。这一类的山水诗歌在这一时期经常见到。像汉代不知名的诗人写的《长歌行》用山水文学作“比兴”、刘彻的《秋风辞》《明月皎夜光》充分地发挥了楚辞的借景抒情的风格等。总体而言诗歌在山水领域的发展还是在依循旧路。
和诗歌的停步不前相比,汉魏时期的文在山水上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主要是赋体的景物铺叙的发展,把诗歌中的山水描写方法运用到文章当中,而且还一反《诗经》比兴和楚辞抒情之方法,把原本抽象的景物描写通过景物的铺叙进行细致的形象刻画,还有就是汉代的山水游记的产生与发展是汉代山水文学极为重要的部分。
汉代最主要的文体是赋,汉大赋的恢宏气势和抒情小赋的细腻感人,这是文学审美情趣对汉代大一统社会的集中体现;并且这种韵散结合的创作形式极为适合作家把叙事和抒情结合到一起。《昭明文选》中关于汉赋中山水园林的分类就有六种:“京都”“郊祀”“畋猎”“纪行”“游览”“宫殿”。⑦可见山水园林在汉赋中的重要地位。著名的大文学家班固的《终南山赋》就是一篇以山水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伊彼终南,岿嶻嶙囷。概青宫,触紫辰,嵚崟郁律,萃于霞雰。暖对晻蔼,若鬼若神;傍吐飞濑,上挺修林。玄泉落落,密荫沉沉;荣期绮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气肃清,周览八隅。皇鸾,警乃前;尔其珍怪。碧玉挺其阿,密房溜其巅。翔凤哀鸣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彭祖宅以蝉蜕,安期飨以延年。唯至德之为美,我皇应福以来臻。埽神坛以告诚,荐珍馨以祈仙。嗟兹介福,永钟亿年。⑧这其中对山水文学的创作手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不是像楚辞中那样比较杂乱的使用,而是非常有层次的进行铺叙,文本中的山水描写按照空间分上中傍下四个层次,上有缭绕之云霭,中有出云之青宫,傍有修林与瀑布,下有落泉及密荫。寥寥几句,将终南山之秀丽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山水文学行至此处已经几近成熟。
汉代的另一个重要的山水文学体式是山水游记,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山水游记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侍从官马第伯所写的《封禅仪记》,其中详细记载了汉光武帝东去封禅的准备工作。作为山水游记,《封禅仪记》中关于山水自然景物也有浓墨重彩的描述:“往往道峻峭……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极望无不睹,仰望天阙,如从谷底观搞峰……”⑨,其中对山水景物之描写随着行迹不断的变换,景物之间又不乏连续性。此时的山水游记中只是把景物作为一种单纯的描写对象,以表达景物外在的审美,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审美内涵,或只是为了说明封禅道路之远,行程之艰,以表封禅至诚的。当然这种看山叹其高峻,观水感其清冽的非功利性的审美情感也在这一时期山水文学用来表达各种思想的风潮中带来了一股清流。他的这种非功利性与庄子的非功利性不同,庄子的非功利性实质上是功利性的,而游记中的非功利性就只是用来表达当时情感的,是真正的非功利性。
汉魏时期的山水文学在先秦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一方面他们在审美情趣上开始把山水当成了独立的审美意象,其次是山水文学的创作上也从先秦的简单杂乱的山水描述发展到了把山水有序地描绘出来,以及对景物的描写也更加细腻精致,山水文学自此有了山水画般直观之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文学进一步地发展到完全独立用山水表达情感,并且出现了独立的山水审美意识。
总的来说从先秦到汉魏,山水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形象一直贯穿了文学的发展,山水文学也从原来的用来祭祀的、工具性的、非情感审美的发展至后来的抒情的、意象性的、情感审美的艺术水平。我们通过先秦至汉魏的山水文学作品的品味,找到了山水文学作为思想意识表达了它所在时期的审美意识,把作者当时的社会情感或个人情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不得不说这就是那个时期的山水文学。当然这些山水文学在后世的学者看来是不成熟的,与刘宋时期的谢灵运的山水诗相比较是那样幼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种文学还没有成熟就把它驱除在某种文学之外,就像诗一样,诗的完全成熟是在唐初,那么我们能说隋唐以前的诗歌不是诗吗?这种观点就有些小家子气了。山水文学在这一时期确实尚未成熟,甚至可以说山水自然的审美意识都还未健全,多数作品还依然只是利用山水的工具性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文学创作中的山水都带有浓厚的个人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这足以证明这些关于山水的文学可以称之为山水文学。
或许我们像分类古近体诗那样来给山水文学分类,将山水文学从谢灵运时期作为界限,魏晋二谢之前的山水文学可以称之为古山水文学或者旧山水文学,魏晋二谢以后的称为近山水文学或者新山水文学。再依据这样的划分来对山水文学进行两个方面的研究——山水文学成熟之前的发展和山水文学成熟以后的创作。我们不能因为前辈的学者把谢灵运的诗歌定名于山水诗就忽略了谢灵运以前的文学中的山水,相反我们更应该花大力气去细致地研究,去发现我们祖先的山水审美和山水意识以及他们关于山水创作的深层内涵。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②岳珍《碧鸡漫志校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③朱彬《礼记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8页。
④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94页,第902页,第260页。
⑤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页。
⑥孙明君选注《三曹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页。
⑦刘昆庸《汉赋山林描写的文化心理》[J],《文艺评论》,1996年第5期。
⑧班固《班兰台集》[M],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⑨赵晔《后汉书·祭祀志上》[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52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2-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