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论:重构中国形象的文学新范式
李遇春
复兴论:重构中国形象的文学新范式
李遇春
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牵涉到现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国家形象学。在全球化时代里,一个国家的形象建基于经济硬实力,更关乎文化软实力。通常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形象的建构与重构,是一种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但不能忽视的是,它其实还是一种话语行动,或者说是符号的编码与解码、传播与接受活动。显然,在众多的话语或符号形式中,文学正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其国家形象建构功能的文字符号审美系统。事实上,我们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形象定式的形成,经常离不开我们对特定国家的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与阐释,所以文学经典往往是建构一个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但我们在今天讨论文学与中国的关系,不仅仅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问题,更重要的是还牵涉到近百年來现代中国文学如何通过创制我们时代的文学经典來重构我们的国家形象。
回眸近百年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我们在建构“文学中国”形象的过程中有过成功的经验,但也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缺憾。众所周知,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所以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下被动发生的,我们被迫采用新型的世界观念取代了原有的天下观念,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取代了原有的家国或王朝观念,由此展开了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形象转变。近现代的历史风雨告诉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国家形象转型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掺杂着种种曲折的蜕变、激进的冒险与自我的迷失。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妥善地处理好两种关系:一个是主体性与他者性的关系,再一个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就前者而言,我们在竭力认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形象时,不由自主地丧失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经意间沦落为西方国家文化规训的他者。就后者而言,有时候我们过于强调我们民族国家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同一性,由此压抑乃至放逐了民族国家内部生命个体的差异性,而另一些时候,我们又过于强调我们民族国家内部的生命个体差异性,由此导致文学的碎片化与欲望化,这虽然有利于破除或拆解既有的落后的文学国家形象定式,但终究无法重构我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同一性与整体性。
迄今为止,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主要出现过三种建构中国形象的文学范式,它们分别受制于三种现代中国文学话语体系,由此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建构理念与思维方式。首先是启蒙文学范式,作为中国现代启蒙话语体系的产物,它长期以来一直在支配着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建构,不仅影响深远而且拥趸甚众。这种文学范式主张以西方视界审视中国,此时的中国成为被审视的客体,沦为西方眼中的他者形象,期待着强势的现代西方话语的拯救与重构,而原本应该是他者的西方则一举在中国的现代化浪潮中僭越为高高在上的话语主体,它主宰着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形象转型逻辑与方式,于是现代性崇拜逐渐深入中国人心,并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成为了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神话般的存在。毫无疑问,这种启蒙文学范式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五四启蒙文学运动还是新时期以来的新启蒙文学思潮,都扮演着借助西方话语权柄消解或重估中国既有的主流权力话语的角色,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产生过巨大的历史推动力,也为提升或重构中国的现代或当代形象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毋庸讳言,中国的启蒙文学范式中隐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话语权力等级结构,西主中客或西上中下的思维定式决定了现代中国启蒙作家的价值立场,他们在颠覆近代洋务派中体西用思维定式之后,走向了西体中用的另一极端,甚至是滑入了全盘西化的陷阱。中国新文学的启蒙先驱者鲁迅和胡适等人都未能幸免。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内地风行以来,包括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内的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启蒙文学话语体系加以理性的反思和清算,虽然其中有些言论有过激之嫌,被认为亵渎了五四启蒙先驱的神圣性,抹杀了他们不应抹杀的历史功绩,犯了反历史主义的错误,但不能不承认,这种对五四启蒙文学话语范式的反思和清算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新的话语逻辑与言说方式。值得指出的是,现代中国启蒙文学范式不仅未能解决中国形象建构中的主体性与他者性问题,而且遮蔽了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现代中国启蒙作家过于注重中国走向世界和融入西方的同一性,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特殊的民族性,后者的个性和差异性被无原则地消融到了前者之中,这就是现代中国启蒙文学胜利的代价。
作为中国现代革命话语体系的产物,革命文学范式在新中国形象建构中发挥着巨大功能。中国现代革命话语起源于五四时期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思想的译介与传播,但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和践行下,原本来自西方的现代革命话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并最终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且枝繁叶茂。与之相匹配的是,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范式也经历了一个逐步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文学史进程,从左翼文学到延安解放区文学再到“十七年”文学,现代中国革命文学一直在探寻着属于中国自己的革命文学道路。以土改和合作化小说、革命历史小说、政治抒情诗和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红色中国文学形态各自以其独特的文学体式参与到新中国形象的审美建构之中,翻身解放的工农兵形象一跃成为新中国文学形象的主体,曾经自诩精英的知识分子形象在革命文学话语体系中沦为被改造和规训的对象。这是革命文学范式对启蒙文学范式的历史反拨,也是革命文学范式对启蒙文学范式中隐含的话语等级结构的颠覆,即颠覆了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启蒙霸权,拆解了那种流行一时的西上中下、西主中客、西体中用乃至全盘西化的现代启蒙话语逻辑与思维定势。于是我们看到,在毛泽东时代里,当代中国文学开始走上了一条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道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学样式的学习与改造,革命中国的文学呈现出不同于启蒙中国的另一种文学形态,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在这种革命中国形象的文学话语建构中,中国作家不再以西方视界审视中国,不再把中国当作西方的客体,而是以中国为话语主体审视西方和整个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年的红色文学经典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功能,它向我们展示了新中国文学建构新中国形象的另一种努力。毋庸讳言,这种革命中国的形象建构进程中曾经发生过某些激进的偏差乃至错误,这直接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文学的兴起对激进革命文学话语的清算与反思。但必须正视的是,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转型以来所导致的诸多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的出现,新左翼文学或后革命文学再度回潮,以底层文学的兴起为标志,宣告了新左翼文学与新启蒙文学一样,依然具有强大的中国形塑力量。然而,现代中国革命作家的左翼文学或者新左翼文学,在新中国形象的主体性与同一性建构中,很容易陷入民族国家本位主义,总是或显或隐地忽视了与西方的平等对话机制,在破解西方中心主义圈套的同时,不经意间走向民族自我中心,而缺乏中西对话主体间性的民族国家想象无疑是需要警惕的。
只有在阐明革命论和启蒙论这两种建构中国形象的文学范式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在比较中鉴别复兴论作为一种建构中国形象的文学新范式的特点和价值。其实,现代中国复兴话语的起源由来已久,早在近代民族危机日渐加深加剧之际,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便开始想象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愿景。资产阶级维新派旗手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和《新中国未来记》中所想象的新中国,就是一种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不割断传统的基础上借助西方外力而复兴的现代中国形象。及至五四时期,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在《青春》中呼唤的“青春中国”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一脉相承,都是期待传统中国蜕变为现代中国,仿佛生命返老还童或者病夫经妙手而回春。至于五四新文学主将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更是一则古老中国死而复生的诗歌预言,其中同样隐含着中华民族复兴与重建的理念与逻辑。这种坚守中华民族国家本位的现代复兴话语与那种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为认同中心的中国启蒙话语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前者主张借鉴西方但不丧失民族主体性和同一性,后者在认同西方的过程中往往沦为西方的他者与客体,逐渐失去了中华民族自身的本源与特色。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张在百废待兴的历史语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重塑世界范围内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新形象。但同时期的新中国文学中所建构的新中国形象因为缺少了西方外力资源的借镜而显得孤独而倔强,中华民族虽然站起来了但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重生与复兴。及至新时期以来,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世界语境中进一步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他明确提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要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步,这意味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我们也要实现中国文学的伟大复兴,要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借鉴世界各民族国家的优秀文化资源,坚持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如此才能开创出有别于现代中国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的第三种新型的中国文学形态。同理,我们才能用第三种建基于复兴论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重构我们民族国家新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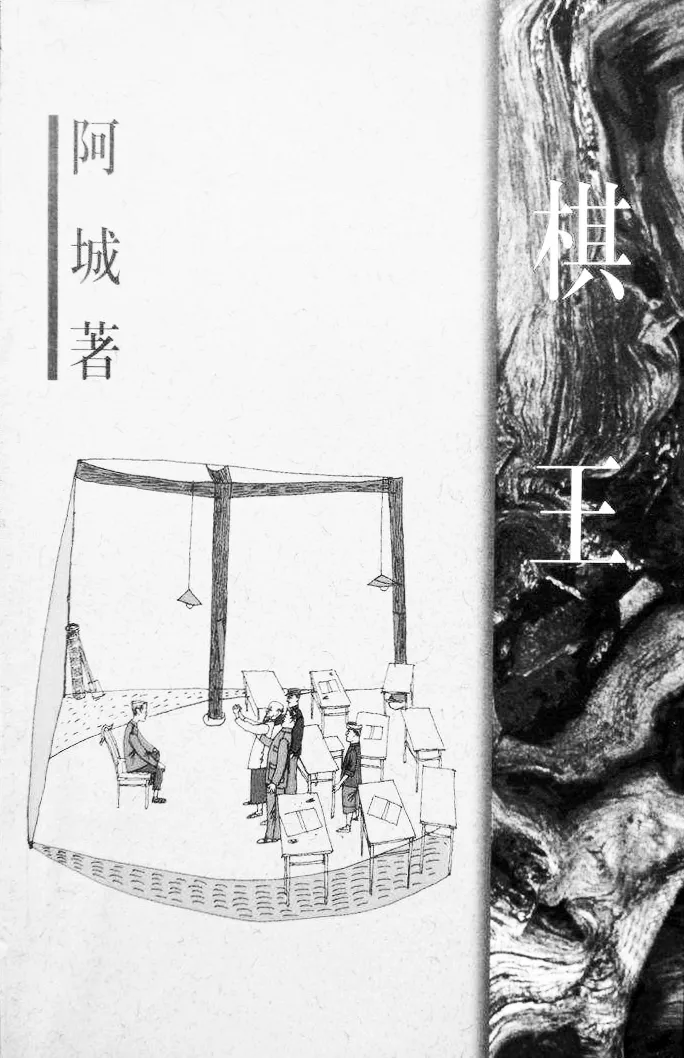
《棋王》
回望新时期之初的中国文学,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历史语境中,文学中国形象也开始一反此前激进的革命姿态而发生转型。最初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伤痕中国”、“反思中国”和“改革中国”、“先锋中国”形象,它们标志着当代启蒙中国形象谱系的重建或重塑。与此同时,另一种中国文学复兴思潮开始崛起,这就是寻根文学的出现,由此开启了“复兴中国”的文学形象帷幕。但在众多的寻根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中,借助西方文化力量批判性地审视中国本土文化劣根性的作品依然占据多数,这类寻根作品中依旧延续着启蒙中国型塑的五四路径,唯有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少数寻根作品在致力于挖掘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传统力量,包括精英文化大传统和民间文化小传统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展开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对话,由此呈现出一个别样的中国形象來。《棋王》让中外读者看到了一个以道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形象的复活,王一生外柔内刚的文化性格彰显了一个有别于西方世界的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象在乱世中的重建。《红高粱》让中外读者看到了中国民间本土野性文化力量的现代崛起,这部作品是关于中国复兴或民族复活的历史文化寓言,不能简单地视为向西方兜售中国落后文化的后殖民主义文本。至于《白鹿原》,它以寻根文学集大成的千钧笔力,更是向世人直接昭示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不死的现代神话。不管政治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也不管欧风美雨如何展开文化侵袭,中华民族必将在历史和文化的阵痛中复活乃至复兴复壮,而一切的牺牲都成了痛苦的代价。如果说鹿子霖最后的疯癫隐喻了中华民族本土儒家功利主义文化的崩溃,那么白嘉轩宁折不弯的脊梁骨则象征着我们民族儒家文化传统中精英德性人格的巨大力量。《白鹿原》的结局固然是苍凉而反讽的,但并不能掩盖作者骨子里的民族文化自信,这当然不是简单的盲目的文化自大,而是建立在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基础上的民族文化自信或曰自性的重建。

《带灯》
自性是自信的源泉,无自性即无自我,也就谈不上自信。正如陈忠实先生生前接受我的访谈时所说,他相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决不是一个“豆腐渣”工程 。我们民族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文化不亡,就是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系统中包含着优秀的文化因子或精华。历朝历代,凡是政权更迭或者民族危难之时,总是有那么一些超拔卓群的豪杰之士站出来担当民族历史前行的重任。近代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从西方文化中盗火,他们希望用西方火种来重新点燃我们民族复兴的理想之灯。即使是鲁迅先生这样经常在批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时不遗余力的五四先驱,他也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片亡国论的绝望情绪中希望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信力。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可见鲁迅先生并没有失去民族的自信力,他一辈子要批判的是“他信力”和“自欺力”。“他信力”就是信他者或者他者性,把民族的未来简单地寄托在外来力量的身上而忽视了激发民族自身的潜能,这就是丧失了主体性的后果。“自欺力” 就是陶醉在民族自身的文化幻觉中而不知道反思和自我批判,由此简单地拒绝援引西方外在文化资源而犯下文化保守主义的错误,这样的民族主体性是虚幻或虚构的主体性,骨子里是自欺欺人。唯有破除“他信力”和“自欺力”,才能在吸收人类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重建我们民族的“自信力”。在当下全球化的时代里,真正的“自信力”必须建立在“公信力”的基础上,而“公信力”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即所谓普世价值。我们需要在普世价值和文化公信力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重估,然后开展创造性转化或现代转换,把那些优秀的民族文化因子转换到新中国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中。比如贾平凹的《带灯》和刘醒龙的《蟠虺》,这两部新世纪长篇小说力作虽然谈不上是寻根文学作品,但两位作家致力于寻找和发掘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文化力量却显示了惊人的一致。贾平凹笔下的乡村女干部带灯,和刘醒龙笔下的知识精英曾本之,他们的青铜人格和带灯人格中均折射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学中复兴中国或中国复兴的艺术标本。这两部作品不仅在文化取向上向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致敬,而且在语言形式和文体风格上均散发出浓郁的中国风味。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当前我们并不缺乏那种将中国人妖魔化或丑陋化的作品,而是缺乏那种在批判中重建的作品,各种苦难大展览和黑镜头集锦并不鲜见,各种人性恶的表演和极端的暴力叙事也随处可见,而我们需要的是在中西文化平等对话中重铸我们民族的灵魂或重镀我们民族的自我。那种单向度的西式批判所导致的文学中单向度的中国人形象谱系需要理性清算,其历史功绩虽然不能简单地否定,但毕竟到了新的文学中国形象学话语转型的时候了。
但通往光明前途的道路也许充满了曲折,我们在展望中国文学复兴与重构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清醒。建立在中国复兴论基础上的新中国形象建构工程必须要吸收启蒙论与革命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要妥善处理好主体性与他者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我们要坚持中西主体间性立场,要时刻保持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对话性。我们不能因为要固守或确保中华民族国家本位立场而忽视或者中断了与世界文明和世界文学的对话,我们也不能为了拆解长期盛行的中西话语权力等级结构而退回狭隘的文化民族保守主义立场。无论以西方中心主义把中国异化成他者或客体,还是以中华文化民族保守主义把西方想象成他者或客体,都违背了中西主体间性哲学基础,都不利于重构新中国形象。只有中西彼此互为主体、平等交流,才能辩证地重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形象。没有他者的主体性是虚妄的主体性,没有差异性的同一性是伪造的同一性,哲学上是如此,文学上亦然。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华民族文学的伟大复兴!

李遇春,1972年生,湖北新洲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入选2009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含旧体诗词)研究。著有《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台湾繁体字版《红色中国文学史论》上、下册)、《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西部作家精神档案》、《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等多部,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选讲》、《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现代中国诗词经典》、《中国现代作家旧体诗丛》、《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丛书》等多种。曾获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湖北省和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表彰奖、湖北文学奖、屈原文艺奖、龙榆生韵文学奖、《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提名等。
——简评《中国法治的范式研究:沟通主义法范式及其实现》(郭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