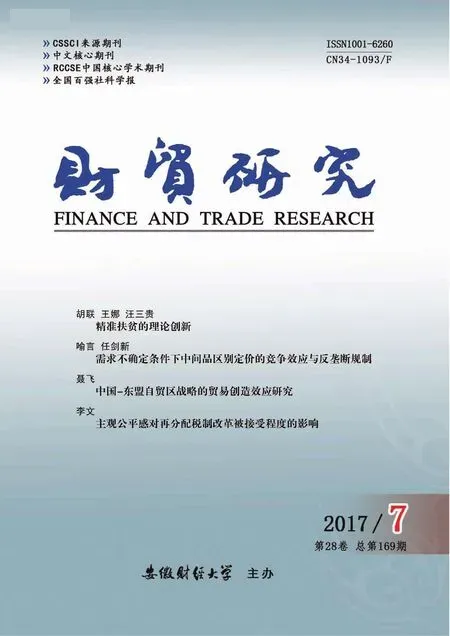政策变动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权衡:政府补助与违规风险规避
姚 圣 周 敏
(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政策变动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权衡:政府补助与违规风险规避
姚 圣 周 敏
(中国矿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以2008年颁布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为研究背景,选择重污染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2006与2009—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信息披露与政府补助以及违规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政府补助、违规风险均显著正相关;《环境信息公开办法》颁布实施后,相较于规避违规风险,企业更愿意为了获得下一期的政府补助而增加环境信息的披露。
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变动;政府补助;违规风险
一、引言
已有研究发现,外部压力会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产生影响,如:Cormier et al.(2005)、陈小林等(2010)均指出,外部压力的存在将促使企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Brown et al.(1998)发现,较高的媒体关注会促使企业进行更高水平的环境信息披露;沈洪涛等(2012)、王霞等(2013)都认为,环保部门的压力会显著影响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和水平;Deegan et al.(1996)的研究表明,当被起诉面临外部压力时,企业会披露更多对自己有利的环境信息以维护自身形象。Darrell et al.(1997)、肖华等(2008)强调,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是管理层对公共压力作出的反应,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持合法性。然而,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合法性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企业管理层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一方面,政府是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推动者,且政府掌握着众多的稀缺资源。企业管理层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很可能会顺应政府的要求而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以获得稀缺资源。在这些稀缺资源中,政府补助是最为直接的,也是政府能够较为灵活分配的一种。另一方面,由于在我国环境信息披露还没有成为常态,大多数企业一般采取比较保守低调的方式来披露环境信息,因为较多的环境信息披露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关注,从而导致后续违规被查处的风险。企业管理层需要在这两方面进行权衡,特别是在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这种权衡表现得更加明显。
2008年5月1日,国家环保总局颁布并实施了我国第一部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的部门法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后文简称《办法》)。《办法》要求企业应按照自愿公开与强制性公开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企业环境信息;同时,要求超标排污严重的企业披露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超总量情况,以及企业环保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等,环保部门有权对企业公布的环境信息进行核查。依照《办法》规定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应当在环保部门公布名单后30日内,在所在地主要媒体上公布其环境信息,并将向社会公开的环境信息报所在地环保部门备案。《办法》的颁布实施加速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明确了环境信息对谁公开、公开方式以及不公开怎么办等等,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由于《办法》的颁布与实施者均为政府,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是选择披露较多环境信息来获得政府资源,还是披露较少环境信息以规避违规风险,是企业管理层面对环境信息披露新政策出台后所需做出的权衡决策。
本文以《办法》颁布实施作为政策变动的主要参照点,选择重污染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2006与2009—201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与政府补助以及违规风险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可能贡献主要体现为:(1)在《办法》颁布实施的背景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对政府补助与违法违规风险的影响,减少了研究的内生性,得出的结论较为客观;(2)拓展了合法性理论,从资源获得与风险规避的角度考察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权衡,丰富了现有理论研究。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环境信息披露
在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方面,田中禾等(2013)发现,企业在境外上市能显著提升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沈洪涛等(2012)的研究表明,媒体对于企业环境表现的报道、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增强舆论监督的作用。毕茜等(2012)的研究证实,制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能显著增加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在披露后果方面,罗党论等(2014)指出,公司环保信息披露情况对于公司IPO融资成本有着明显的约束作用。孟晓俊等(2010)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然而,上述文献并没有从管理者决策的角度深入探讨环境信息披露这一行为。实际上,企业任何的决策都是多方综合考虑的结果,后果与决策是双向作用的。面对诸多可能后果,企业是如何作出环境信息披露决策的呢?本文将重点分析环境信息披露的多目标决策。
(二)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政治与经济的方针和政策,按照特定目的,向企业提供的一种无偿的转移支付,具体包括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和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Shleifer et al.(1994)指出,政府在利用补助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激励着企业与自身一起追求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基于政治方针和政策的考虑,政府补助有维持高就业率的政治动机(Carlsson,1983;Eckaus,2006;王凤翔 等,2006;唐清泉 等,2007);基于经济方针和政策的考虑,政府补助被认为是地方政府“促投资、谋增长”的一种手段(许罡 等,2014)。当然,政府在决定补助对象时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Cull et al., 2005)。在其他条件一定时,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由于信息沟通较为通畅,不仅获得政府补助的可能性更高,而且数量也显著多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Faccio et al.,2006;潘越 等,2009;林润辉 等,2015)。但现有文献鲜有关注环境信息披露与政府补助之间的关系,本文尝试将环境保护纳入政府补助的政治动机中,并将环境信息披露纳入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
(三)违规风险
Yamaguchi(2008)发现,企业的环境违规行为会导致股价下降。Hamilton(1995)的研究表明,企业在TRI报告(环境保护局发布的有毒物质排放报告)中的污染数据越高,媒体对该公司的报道就越多,且在污染数据发布当天股东平均会损失410万美元。Capelle-Blancard et al.(2010)发现,环境事故被披露后的两天内公司股票市场价值平均下跌1.3%。资本市场会给破坏环境的企业带来一定压力,进而激励企业保护环境(Lanoie et al.,1998)。另外,Porter et al.(1995)指出,企业的环境违规行为还将导致销售额降低以及成本增加,原因主要在于环境破坏行为给企业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Mohr et al.(2005)的研究表明,50%以上的消费者是“伦理道德型”的,他们不愿意购买有环境违规行为公司的产品。然而,现有研究很少考察环境信息披露与违规风险的关系。实际上,环境信息披露的最直接问题就在于可能引发潜在违规行为被查处的风险,管理层既希望通过环境信息披露获得一定收益,同时也需要考虑控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以避免潜在的违规诉讼风险。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即环境信息披露与经济后果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2)现有文献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权衡性关注不足。已有研究认为,环境信息披露会导致某一后果是确定的,但实际上,企业管理层在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时需要权衡各种后果,然后做出有利的决策。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信息披露与政府补助
在理性层面,政府与企业是互为彼此的利益相关者,属于声誉共同体的关系(李焰 等,2013)。对政府而言,保护环境是其主要的政治目标。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主体,其能否积极有效地协助政府是维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对企业存有依赖。在过程层面,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相关部门进行环境治理具有重要作用(王霞 等,2013)。在交易层面,政府为了获得企业的支持,会与企业建立联系并向企业投入资源。向企业提供补助是政府建立联系的方法之一,较之过去依赖行政手段干预企业,这实际上是一种进步(王凤翔 等,2006)。从补贴效果来看,政府补贴有助于上市公司社会效益的发挥(唐清泉 等,2007)。因此,本文预期,政府会根据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来决定其是否有资格获得政府补助以及具体的补助金额。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高水平的环境信息披露会给企业带来良好声誉,政府部门可能认为企业是支持其环保政策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因此无论是出于鼓励还是补偿的目的,政府都会增加提供给企业的补助(可能性)。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政府补助正相关。
(二)环境信息披露与违规风险
外部关注是把“双刃剑”,受关注的企业既可能因此成为“明星企业”,也可能受到谴责与惩处。环境信息披露会提高关注者对企业环保行为的敏感度,大多数关注者认为企业应当在经营中采取合法的环保措施。一旦关注者发现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信息低于期望,其会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关注,从而使企业被查处的概率增加。而且,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越多,企业被查处的概率也越大。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违规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三)政府补助、违规风险与环境信息披露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企业的生存都离不开资源,而很多资源企业是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的,因此每个企业都或多或少依赖于外部环境。在政企关系中,政府地位的特殊性使得政府拥有许多企业所需的稀缺资源,政府补助就是其中之一。一方面,政府补助具有质量甄别与信息传递的价值,对于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而言,公众会认为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社会声誉。另一方面,政府补助具有经济补偿价值,能够给企业提供资金用于升级设备、购买环保设施等,有助于进一步支持企业的环境治理。
政府部门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推行者以及监督者,而真正将规定落实到位以实现相关政策目标的是企业,那么政府对企业也具备依赖性,政企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对于想要从政治机制中实现组织利益的企业家来说,弄清政治决策者面临的压力和诉求以及如何将自身利益与政治决策者的需要相联系非常关键(Reitz,1979)。因此,当企业认为政府补助的溢出效应高于违规风险导致的后果时,可能会通过增加环境信息披露来支持政府的政策,进而提升政府对自身的依赖,最终获取政府补助。在《办法》颁布实施前,环境信息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环境信息披露对政府补助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然而,《办法》颁布实施后,环境信息的地位得到有效提升,此时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状况会显著影响政府补助的发放情况。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3a:当政策变动后,相较于规避违规风险,企业更愿意为了获得下一期的政府补助而增加环境信息的披露。
然而,从另一角度思考,政府补助带来的溢出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如:雷鹏等(2015)发现,政府补助虽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对企业的研发综合效率却存在负面影响。周霞(2014)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发现,政府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与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它既可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也可能引发管理者和员工寻租或偷懒等行为,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此外,环境信息披露还会导致违规风险,所以环境信息披露的增加给企业带来的结果是不确定的。Kahneman et al.(2000)将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到经济学领域,并提出了前景理论。该理论认为在面临不确定时,人们对损失和获得具有不同的敏感度,损失时的痛苦感要远超过获得时的幸福感。基于此,本文认为在环境信息披露程度的选择上,企业可能更在意违规行为被发现所造成的后果,如声誉的破坏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违规成本。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3b:当政策变动后,相较于获得政府补助,企业更愿意为了规避下一期的违规风险而减少环境信息的披露。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政策变动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1):
(1)
为了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政府补助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2):
(2)
为了检验环境信息披露对违规风险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3):
(3)
为了检验政府补助(可能性)、违规风险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4):
(4)
模型中所涉及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二)数据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重污染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2006与2009—2011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本文选择《办法》颁布前后三年作为样本期间,但由于政府补助、企业违规违法数据从2005年开始,因此,2004年数据并未放入研究样本。,并进行了以下处理:剔除ST、SST及*ST等被特殊对待的公司;剔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整理筛选后共得2559个有效观测样本。环境信息披露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上市公司年报与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信息相关部分,而年报与社会责任报告均手工收集于巨潮资讯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数据收集于CCER、CSMAR等数据库。
(三)描述性统计
从表2的描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到,EID、EID_sig、EID_amount、EID_time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差距较大,平均数偏低,说明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不稳定且普遍偏低。Subsidy_dum的平均数为0.87,方差为0.11,而Subsidy的方差为28.8,说明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能获得政府补助,但各企业获得的补助金额差距较大。Illegal的平均数为0.12,说明目前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是存在的,但违规企业不多。Change的平均值为0.7,说明样本公司所处的环境公共压力比较大。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政府补助以及违规风险之间的关系,分析企业如何在获得政府补助与规避违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进而披露环境信息的,本文分别对模型(1)、(2)、(3)、(4)进行回归分析。
1.政策变动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表3是对模型(1)回归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政策变动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均为正相关,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办法》颁布后,政府以及公众参与带给企业的压力增加,企业会选择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该结果与沈洪涛等(2012)、王霞等(2013)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3 政策变动与环境信息披露回归结果
(续上表)

EIDEID_sigEID_amountEID_timeGDP-0.089(-1.08)-0.027(-0.38)-0.031(-0.33)-0.026(-0.44)Wage-0.385∗∗∗(-3.42)-0.240∗∗∗(-3.68)-0.366∗∗∗(-3.53)-0.178∗∗∗(-3.58)MB-0.173∗∗∗(-5.24)-0.136∗∗∗(-4.35)-0.167∗∗∗(-5.46)-0.103∗∗∗(-3.77)_cons-9.550∗∗∗(-3.56)-5.274∗∗(-2.25)-8.035∗∗(-2.85)-6.250∗∗(-2.76)N2559255925592559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2.环境信息披露对政府补助的影响
表4是对模型(2)进行回归的结果。从表中可见,环境信息披露各指数与政府补助(可能性)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随着环境信息披露的增加,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数额与可能性都会显著提高。因此,假设1得到证实。

表4 环境信息披露与政府补助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3.环境信息披露对违规风险的影响
表5是对模型(3)进行回归的结果。表5的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各指数与违规风险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会导致违规风险增加。因此,假设2获得支持。

表5 环境信息披露与违规风险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4.政府补助(可能性)、违规风险与环境信息披露
为了验证假设3a与3b,本文将Illegalt和Subsidyt(Subsidy_dumt)一起作为解释变量对模型(4)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中可以看出,Illegalt与EIDt+1、EID_sigt+1、EID_amountt+1和EID_timet+1均为负相关但不显著;Subsidyt(Subsidy_dumt)与EIDt+1、EID_sigt+1、EID_amountt+1和EID_timet+1均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与假设3a一致。这说明,为了降低下一期的违规风险,企业会选择减少环境信息披露;而为了(继续)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会增加环境信息披露。当面对这种矛盾时,企业权衡之后会选择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原因可能在于:尽管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违规风险,但事实上无论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如何,在政策变动较大的环境之下,企业的违规风险永远存在,唯一能够降低风险的办法便是企业真正做到在经营过程中不污染环境、做好环境保护措施。因此,降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相反,通过提高环境信息披露带来政府补助(可能性)的提升则是切切实实的,对于企业而言,充分利用政府补助的溢出效应是正确的选择。

表6 政府补助(可能性)、违规风险与环境信息披露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5.政策变动前后对比
进一步,验证政策变动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选择是否具有影响。本文将全样本分成《办法》颁布前与颁布后两组,《办法》颁布前表示企业和政府面临的政策变动比较小,颁布后则意味政策变动比较大。回归结果如表7、表8所示。其中,表7将Subsidy_dumt和Illegalt作为解释变量,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办法》颁布前,Illegalt和Subsidy_dumt的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办法》颁布后,Subsidy_dumt与EIDt+1、EID_sigt+1、EID_amountt+1均显著正相关,而与EID_timet+1正相关但不显著,该结果与Illegalt正好相反。这说明随着政策变动的增大,企业为增加下一期获得政府补助的可能性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包括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性和披露数量),这与先前的结果一致。表8是将Subsidyt-1和Illegalt-1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办法》颁布后,Subsidyt-1与EID、EID_sig、EID_amount的关系由颁布前的相关但不显著变成了显著正相关,而Illegalt-1的系数一直不显著,说明《办法》颁布后,随着政策变动的增加,企业会为了增加下一期政府补助的金额而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此与之前的检验结果一致。

表7 政府补助可能性、违规风险与环境信息披露滞后一期回归结果(《办法》颁布实施前后对比)
(续上表)

《办法》颁布前EIDt+1EID_sigt+1EID_amountt+1EID_timet+1《办法》颁布后EIDt+1EID_sigt+1EID_amountt+1EID_timet+1ROE2.226∗(1.84)2.072∗∗(2.81)2.413∗∗(1.96)1.360(1.53)-0.216(-0.19)-0.072(-0.09)-0.070(-0.06)-0.481(-0.56)FCF0.599(0.16)0.322(0.29)0.563(0.17)0.187(0.17)1.172(0.75)0.872(0.79)1.835(1.19)1.743(1.45)Growth-0.077(-0.38)-0.050(-0.29)-0.054(-0.23)-0.134(-0.95)-0.224(-1.37)-0.149(-1.30)-0.229(-1.43)-0.074(-0.59)Size0.249(0.96)0.135(1.05)0.203(1.01)0.220(2.08)0.856∗∗∗(5.42)0.514∗∗∗(4.65)0.781∗∗∗(5.06)0.463∗∗∗(3.84)LEV1.449(1.25)1.231∗(1.91)1.595(1.60)0.938∗(1.84)4.328∗∗∗(5.57)2.869∗∗∗(5.26)3.828∗∗∗(5.04)2.563∗∗∗(4.31)Herfi50.965(0.55)0.642(0.49)0.811(0.56)0.608(0.74)0.288(0.27)-0.655(-0.86)-1.031(-0.98)-1.681∗(-2.03)Big4-0.539(-0.50)-0.622(-0.86)-0.611(-0.64)-0.264(-0.51)-1.825∗∗∗(-3.29)-1.273∗∗∗(-3.27)-2.012∗∗∗(-3.71)-1.035∗∗(-2.44)Independent-0.294(-1.34)-0.239∗∗(-2.36)-0.345∗∗(-2.27)-0.030(-0.27)-0.057(-0.38)-0.075(-0.72)-0.088(-0.61)-0.021(-0.19)Market0.039(0.49)0.033(0.96)0.051(0.61)0.019(0.69)0.009(0.15)0.042(0.99)0.045(0.76)0.062(1.32)_cons-3.001(-0.57)-1.320(-0.45)-2.154(-0.47)-3.857(-1.41)-16.330∗∗∗(-5.00)-9.323∗∗∗(-4.07)-14.68∗∗∗(-4.59)-7.731∗∗∗(-3.09)N301301301301858858858858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表8 政府补助、违规风险与环境信息披露滞后一期回归结果(《办法》颁布实施前后对比)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办法》的颁布为研究背景,选取重污染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管理者决策视角分析了企业处于政策变动背景下是如何在获得政府补助与规避违规风险之间进行选择的,从而确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披露质量的问题。结果表明:(1)政策变动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同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越高,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大,且违规被查处的概率越大;(2)从企业管理层披露动机上看,当政策变动后,相较于规避违规风险,企业更愿意为了获得下一期的政府补助而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因此,本文研究了在外部政策变动背景下,管理层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真实动机。来自于外部政策变动所产生的压力并不是管理层的全部动机,管理层在披露决策过程中会在政府补助与避免被规制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在政府大力倡导环保的背景下,管理层倾向于披露更多且更有质量的环境信息以获得政府补助。
为了规范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环境信息违规披露的处罚力度。在独立第三方进行审计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环境信息定期审核的机制,查处环境信息违规披露行为,并予以重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补助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遏制政府补助的负向作用。因此,需规范政府补助的发放行为,提高透明度,加大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力度,积极引导管理层披露环境信息的行为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毕茜,彭珏,左永彦. 2012.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和环境信息披露[J]. 会计研究(7):39-47.
陈小林,罗飞,袁德利. 2010. 公共压力、社会信任与环保信息披露质量[J]. 当代财经(8):111-121.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 2011.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雷鹏,梁彤缨,陈修德,等. 2015.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研究[J]. 软科学(3):38-42.
李焰,王琳. 2013. 媒体监督、声誉共同体与投资者保护[J]. 管理世界(11):130-143.
林润辉,谢宗晓,李娅,等. 2015. 政治关联、政府补助与环境信息披露:资源依赖理论视角[J]. 公共管理学报(2):30-41.
罗党论,王碧彤. 2014. 环保信息披露与IPO融资成本[J]. 南方经济(8):13-26.
孟晓俊,肖作平,曲佳莉. 2010.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互动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一个分析框架[J]. 会计研究(9):25-29.
潘越,戴亦一,李财喜. 2009. 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5):6-17.
沈洪涛,程辉,袁子琪. 2010.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年报还是独立报告[J].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6):5-12.
沈洪涛,冯杰. 2012. 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J]. 会计研究(2):72-78.
唐清泉,罗党论. 2007. 政府补贴动机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6):149-163.
田中禾,郭丽红. 2013.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J]. 求索(9):26-28.
王凤翔,陈柳钦. 2006. 地方政府为本地竞争性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的理性思考[J]. 经济研究参考(33):18-23.
王霞,徐晓东,王宸. 2013. 公共压力、社会声誉、内部治理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2):82-91.
王小鲁,樊纲,李飞跃. 2012. 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1年报告[M]. 北京:中信出版社.
肖华,张国清. 2008. 公共压力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基于“松花江事件”的经验研究[J]. 会计研究(5):15-22.
许罡,朱卫东,孙慧倩. 2014. 政府补助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视角的检验[J]. 经济学动态(6):87-95.
周霞. 2014. 我国上市公司的政府补助绩效评价: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J]. 当代财经(2):40-49.
BROWN N, DEEGAN C. 1998. The public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formation—a dual test of media agenda setting theory and legitimacy theory [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29(1):21-41.
CAPELLE-BLANCARD G, LAGUNA M A. 2010. How does the stock market respond to chemical disaster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59(2):192-205.
CARLSSON B. 1983. Industrial subsidies in Sweden: macro-economic effects an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 .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32(1):1-23.
CORMIER D, MAGNAN M, VAN VELTHOVEN B. 2005.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quality in large German companies: economic incentives, public pressures or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14(1):3-40.
CULL R, XU L C. 2005. Institutions, ownership, and finance: the determinants of profit reinvestment among Chinese firm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7(1):117-146.
DARRELL W, SCHWARTZ B N. 1997.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and public policy pressur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6(2):125-154.
DEEGAN C, RANKIN M. 1996. Do Australian companies report environmental news objectively?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by firms prosecuted successfully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uthority [J].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Accountability Journal, 9(2):52-69.
ECKAUS R S. 2006. China′s exports, subsidies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WTO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7(1):1-13.
FACCIO M, MASULIS R W, MCCONNELL J. 2006.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1(6):2597-2635.
HAMILTON J T. 1995. Pollution as news: media and stock market reactions to the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data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8(1):98-113.
KAHNEMAN D, TVERSKY A. 2000.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OIE P, LAPLANTE B, ROY M. 1998. Can capital markets create incentives for pollution control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6(1): 31-41.
MOHR L A, WEBB D J. 2005.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ice on consumer responses [J]. 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39(1):121-147.
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 1995.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4):97-118.
REITZ H J. 1979.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2):309-310.
SHLEIFER A, VISHNY R W. 1994. Politicians and firm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4):995-1025.
YAMAGUCHI K. 2008. Reexamination of stock price reaction to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 GARCH application [J]. Ecological Economics, 68(1):345-352.
(责任编辑 张建军)
DisclosureofEnvironmentalInformationunderPolicyChange:ATrade-offbetweenGovernmentSubsidiesandRisksofViolations
YAO Sheng ZHOU Min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Selecting th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Rules in 2008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with data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in environmental sensitive industries over a 5-year period (2005-2006 and 2009-2011),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risks of violations.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risks of violations. After th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Rules is implemented, compared to avoiding the risks of violations, firms prefer to disclose mor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to obtain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olicy change; government subsidy; risks of violations
2016-09-12
姚 圣(1978--),男,江苏徐州人,博士,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周 敏(1991--),女,江苏南通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空间距离、同业模仿与环境信息披露机会主义行为:动因、实现路径与经济后果”(7157218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关联、地方利益与环境业绩——基于生存权保障的研究视角”(71102163)。
F23;F271
:A
:1001-6260(2017)07-0099-12
10.19337/j.cnki.34-1093/f.2017.07.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