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焰
■龙巧玲
夜焰
■龙巧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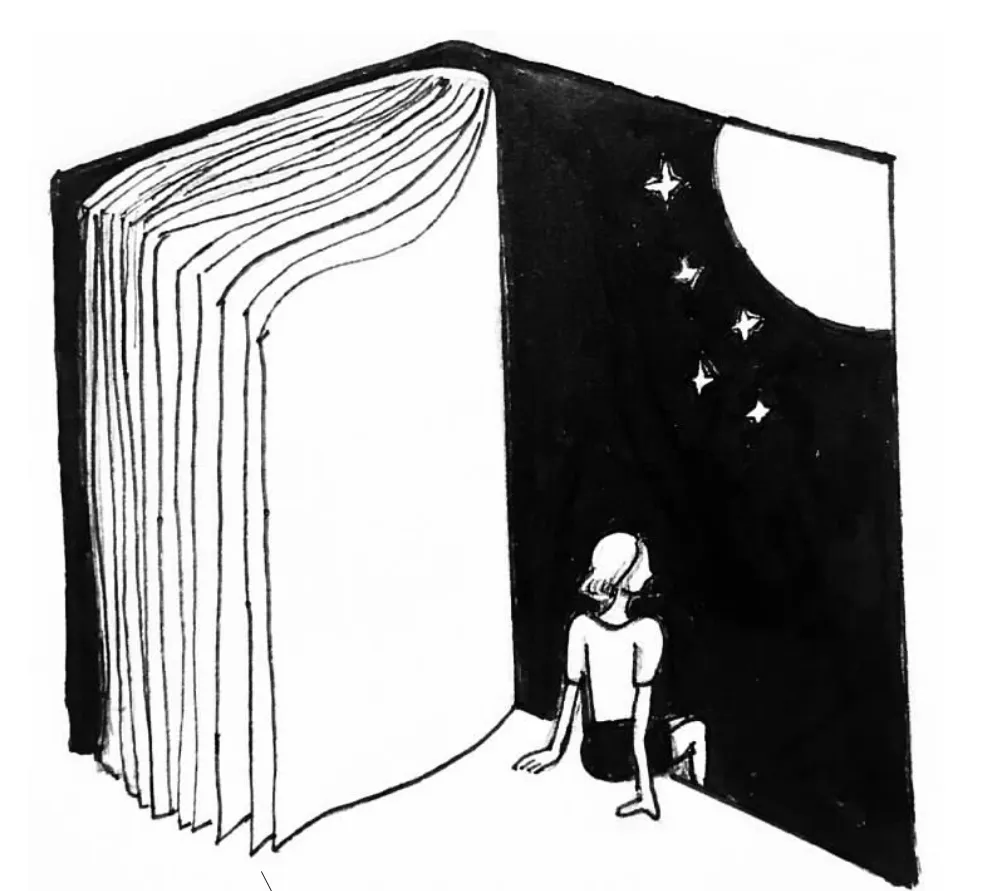
新买的刀,老板说这是最好的刀,锋利无比。一直没用,今天派上用场,早早把肉馅儿剁了,明天大年三十,包饺子就不慌张了,胡云大年三十要值夜班。很多人家肉馅儿是机器绞的,方便。胡云自己剁,手剁的肉馅儿香,她一个人吃,剁不了多少。一个人的年,她要好好过。才褪了猪皮,切成块,手指擦着刀刃,一股血飞出来,染红了肉和砧板。哎哟!疼牵着心尖,心莫名其妙地翻腾了一下。新刀是要吃血的,吃了血才肯认主人。胡云按着伤口,血滋滋冒,伤口不大,深,一团卫生纸很快浸透,还止不住。指根缠了皮筋,用劲压了一会儿,血才止住,用胶布缠了,戴一只塑料薄膜手套,刚要进厨房,大门敲响了。
天都黑了,谁会在这个时候敲门?她走到门口问:“谁呀?”
“开门。”
胡云一听就知道是谁。
“不开。”拉了拉门把手,确信上了锁。
又一个声音说:“嫂子,开门。”
她也来了?胡云知道怎么回事了。把里层的门也关了,上了锁。
门外持续不停地敲门,喊门。胡云还听出了几个声音,都是他家的。
“敲去。我不开,你们能怎样?”她心里说。回到厨房继续剁肉。刀咚咚响,心也咚咚跳。原来方才心里的那一翻腾,才是这事。迟早都要来的,只是没她预料的快,也没预料是今晚。要过年了呀!
剁肉。只有剁肉能集中她的心绪,刀刃是要吃血的,刚才虽然吃了,如果她再不小心,还是要被它咬着。
她不担心外面的人破门而入,防盗门还是很结实,锁是才换了不久的,她心里想的是另一个问题:谁把她的住处告诉他们的?昨天她还把鸡、鱼、羊肉,给了他,让他去他弟弟家和他母亲一起过年。一来是觉得他孤单;二是让他不要再给远在外地的儿子施加压力,逼迫回家。他答应得好好的,不再强求儿子回来,也不要求她回去。答应了又怎么会突然找上门来?她的住处如果不是有人详细告诉他,他们绝对找不到这里来。父亲来过好几次,前天来都走错了,找不到楼,进错了单元,敲错了门。父母亲第一次来,在小区里转悠了两小时没找到,还是她出去接他们来的。生人怎么能这么顺当找来?如果是跟踪,他早找着她了,还能等到今天?
敲门声持续不断,喊叫声也持续不断。这叫四邻听见,不知怎么说她!一层楼住着四户人家,窗户都开在走廊里,什么都瞒不住。隔壁男人冬天喝醉了酒,在她门口唱歌、敲门,搅扰得她一夜不敢入睡。今晚这样,叫邻居必以为她是另类的人,要拿怎样的眼光审视她?
敲吧!敲吧!门不开,总有走的时候,不累你们就敲一夜。
别人离婚,几天就处理得干净利落。胡云离婚,十年了,还纠缠不清。十年前虽然办了离婚,因为儿子小,顾虑儿子的成长,前夫又提了要求,不让她搬出去,便又过在一起。转眼十年,儿子上大学走了,生活的磨合,并没有改变彼此的心性。在众人一致赞美他们眼里的完美家庭的时候,胡云又坚持了一年,终于,在前夫又一次半夜醉酒的羞辱和暴力中离开了家。
那天晚上,她从前夫的拳脚下逃脱,穿着撕破的短袖睡衣、拖鞋,在中秋夜12点的楼道里瑟瑟发抖。她怕前夫抓她回去,又跑到院子里,夜黑,寒凉,如铁般冷硬,她犹豫了半天,去了另一单元的朋友家,借住了一晚。天刚亮她就回去,怕大院里人看见。敲门,门开了,前夫的背影走向卧室继续睡觉,看也没看她一眼,也不问她一晚去了哪里。她早习惯了这些。收拾了简单的东西,走出家门,再也没回去。前十年为了儿子委屈着自己,现在儿子大了,她不想再委屈自己,想要自己的生活,安全、安静,即使孤独,也是没有暴力与羞辱的孤独。她愿意。女人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活着?她不争,也不吵,房子、财产,她都不要,她要儿子,儿子是她的命。
半小时过去了,门外传来嚷嚷声,是胡云父母亲的声音。喊她的名字,叫门,敲门。胡云心里一喜,毕竟是亲骨肉,知道她身处险境,来给她解围了。来得真是太及时了!父母亲敲门,定是做做样子,胡云不开门,父母亲就会劝他们回去,胡云的危机便解除了。胡云长长出一口气,半个紧张放下来。还是父母亲好,虽然嘴上说不同意她离婚,反复劝她回家去,到了关键时刻,还是向着她嘛!
她想多了!除了父母渐渐增高的责骂声和逼债催命般的敲门,还有兄弟和弟媳的高叫声。他们也来了?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来的?莫非?他们是串通好了,一起来的?好!他们终于联合起来了。胡云手一抖,刀刃又舔了她的指头,血放出笼子似的喷出来,兜在薄膜手套里。她包扎了伤口,继续剁肉。现在除了剁肉,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防盗门被打开了。父亲有她家的一把钥匙,但是没有里面的门钥匙。防盗门打开,把声音和暴怒放大,叫骂声和砸门声,就像刀刃舔血,犁进她的心。
“你就打算这样?从此也不上娘家门?”母亲高八度的嗓门。
她想起那日姨妈到母亲家,看见胡云问:“云儿怎么老在这里吃饭?你来了,栾雨咋吃哩?”
母亲剜了她一眼说:“都是有家的人了,还叫我伺候。”
胡云中午下班去母亲家吃饭,她住的地方离单位远,到家还来不及做饭吃,上班时间就到了。这才吃了个把月,母亲这样说,让她的脸像泼上了烧碱。
姨妈走后,她对母亲说:“以后中午我不来了。”
母亲有些讪讪:“那,你去哪里?”
“回家。”
“回哪里的家?”
“我自己的家。”
“好好的家不回,你四处漂流?叫我在人面前张不开嘴!给亲戚们怎么交代?今天立马搬回去。”母亲高八度的嗓音,满屋子飞,在四壁撞来撞去,不肯熄落。
“我不回去。别人单身也过得好好的,我为什么不能自己过?”
“别人是别人,你必须回去。”
“我就当守寡了。”
母亲抬手给她一记耳光。
她哭着说:“我回去就是个死。”
母亲狠狠说:“你死就死,死也得回栾家去死。”
那以后,她再没去母亲家吃午饭,父母亲喊了几次,她借口推托了。转眼到了年关,母亲老打电话来,问她儿子咋还不回家?后来母亲给胡云的儿子打电话,说他父母分居了,出了大事。父亲也发信息给她儿子,让他赶紧回来处理他父母的事。父母亲的心思,就是逼她回家。她把原委告诉了儿子,没让儿子回来。所有的疼她情愿自己承受,也不让儿子担。
胡云抹了一把眼泪。好希望父母能放弃敲门,劝前夫家的人回去。但已容不得她那么想了。
“咚咚”,是脚踹门。门后吸盘上的小滚刷掉下来,窗框也嗡嗡颤叫,屋顶的吊灯似乎也晃动着,要坠下来,大厦将倾般。胡云扔了刀,去开门。打开的瞬间她后悔扔了刀,提着刀才对。谁要进来一步,她就让这刀刃舔谁的脖子。
黑压压一堆人。打头的是她弟弟。
“谁把我住处告诉他们的?”胡云问抢进门的弟弟。
弟弟瞪着眼睛说:“咋了?你的门,不能让人进吗?”
人就涌进门。她看也没看,转身进了厨房,抄着刀继续剁肉。握着刀,她什么也不怕了。谁敢动她,她就让刀把她的血和肉吃个够。哪怕是命!
母亲忙着招呼前夫家的人落座,说:“你们咋今天才来?”前夫家的人不知所云地应答。
父亲和弟弟、弟媳高声叫骂,一把把刀飞进她的心,剁馅儿般刀起刀落。
“你这个伤风败兴的,我老胡家还没出来一个,你是头一个,丢尽了我们胡家的脸。”
“你还是个文人?丢人!爹妈来了都不给开门,亲戚上你的门不给开门,你多贵重?”
“地方是我说给的,咋了?干啥?你把我干啥?你多贵气的住处,不能叫人知道?藏藏掖掖的,躲到什么时候?!”
早该想到是她。当初说得多好!“离就离了,你回娘家来,我们照顾你,我们三个互相照顾。”还要胡云住在娘家。把胡云感动的,十几年了弟媳妇第一次说出这么感动人的话,再也不怕出嫁的姑娘将来分家产了。这才几个月,就又变回去了。幸亏她租了房,没有在娘家住。
“要不是老爹踹那两脚,看来我们今天别想进你的门?你这有啥见不得人?”
好像在他们进来之前,胡云是偷了男人的,杀人越货的,放火吸毒的!
一个个,凭什么来责难她?她搬到这里时,白天上班,晚上收拾屋子,没有床铺,她在沙发上将就了半个月。每一寸灰,每一颗螺丝,都是自己动手。抽油烟机洗干净后抱不上去,掉下来砸碎了橱柜门板,差点砸折了她的脚。她有恐高症,硬着头皮擦窗户。一天吃一顿饭,遇到休息日,前一天买一张大饼,一瓶矿泉水,当一天的饭食。埋头干活,苦累就着眼泪吞。什么难都过了,什么苦都吃了。那时的你们在哪里?家用的一切她都要买,谁给她添了一根筷子?现在,都理直气壮来指责她的不是!她这个家好像是违法建筑!
弟媳尖酸的声音,挂在厨房门上,人已进来。前夫家的两个弟媳妇也跟进来,凑到胡云身边,拉扯她。
胡云喝:“出去。”刀举到左手臂上,剁下去的架势。
老二媳妇说:“嫂子,放下刀,出去说。”上前要夺刀。
胡云抬起刀朝左手臂剁,老二媳妇唬地跳出厨房。老三媳妇也不敢进来,只凑到门口,探进半个头。
弟媳凑上,伸出胳膊说:“来,给你剁”。
胡云想说:“脏了我的刀。”忍住了。手肘用劲撞了她一下,什么也没说。她倒识趣,出去了。
客厅里骂声不绝。前夫家的人一句话也不说。胡云只管剁肉,不出去,也不说话。话让他们说尽了。娘家人现在要和她断绝关系,在前夫家的人面前,撇清了他们的干系。
“就当胡家门里没她,就当我们没养这个人,以后我们也不认她。走,我们走。”弟弟绝决地说。“处理过多少事情,没见过你这样的!这是啥态度?不管了,我们走!”
弟媳跟着喊:“走,老爹老妈,我们走,不认了!”
母亲声音软塌塌朝厨房伸进来:“云儿,我们走了。”
胡云的眼泪涌上来,放下刀出来,也不抬头,从冰箱拿出两袋真空包装好的羊肉递到母亲手里,想说,已说不出话,大滴的眼泪落在袋子上。
弟弟绝决地说:“不要。都买了……不要拿!”
母亲的手犹豫着还给胡云,胡云眼泪掉到母亲手上,甩身进了厨房。听他们出门,和前夫家的人道别。心里却想,母亲是不是把那羊肉放下了?真的不要?和她断绝情分?
防盗门“嘭”地关上,像一刀切断了胡云的前世和今生,切断了她的根。巨响把他们也推出了她的心。她心里比山还重的亲人啊!西北风刮过般,走得干干净净。原来她只是娘家树上的枝杈,丢掉她,就像丢掉一片落叶。女人的宿命大抵如此!她曾幻想靠着大树歇脚的念想,如今连根拔除。几十年苦心委屈自己的孝顺呢?原来是亲人惯以掣肘的手段。他们都是被她惯坏了,只要她屈从,不惜胁迫的屈从。
胡云不停剁肉,肉已成泥。刀划伤的地方,又裂开来,血滴滴答答,和肉泥,和眼泪混搅在一起。眼睛模糊不清,刀刃再一次咬了她的手指。她举着手指,看着血涌出来,像从悬崖爬上来的藤,疯长着爬上她的手掌,竟丝毫不觉得疼。看到灶台上一颗洋葱。洋葱内层有一层极薄的膜,贴在伤口,杀菌又止血。一层一层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心里却是茫然:想要的生活远离她,好比隔岸看花,只一片风景,在画里华丽着,她却在尘世的因里做着无力挣扎。刺鼻的洋葱味辣得睁不开眼,灶台一堆血糊糊的洋葱瓣,手里只抱着一团洋葱芯,在灯光下剔透莹白如玲珑心。
黑黢黢的窗外,谁家的孩子放小飞炮,升到半空,橱窗前,“啪”一声红光,像夏天拍蚊子,“啪”一声,蚊子血。她凝望着窗外,忽然明白,父母亲拼命要进来的原因,是要她给他们一个清白:这屋里,除了她,没有旁的男人。这清白给他们足够的脸面和底气,才可以数落她的失礼,在栾家人面前才可以赚尽威风,耕读世家,不可以小觑。许多不情愿的婚姻,结婚是为了给娘家人撑门面,结婚后离婚,自然是为了自由。这自由,唯有靠自己去拿,强取豪夺。
前夫探进厨房,高大的身影,半堵墙。胡云看不见他的脸,却觉得出他的得意。“走。回家。闹够了吧!”
两个弟媳跟上来,规劝,似乎在她们面前的,是一张破蓑衣,需捡回去再缝补。
胡云只觉伤口里无数条蛇吐着信子。十年的屈辱和暴力,隐忍和磨难,像刽子手砍落人头的一瞬,血柱冲天。她抓起洋葱,肉馅,砧板,刀,都飞出去。
“滚……滚……滚出去……滚……”刀钉在门框,寒光闪闪。
这是她的家,她自己的家,不是狗窝,让人任意践踏!
他们惊叫着跑了。闻声而逃的还有客厅里他的两个弟弟,脸色煞白。
碗也砸出去。
防盗门巨响地关上,“哗啦啦”,瓷片四溅,溅到胡云身上,又落到地上。碎裂的痛快。
“嗵嗵嗵”连声炮响,窗外火光迸射。人家已放起了炮仗,大盒子的筒子炮,震耳欲聋。人的欢呼夹杂其间,喜悦的欢呼。炮声不绝,烟花腾空,光芒照亮了黑夜,也照着胡云的脸,变换着烟火的颜色。一切的碎裂,一切的伤,顷刻间四平八稳,都是为胜利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她打开窗,炮声和烟火似要跳进来。要过年了啊!冬天就要过去,春天要来了。
龙巧玲,女,甘肃省山丹县人,甘肃省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谁摘走了你的第二颗纽扣》、散文集《春天有双冰翅膀》、旅游散文集《向东,向大海》,《向东,向大海》入选当代精品旅游散文集。有作品入选《2014年度精品散文选》。曾获甘肃省第四届、第六届黄河文学奖,并在全国文学征文中多次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