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肉是香的,但鸡窝不可能是香的
鸡肉是香的,但鸡窝不可能是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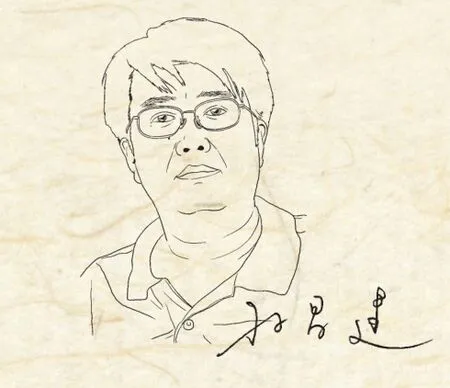
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想说鸡,我只是说人活到一定年纪和文章写到一定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事物的真相或叫事物的本质有一点点了解。老话讲,花伤春或一叶知秋,大概是这个道理。
饭桌上某个气场强大的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自己的故事,或者说改编了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他亮嗓高歌一曲,初听惊喜,复听好笑,三听就觉得此人太悖时了,因为说来说去和唱来去就是这么几句。饭桌上是人以类聚的,同时也有分工,有的人负责说,有的人负责听,有的人想说,有的人不想说,这也正如喝酒,有人每酒必醉,有的只象征性地敲敲杯,但你不能小看那些轻轻敲杯的人,有可能她只是不出手而已,她只是觉得这不是出手的场合。
如果你觉得某些人的话语烦了,你下次不去就是了,然而职场也尤如饭局,工作或者开会,按职务和职业的分工,有些角色就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你眼前出现,一些大段大段的报告,某人竟能不看稿子张口就来,初听以为发现了新大陆,然而你转了几个场子之后,最终发现他讲得还是这些,诸如“我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美国的地铁完全不能跟我们相比……”这样的话听多了,你就觉得不过如此,只是觉得这些人还有那么一点点追求,他还在考察老牌帝国主义,还在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有选择地看世界、说国情……



为有追求的人鼓掌,不管是我们站在路边鼓掌还是在场的起立鼓掌,反正这是一种现象。对于一个记者和写作者来说,这些不过是素材而已,职场官场的人物百态,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我们只能永远当个新兵,保持好奇,尤如初恋,然后且想且写,且写且想。
这些年去农村,一定会去看文化礼堂,一定会去住民宿,也一定会去吃农家菜,这已经是农村的“三大法宝”,但是我觉得这里也已经有一些新的现象出现了。比如说农家菜,以前是农家乐的标配,现在也是,但这些年民宿热兴起,农家乐正在向民宿过渡,渡得好不好,我不敢评价,包括对民宿热本身,我也只是当作神话故事来听的,因为我们的土地还是能产生神话的。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以前农家菜吃完,大家各自去散步,拍花的拍花,逗狗的逗狗,现在情况有变了,首先是主人的态度变了。现在往往支起一张茶桌,开始泡起功夫茶来了,普洱乌龙和岩茶什么的,市面上流行什么,茶桌上就泡什么,这一类的喝茶方法,就是不让你一下子喝够,因为那个水不断地在烧,主人不断地在做泡茶的动作,这一来二去的,天色也就渐渐暗了起来。喝茶总要说话,正如在朋友群里,“左中右”各色人皆有,那就说点字画方面的话题吧,不仅说,主人还带你去看他的收藏,在二楼或在三楼,本来中堂和大厅也是挂着某个地方名人的某幅字的,但这回主人向你“请教”了,有的朋友就忍不住了,又从《兰亭集序》的“失踪”开始讲起,还有的人更忍不住,于是被留下了“墨宝”……我觉得这大约已经是新常态了,即在农家乐转向民宿的过程中,主人们的一种拼和钻,至于他收藏的那些书画作品水准如何,正如那些被留下的“墨宝”到底怎样,这个不应该有我们来评价,那是下一拨客人会评价的。

文化礼堂是新农村的标配,包括广场舞什么的,村子里也很热闹,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农村很是干净,保洁工作做得实在是好。有一年在荷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几个朋友在村道上走夜路,走着走着就看到远处的光,那是村的灯光球场,正在放电影,是一片拳击木桩的声音,那应该是《叶问》吧。多少年没有看露天电影了,寻声而去,看到的景象还是有一点点失望,因为看电影的人稀稀拉拉不足半百,正如我们影厅里放艺术片的情形。这可能就是本质的问题了,当我们看到了美化和绿化,看到了清洁和有序时,我们发现大量的村子还是空心村,现在在新农村,能看到宠物狗早就不稀罕了,但如果能看几十个青壮年,那就是神话了。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的,有时我觉得红灯笼挂得越多的地方,恰恰是人最少的地方,当然逢年过节又是另一种情形了。正如去年我跑了几个乡村,去采访五水共治,我看到有的村子里一只鸡都找不到了,但养鸡专业户还是有的,否则餐桌上的本鸡哪里来呢?
跟着河长走在绿化很好的河道上时,我突然提了一个要求,我要去养鸡场看看。具体数据我不记得了,反正养鸡场离河道至少要几百米以上,那是成规模的鸡场。其实人没进场,气息就已经闻到了,这自然不是本鸡的香味,那就是养鸡场的气息,不,那就是小时候鸡窝散发的那种气息。我凑近那些鸡们,它们有的怒发冲冠,有的呆如木鸡,有的以斗鸡眼睥睨我,它们在一格一格的笼子里接受我的检阅。
本人没有机会去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地铁和养鸡场,但是当我从吾土吾民的养鸡场出来,我对那些清洁的河道有了更感性的认识。是的,感谢那些还在坚持养鸡的人,他们在鸡场撒过消毒水,但没有撒花露水。再想想伴了我们几千年闻鸡起舞的这些鸡们,也为五水共治做出了牺牲,不仅仅是人。如果说人最终会获处好处,但那些鸡得到了什么呢?我这样想的时候,那些宠物犬可能在暗自窃笑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