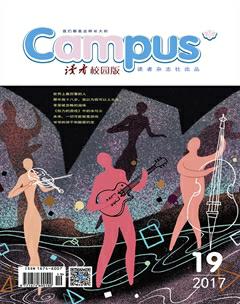《三毛流浪记》里的你情诗消失了
凌霜降,作家,编剧,河南省作协会员,现已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近百万字,出版有《偷窥》《非常爱物语》《灰姑娘的星动时代》《漂洋过海来看你》等12部长篇小说。
1996年,我在读初中,那一年有一个谣言:人们为了开荒,砍树烧山太多,山神要发怒了,要地震了,地震会毁了水库的大坝,将整个小镇都冲走。
那年15岁的我,是一个小胖妞。有点小聪明,又反被聪明误;因为偏科,成绩不好也不坏;因为自卑,人缘也不好不坏,是很普通的那种女生。
我暗恋着隔壁班的一个男生,他的成绩和我一样不好也不坏,他长得也不好看,甚至脸上因为有一块胎记而被人起了一个很难听的绰号。
那时候的我,听到别人叫他的外号,会在心里替他觉得伤心与愤怒。
但我喜欢他。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坐在我后桌,我们聊过很多好玩的话题,相互借过很多书给对方看。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那样一个男生,但就是想到他心就会乱跳。在路上偶尔遇到他一次,就会觉得心动很久。想到他的名字,会很不好意思。经过他家门口,会觉得他家的房子因为是他家而变得不一样。
总是期盼会偶遇他。激动,紧张,又害怕。
自卑少女的心事,又可笑,又美好,又有趣。
当然,我只是暗暗喜欢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表白。学校对早恋管得很严,偶尔有那么一两对被通报批评之后,父母也会觉得出门都丢脸。
当然,我主要是怕自己丢脸,怕会被拒绝,怕会被说:“胖成个球还想早恋呀。”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幼稚,也很认真。
关于地震的谣言,我是在学校食堂边的小卖店那里听到的,几个男生以讹传讹,说得绘声绘色。
镇政府已经在宣传台那儿贴了一张告示辟谣,但人们依然用一种“鬼神之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坚持,在悄悄传说着。都说很久以前,就是地震才形成了城隍镇独特的山与地貌,再次发生地震并不稀奇。
谣言愈演愈烈,终于传到了封闭式教学的学校里,我的耳朵里。
我当时就傻了。
敏感的早恋少女,脑子里总是有奇怪的想法,比如,死亡与爱情。在听到那个谣言之前,我还认真地思考过,假如有一天我忽然之间死了,除了我的父母,他—那个我暗暗喜欢着的隔壁班男生,他会不会也会为我伤心,会伤心到什么程度,会掉一滴眼泪吗?
或者,我忽然之间得了绝症,会死得很惨,我要直到死前一刻才告诉他我喜欢过他。
心里的戏一场又一场,一本正经地想几天几夜,想得彻夜不眠以致第二天在课堂上打瞌睡。
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内心戏多得太搞笑。
然后慢慢地冷静,知道自己除非自杀,否则不会轻易死。
谣言让我兴奋而又沮丧,兴奋于忽然真的有了一个横死的机会,沮丧于即使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也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去表白。
1996年的小镇百姓已经吃饱穿暖,虽然信息仍然依靠报纸、杂志与书籍,当然,还有谣言来传播,但是,像我这样的小女孩也已经有了精神追求―憧憬爱情就是当时最直接、最接地气的精神追求。
我无法阻止那种想见到他,为他动心与伤心的情绪与情感变动,所以,只能被它左右。
到谣言的第二天,他到我们班教室来向我借书。那时候,我一个在省城里的姐姐送给我一套精装的《三毛流浪记》。
那时候,小镇学校的图书馆里,基本都是《林海雪原》《红灯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书,可能连我们的语文老师都没读过张爱玲的文章,《三毛流浪记》对于我们来说是超级时髦、前卫又有思想的书。
我不想把那套珍贵的书借给任何人,但像以往一样,我没有拒绝他。他不是别人。
我说书在家里,后天,也就是周末之后的周一給他带,对了,那时候还是单休日。
那简直是我过得最坐立不安的一个周末,我帮妈妈洗衣服,衣服被河水冲走了,自己也掉进了溪水里;我去帮妈妈做饭,菜烧焦了,裤腿着了火;我走楼梯,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摔肿了额头。我在那个周日失魂落魄地做错了很多事,被父母骂了无数次。
但我不在乎,我的心里全是一句话:要不要告诉他?
死亡是什么呢?没有人告诉过我。
作为一个小孩,去参加葬礼,除了对棺材与鬼魂的恐惧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感受了。
我对死亡的理解,只能依靠自己抄来的名人名言。
托尔斯泰说:“如果我们并不害怕死亡,我相信永生的思想绝不会产生。”
我想,所以我怕死是正常的。
哈夫洛克说:“痛苦和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抛弃它们就是抛弃生命本身。”
我想,我现在痛苦也是正常的,它是生命的一部分。
卡曾斯说:“死并不是人生最大的损失,虽生犹死才是。”
我又想,是呀,喜欢的人不知道我喜欢他,可能直到我死都不知道,所以活着有什么意义?
坎贝尔说:“活在活着的人的心里,就是没有死去。”
我最后想,对呀,我告诉他后,即使我死了,他依然会记起我,哪怕只有一次。
信是半夜起来写的。想得太多,痛苦得无法入眠。没敢开灯,怕吵醒隔壁的父母会被问询。要写的有很多话,但是觉得没有一句可以表达心意。
犹豫踌躇至天将亮,才抄了一首小诗,夹进了《三毛流浪记》里:
我爱你
但我不敢说
我怕我说了
我就会死去
我不怕死
我怕我死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像我这样爱你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了那本夹着那首小诗的《三毛流浪记》,它变得特别特别的沉重,忐忑、希望、担忧、失落、惶恐、不安、羞涩、尴尬,每一种情绪都像一颗沉甸甸的石头装在我的书包里,就快让我挪不开脚步。endprint
他似乎特别急切想看到书,早读刚下课就跑到了我们班教室的窗外:“书带来了吗?”
我把书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他的时候,像拿着自己整颗装在一个脆弱的气泡里的心脏,我想说一句“你能看仔细些吗”,或者叮嘱一下“看完要马上还给我呀”之类的,话还没有出口,他已经带着那声“谢谢”跑远了。
上课铃响了。
地震是在那天早上的第三节课时发生的,我们在上数学课,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个男老师,他上课特别严格,课堂非常安静。
也因为这样,地震造成的声响就特别明显。
窗玻璃“哗哗”地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然后,大家就都感觉到了楼板好像在摇,课桌也好像在摇,所有同学都愣住了。不只是我们,就连我们的数学老师,大概在他几十年的城隍镇生活里,也没遭遇过地震。自然,他也没有什么防震意识。
有个男生说了一声“地震了”,班上顿时窃窃私语起来。数学老师停止讲课,到走廊上看了一眼,教导主任并没有拿着喇叭站在操场上喊通知,于是他又回来了,他敲敲黑板,正要讲课,教导主任播通知的声音从楼下传来了:“通知,通知。请各班老师组织同学有秩序地下楼到操场上集合。”
同学们下楼的时候,老师管不住大家说话了。
“水库大坝能受得了吧?”
“我爸说水库的水淹两个镇都够了。”
“镇周围都是山,水当然是往镇上流呀。”
“幸好我会狗刨。”
“发大水的话狗刨也没用。”
我没有别人那样关注民生,只想着地震怎么死,好像都死得很惨。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事,父母会不会有事。
可我环视走向操场的人群,人群里没有他。
我悲恸地想,死前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当所有人都集中到操场上之后,校领导通知学校因为地震放假。
宣布放假的时候,同学里还有人欢呼了一声,大多是男生。
可我怕。
这种怕带着一点点的悲壮,想象着当我死了之后,他看到书里的那首情诗时的样子。
内心戏丰富得演完了自己知道的所有悲剧电影的女孩没有等来她预想的死亡,甚至,那地震都像地球睡累了不自觉地打了一个鼾一样,整个城隍镇都没有等来传说中的大地震、大水灾,广播、电视都开始播放相关的新闻了,地震发生在别的地方,城隍镇因为靠近地震带的尾部,所以感受到了一点儿余震。
整个小镇的人们停止了谣言与恐慌,慢慢地恢复了平静的生活。而我在知道自己不会死的第一时间,就跑到了他的教室:“把书还给我呀!”
我的气急败坏一定吓着了他,他慢悠悠地从抽屉里翻了翻,把还崭新的书还给了我,我没顾得上说话,转身跑到一个没人的角落,飞快地打开书翻找那张写着情诗的纸!
可是!它不见了!
我咬着牙回去找他,问他的时候大概眼睛都急紅了:
“你真的一页都没看?”
“没呀。”
“我想借的不是这个《三毛流浪记》呀。这种书我不爱看。我喜欢看这种。”
他把一本漫画拿给我看,上面有个头上有三根毛的小男孩。
呵,原来如此呀。
我的《三毛流浪记》是少女的隐秘心事,他的《三毛流浪记》则是男孩的调皮纯真。
就像那场在人们的言语里凶猛无比的地震一样,我的表白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而我的青春期似乎也像那场戛然而止的地震一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那个内心戏丰富无比的少女,又渐渐地回到了理智的现实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