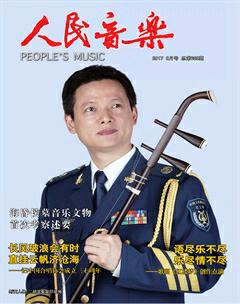试析“乐说”及其与唱的关系
文所提“乐说”,实指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的“说”,为区别于言语{2}中的“说”,也为强调其音乐属性,故冠以“乐”(yue),称“乐说”。这个概念,在此涵盖所有声乐品种中区别于“唱”的,与言语之“说”发声形态接近的音声,如各种“说”“白”“诵”“吟”以及唱段中夹杂的类似音声。“乐说”,在声乐品种中,是与“唱”平起平坐的另一种音乐表达方式。
本文所提“乐说”与唱的关系,并不等同“腔词关系”,但有交叉联系。在“腔词关系”(即声乐品种中唱腔与唱词的关系)这个概念中,强调的是“依存”(声乐演唱时,唱腔与唱词是绑在一起,互为依存的部件);而在“乐说与唱的关系”这个概念中,强调的是“对比”(声乐演唱中,“乐说”与“唱”是有意运用的两种表现方式,追求听觉上的异色彩)。
“乐说与唱的关系”与“腔词关系”之间的交叉关系主要体现为,对“乐说”的解析必须使用到对唱词音声本体(“唱词的显性音乐符号”)的非乐谱类解析手段。因为“乐说”音声与部分唱词音声是等同的。实际上,既然“乐说”与“唱”是声乐中并行的两种艺术表现方式,“唱词”这个称谓就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唱词”包含狭义的“唱词”与“说词”。
因此,论及这个话题,也需要对“音乐”这个概念有一个共识。即,“音乐”不仅包括乐音,也包括所谓“噪音”。{2} “音乐是凭借声波振动而存在、在时间中展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的艺术门类。”{4}
一代宗师刘宝全先生对京韵大鼓演唱有一个经典要求:“说中有唱,唱中有说;说就是唱,唱就是说。”这句话不仅道出京韵大鼓的演唱特色,也道出了说唱艺术(曲艺)的演唱特色。我在这里想再进一步强调的是,纵览中国传统音乐,刘宝全先生这句话其实道出了中国传统声乐品种整体的一个特色,即“说”(“乐说”)与唱的相互转换、相互融合。因此,本文所提“乐说”与唱的关系,又不仅限于曲艺类别中的说唱关系,应该说,这对关系涵盖了曲艺类别中的说唱关系,但这对关系的外延其实要广阔得多。
在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乐说”与“唱”常常是协同上阵的。它们不仅呈现为具有互补、对立的音声色彩,而且还能碰撞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音声。但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的这对关系却鲜有深入的量化研究。
为了迈出量化分析的步伐,首先需要从生理层面搞清发声器官的某些功能;其次,需要为与“乐说”相关的术语找寻定义。
一、相关常识与术语定义铺垫
在解析“乐说”之前,必须交待清楚相关概念与术语定义。
(一)发声三腔的两种功能
人的发声器官中,与造成说和唱发声形态差异最直接的部位是发声三腔——口腔、鼻腔、咽腔。这三个腔中,口腔因具有较好的开合余地,再加上舌头的作用,腔体可变性最强;鼻腔空间比较窄小且无法开合,离声带最远;咽腔是狭长的,上通鼻腔(这段称鼻咽腔),中通口腔(这段称口咽腔),下通声门(这段称喉咽腔)。咽腔本身没有出口。
这三个腔,相对说与唱,主要有两个必须说明的音声创构功能(为突出主题,本文抛开声带及其他器官在造声上的作用):其一,作为发声通道的功能,即声带振动之后,通过这三个腔把声音送出去;其二,作为乐音化的共鸣腔体功能,即声音进入腔体后,用气托住,在腔体里有规律地旋转,使声音能够按照一定的频率延展。
解析“乐说”与“唱”的发声形态,三腔的两个音声创构功能(发声通道、共鸣腔体)是关键点。
(二)“唱”的发声形态
如前所述,笔者在此论述的“乐说”与“唱”是声乐品种中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当我试图阐述它们的差异时,发现相对来说“唱”的特点比较单纯。我把“唱”的发声形态特点归纳为两点:
1.乐音化
唱,在发声时主要把三个腔体(口腔、鼻腔、咽腔)当作共鸣腔来使用,用气托住字音在其间回旋,因而产生可以持续延展的稳定音频。
2.音高比较确定
由于“唱”的发声音高比较确定,容易用音符捕捉,所以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凡是可以用乐谱记录的歌唱成分都属于“唱”。
二、“乐说”的定义与类型
“乐说”,则由于多种变异类型的存在,发声形态的呈现,显得比较复杂,需要分层次解析。
(一)“说”与“乐说”的差异
毫无疑问,相对唱,“乐说”的发声形态必然是接近说的。语言学里的“说”,是“言语”的意思,即用语言传递信息。而传统声乐品种中的“乐说”,如前所述,则是与“唱”相对应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
言语中的“说”,发声状态基本上用的是三腔的通道功能,当然有时也用三腔的共鸣腔功能,如拖长声呐喊时。不同地域的人群,甚至人与人个体说话习惯也可能兩种功能使用产生差异,但总体上,言语中的说,主要使用三腔的通道功能。
传统声乐品种中的“乐说”相对言语中的说,其差异是:首先,身份不同。“说”是信息交流的手段,“乐说”则是声乐品种的一部分,本质上已成为该听觉艺术的音声,也就是音乐身份;其次,基于上述不同,导致“乐说”在音乐艺术审美的需求下还可能产生诸多变异。
(二)“乐说”的多种类型
我把声乐品种中的“乐说”分两种类型解析:一类是较典型的“乐说”;另一类是非典型的变异“乐说”。
1.声乐品种中的典型“乐说”
这种类型的“乐说”之所以言其“典型”,是因为它们在发声形态上与言语中的“说”基本类似或比较接近。我在此把典型“乐说”的发声形态也归纳为两点(与上述“唱”对应):
(1)非乐音化
声乐品种中典型“乐说”的发声形态与“唱”相比,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它们主要把发声三腔(口腔、鼻腔、咽腔)当作字音的发声通道,而不是共鸣腔体。
(2)音高不够确定
声乐品种中的典型“乐说”稳定音频延展时间较短,要么唱词音值短促,要么唱词音高急速进行(或上趋,或下趋)微观运动。
典型“乐说”主要存在于传统说唱曲种中大段的叙述、戏曲的散白,还有各种传统声乐品种唱段的唱词之间,如苏州评弹《新木兰辞》中“惊[t?揶i?誽]闻[v?藜n]可[kho?揲3]汗[?捩?尴13]点[ti51]兵[pi?誽]卒[tso]”这一句中的“卒”,与同段的另一句“又[jy]见[t?揶i]兵[pi?誽55]卒[tso?揲3]”这一句中的“卒”,与同段的另一句“又[jy13]见[t?揶i51]兵[pi?誽55]书[s?尢51]十[s?藜?揲3]数[s?奕?蘼?諧51]行[h?魨?蘼?誽13]”中的“书”,在演唱时都是“说”出来的。“卒”是入声字,“入声短促急收藏”,演唱时音值短促而有弹性;“书”字演唱时是下趋字调。这两字的音高都站不住。
上述例子之所以归入“乐说”,简言之,是因为它们是声乐品种中的音声,却难以用音符准确标示,音声形态更接近言语中的说。
2.声乐品种中的非典型(变异)“乐说”
由于声乐品种中之“乐说”的存在目的是进行音乐表现,它们必然会根据不同的表现需要追求一定的艺术夸张,而且是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艺术夸张。有些艺术夸张仅仅表现为节奏上的变异,例如“急急忙忙”这四个字,在作为言语的说中,节奏是以××××均速呈现的;而作为说唱品种中的“乐说”却往往夸大成符点化,变成×·×××。有些则是全方位的变异,如各地大戏中的“韵字”就迥异于言语中的方言字,它们在作为韵白出现的时候,在音色、音调、音值各个方面都可能出现明显的艺术夸张,有些还更多地使用了三腔的共鸣腔体功能。如图表1京剧韵白“夫人哪”中的衬字“哪”字。
如果不使用共鸣腔体功能,是不可能呈现的。之所以把它还称作“乐说”,是因为尽管这个“哪”字已具有唱的某些特点(用气托起的高低起伏地长音),但它的音高相对不确定,依然不能用音符记录。
总之,作为声乐品种中的两种表现方式,“唱”与“乐说”的本质区别就是能否用音符准确记录(凡加用上趋或下趋箭头处,都算不上“准确”记录)。声乐品种中的“乐说”不仅涵盖声乐品种中所有不能用音符捕捉的“诵”“念”“白”“吟”等明显属“乐说”的三腔(口腔、鼻腔、咽腔)发声成份,而且还包括唱段中夹杂的,不能用音符准确捕捉的三腔(口腔、鼻腔、咽腔)发声成分。
三、“乐说”的存在及其与唱协同的审美意义
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乐说”的存在以及“乐说”与“唱”作为两种声乐表达方式的协同关系,都有着极其丰富的探索空间。本文仅举隅若干。
(一)互为主配角
在称谓为“说唱”的曲种里,“乐说”与“唱”的搭配作为主要特征之一,肯定应该是常态。可更值得我们正视的是,事实上,由于中国语言中原本就存在字调{5}造成的旋律感,在说唱品种以外的声乐品种(如戏曲、民歌)中也大量存在“乐说”与“唱”搭配使用的现象。由于戏曲里专设有“念白”,唱段里便往往是以“唱”为主,以“乐说”为辅。再有,许多地域的吟诵调、吟唱调(甚至山歌),是以半说半唱,甚至是以“乐说”为主:以“唱”为辅的方式存在的。
(二)线性对比
中国文化充满“线”的艺术精神,如同节奏方面,会有“散—慢—中—快—散”等异质节奏转换的线性审美追求传统,音色方面,“乐说”与“唱”的线性对比也处处显现。
由于汉字音声的特殊性,“乐说”状态的唱字本身就有音高起伏的字调,“乐说”与“唱”的衔接在传统声乐品种中就显得极其自然,呈示了既有对比,又有内在联系的线性自然流程。下面这支龙岩山歌(谱例1{6})的句子结构(这句的歌词大意:“什么生下来就能叫爹”{7}),是先以“乐说”起音,“说”着“说”着,逐渐进入“唱”,最后一字又归入“乐说”状态(音高没有在固定位置延展,而是故意走向下趋,我用下趋箭头标示,此乃“乐说”的特性)。“乐说”部分音高无法记谱。我的办法是,“乐说”部分,乐谱只记节奏,乐谱下面一行的国际音标直接记字调;“唱”的部分,乐谱开始记音高,下面那行音标就只记辅、元音而省略字调符号,最后一字在音符外再附以下趋的箭头(标示其变异“乐说”的特质)。
于是,一个“乐说”- 唱 -“乐说”的线性变化流程清晰可见。
(三)“点”式对比
仔细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在民间声乐品种中,实际上民间艺人们是相当刻意地使用“乐说”与“唱”这两种艺术表现方式来寻求对比。“乐说”与“唱”的线性对比之外也不乏“点”式对比,如下例是一个同字异方式的“点”式对比:
五音戏《王小赶脚》里有句“大口地吃姜不觉辣,大碗地喝醋也不觉酸”,我听了好几个音响,发现五音戏演员们对这句唱有一个共同的处理方法,即第一个“大”是“说”出来的(“乐说”状态),第二个“大”却是“唱”出来的。再加上音高差异,这两个“大”字就形成了特别鲜明的色彩对立(见谱例2{8})。
(四)“樂说”之于雅俗分野
中国传统文化素有雅俗分野,音乐文化也不例外。雅俗风格的音乐文化是相对存在的。音乐中的雅风格,一般指加工痕迹较重的艺术化风格,审美适应群体往往是受过教育的阶层;音乐中的俗风格,一般与野趣、生活化相联系,审美群体多为底层百姓。有意思的是,民间艺人们竟巧妙地利用“乐说”不同类型的存在,在民间音乐之集大成者——戏曲里自然地实现了雅俗分野的对立统一。前面曾提到,戏曲的念白分两类,一是韵白,音声的艺术变异较多,多用于有身份的人或主要角色,行当类型如正旦、老生、老旦;另一种是散白,音声与言语中的方言较接近,多用于花旦、丑角。而这两大类念白在各剧种中的审美差异,恰恰呈现出的是雅、俗艺术观的差异,同时又能呈现雅、俗艺术风格的相互映衬。
其实,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这种“乐说”与“唱”搭配的普遍现象,正是中国传统声乐演唱中,一种有意增加对比因素的艺术技能。高超的演唱者总能将这种技能运用得精妙无比,意味无穷。也就是说,方言中的说(言语)进入声乐品种,经过不同层次的艺术加工形成不同类型之“乐说”,呈现出与“唱”交相辉映的艺术表现特色。
可以想见,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乐说”,无法用乐谱标示清楚的“乐说”在演唱中会增加何其多的难度。无怪乎我们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一向借助口传心授。显然,“乐说”与“唱”的高频率搭配是基于语言的中国特色(旋律型声调语言{9}),展示的是语言与音乐的特殊亲缘关系。研究各民族各地域声乐品种中“乐说”与“唱”的搭配,存在着巨大的开掘空间。这类课题的研究,乐谱类与非乐谱类手段缺一不可。我的学生彭彦婷{10},最近在其硕士论文《语言音乐学视角的湘剧高腔音乐探究》中,结合乐谱与非乐谱手段,把湘剧高腔音乐的“念白”“放流”“放腔”,很有新意地梳理出了“‘乐说与唱协同关系三层次”。
这个领域的开拓成果是可以期待的。
{1} 本文基于2015年,笔者在巴黎ICTM(国际传统音乐学会)“说与唱的阈限”专题论坛上的发言修改稿,发言题目是“Speak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Vocal Music and its Relation to Singing”。
{2} “言语”,是语言学术语,特指以语言传递信息的行为。
{3} 钱茸《唱词音声的“音乐性”再认识》,《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82—85页。
{4} 赵沨、赵宋光《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 舞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5} 由于中国文化的模糊性特点,使得汉字往往会一字多义。声调的“声”字就有这种倾向。为了不产生歧义,我具体谈及汉字声调时,尽量使用“字调”。
{6} 郭金香演唱,钱茸记谱注音。
{7} 歌词翻译:陈舜迪。
{8} 张晶、钱茸改谱注音
{9} “旋律型声调语言”,语言学界术语。从声调的视角,全世界的语言分两大类:声调语言与非声调语言。声调语言又可下分两大类:高低型声调语言与旋律型声调语言。汉藏语系语言属旋律型声调语言。详见林焘 王理嘉《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124页。
{10} 彭彥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17届硕士毕业生。
(作者附言:由于ICTM中国理事萧梅女士力荐我前往巴黎作专题论坛发言,促使我思索出了这个论题。特此表示感谢。)
钱茸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責任编辑 荣英涛)
——评陈辉《浙东锣鼓:礼俗仪式的音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