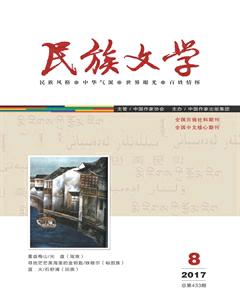光棍的房子
韩静慧
一
村民们都说,蒿子沟最有福的光棍就是老甘图。
因为蒿子沟老少加起来就三个光棍,唯独老甘图今年住上了政府给盖的免费房子。
甘图的房子盖在村西口,在村子中间那条主路的边上,因为没有围墙的遮挡就格外显眼,每个进村子的人第一眼都能看见这两间漂亮的房子:白瓷砖墙,红瓦屋顶,白色塑钢窗子,里里外外四白落地,亮亮堂堂。
于是村里就有人生气:
“他炕头上睡着女人,凭啥算光棍?”
“盖了房子也不住,这房子纯粹是给那‘烂板凳盖的。”
“这不是骗取国家资金吗?”
村民刘三也羡慕嫉妒恨,但他的恨只在心里装着,从不用嘴巴表达,谁也看不出他真正的心思。他见着老甘图照样点头哈腰地招呼二哥,一脸谦卑的微笑。他历来认为自己在蒿子沟三组是最有品的人,不能跟一般的村民那样没事骂大街。
刘三有自己恨人的文明方式——告状。他三天两头去代理村长(村民对村主任都称村长)陈波那儿告状,但一回来就装作啥事都没发生。
陈波为什么是代理村长?因为这个村的村长甘文只干了一年就被村民刘三拉下了马。刘三当初也想当村长,但他的实力不如甘文,人家甘文竞选那天给每个村民补助误工费二百元,而刘三只拿出了区区一百元!更让刘三始料未及的是,竞选那天甘文把所有去外地打工但户口仍在蒿子村的村里人都一一请了回来,连跟随儿女住在城里的那些耳聋眼瞎的八九十岁老婆子、老头子也都用小轿车像接祖宗一样恭恭敬敬地接回了蒿子村,甚至两个中风瘫痪的病人也用担架抬了回来!这小子真是贼呀,一票都不想放过,还美其名曰:要尊重所有村民的选举权!尽管刘三在会上把蒿子村的未来蓝图描绘得比玉皇大帝住的天宫还美好,还唾沫飞溅地许了一大卡车愿,承诺出去招商引资把蒿子村那满山坡的蒿子都兑换成金条……但仍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的那些狗屁蒿子梦想,村民们把票都投给了那个在城里发了点小财的甘文,甚至几个刘姓家族里的人也见钱眼开临阵当了叛徒!甘文高票当选,刘三损失了不少钱,把气都撒到甘文身上,选举结束后他不但处处给甘文找麻烦,还天天去镇长办公室上班,告甘文贿选。
2015这一年镇政府办公室的门槛都让刘三给踏平了,搞得镇长不胜其烦,只好派了个工作组去蒿子村调查甘文的贿选情况,这一调查还真调查出甘文给村民二百元钱的事情,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钱,所以镇长大巴掌一挥,就把甘文给挥下台去了。甘文本想回家乡施展一下自己的才干,但经过这一折腾,对生他养他这块土地上的人很失望,又回城里挣自己的省心钱去了。甘文下去了,让谁去当这个村长?总不能让这个一肚子小算盘的刘三干吧?何况你告人家贿选,你自己不是也参与贿选了吗?
镇政府为蒿子村琢磨了半年村长也没琢磨出来,像样能干一点的中青年都去城里打工了,谁也不回这个地处高原的塞外小村子,剩下的不是有这个缺点就是有那个毛病,稍微聪明一点的也都自己搞点养殖,有的村民还公开跳出来瞎嚷嚷:今年中央管得严了,不允许随便征地了,没好处谁愿意去操那些闲心,不如自己挣点省心钱……
就这样蒿子村的村长位置空缺了半年,镇政府非常着急,于是就派街道司法所的所长陈波到蒿子村临时兼任村长。
陈波戴着一副白边的眼镜,白白瘦瘦的身材,文文弱弱的气质,一看就是个长期坐办公室的,没在农村牧区摸爬滚打过。
这陈村长听了刘三告的状,就悄悄地跑到蒿子村微服私访,他把脸贴在老光棍甘图小房窗玻璃上往屋里窥视,想看看里边到底有没有女人。这时辰正是农牧民们在家吃晌午饭的时候,村长是专门挑这个时间来的。因为他觉得如果这个房子里住着人,这个时候就能一目了然。
村长这一看不得了,里边不但没有女人,连男人都没有。共计两间屋子,一间堆满了镐头铁锨镰刀马鞭马鞍子等农具,另外一间屋关着一匹马,那马本来正安静地低头吃草,听见动静警觉地抬起头来,将那傲慢冷漠的大马眼投射过来,也许它以为这个自己从没见过的白面书生要侵犯自己的领土,是的,这房子从一盖好主人就把它从那个四处漏风漏雨的臭棚子领了出来,领进了这个亮亮堂堂的新房子里,这是它的岛屿,主权归它,除了它的主人能进这个领地,别人都无权进来,即使是脸蛋子贴在玻璃上张望也具有偷窥的可耻企图。是可忍孰不可忍,维护领土完整是自己的责任,大白马瞪圆两只鼓鼓的马眼用鼻子愤怒地向外喷气:“噗噗噗——噗噗噗”,大白马喷出来的气将马槽里的草吹得飞起来,也把本来很干净的窗玻璃弄得雾气蒙蒙的。
陳村长心里的愤怒也不比大白马的愤怒小到哪里,好呀,政府给光棍盖的亮亮堂堂的好房子现在成了马棚,怪不得这刘三盯着这件事没完没了!人家就是告得在理!这还了得,如果这事自己不解决,将来真查下来,自己吃不了也得兜着走。
陈村长气冲冲地找来这个村的村民小组长,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大骂:“政府给钱盖的房子是给人光棍住的,不是给马光棍住的,你们村的马怎么他妈的这么金贵,那个什么甘图老光棍既然有住处,既然有女人,你们为啥还要打报告把他当成光棍让政府拿专项基金给他盖房子?他现在在哪里?如果他真不需要那房子就立刻没收给村子里其他的光棍住。”
陈村长劈头盖脸的一顿大吼把蒿子村三组组长吓得膀子都斜了,这代理村长别看长得文文弱弱的很奶油,脾气还真不小。
三组的组长平日说话本来就结巴,这回更结巴了,好在人还算聪明,说话咬骨头,他结结巴巴地说:“陈村长,村里……村里老老少少……就……就三个光棍,一个……一个是甘图的哥哥甘钢,他在石灰厂打工得了矽肺病几年前就死了。”
结巴组长结结巴巴地说,陈村长听得很费劲,他不耐烦地摆摆手,心想这蒿子村的人都死光了?怎么选出这么一个结巴当村民组长,下一步我就把这家伙给换掉。
陈村长厉声呵斥道:“那另外一个光棍呢?给他盖房子了吗?”
结巴组长被陈村长一吼立刻不结巴了:“另外一个姓刘,上个月政府刚要给他盖房子,可他一时想不开在果园的一棵果树上吊死了。你说这小子,四十多岁了,怎么就想不开呢?”
陈村长问:“他有什么想不开的,国家要拿钱给他盖房子,他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结巴组长立刻解释:“唉,可怜呀,四十六岁了还没讨到老婆,又生了鼻癌,咱政府还真没少管他,现在看病住院有新农合,出院就给报销。但他那病不是三两个钱能治好的,就是报销自己也得先拿钱交上呀,一次一次地跑医院,那药忒贵了,一个光棍老农民实在承受不住,也受不起那个罪呀,就一时想不开跑到僻静地方上吊了!这不是吗,我刚给他老娘送殡出来。这几天可忙坏我了,连抬棺材的人都没有,村里的年轻人都走没了,半个村子都空着,上哪里去找抬棺材的人,最后没办法还是求人找辆卡车送到坟地的。唉,这村子不大,啥……啥事都靠……靠我张罗。”
陈村长被这结巴组长给搞蒙了,这叫啥事,不是光棍上吊了吗?怎么这又出了一个给什么老娘送殡!
结巴这才解释:“这不是光棍上吊死了吗?他老娘昨天去给他烧头七,竟然在坟头前哭死了,一起上坟的人以为她哭晕过去了,就又拉又打核勒(用手拍肋骨处)的,等发现身上凉了才往医院送,送到半路人都僵硬了,只好又拉了回来,七天工夫死了两口,阴阳先生说老光棍死的时辰不对,犯内乎,乎死自己亲娘了。”
陈村长觉得这组长实在不像话,怎么还相信阴阳先生什么犯内乎外乎的,都是不懂科学的狗屁话,你说这个蒿子村还有好?村组长不但是个结巴还是个啥文化都没有的老迷信,蒿子村蒿子村,就出结巴这样的蒿子,连小组长这样最小级别的村组干部都扒拉不出来像样一点的人才。
陈村长和结巴这一扯,脑袋里全是“内乎外乎”的事情了,差点就忘记了身边那亮堂堂的两间房子,多亏房子里边的大白马响亮地打了一个响鼻才使他转过神来:“听说你们村的甘图是有女人的,不算光棍,你们为什么谎报他是光棍?骗国家的钱给他盖房子?”
这大帽子可是太大了,结巴吓得一哆嗦,这回一点都不结巴了:“那女人是人家的,不是他的女人呀,他只是在人家家里睡觉。”
“啊,什么?睡人家的女人?”
“啊,就是,就是,就是人家的女人。”
结巴手往那两间房子下边一指:“他就睡在这家。”
陈村长顺着结巴的手指向下一看,一个方方正正的砖墙院子里,四间白墙红瓦的大房子矗立在老光棍的两间房子下方,院子的南边是菜园子,菜园子里绿油油的,还种着几棵果树。院子的东边有一个羊圈,圈里并没有羊,是空的。房子的前边已经都被水泥硬化,水泥地上晒着一些粉红色的肉蘑菇,墙上挂着一些用线穿起来的瓜条子和红辣椒,整个院子干干净净的,一看就知道主人是个整洁利索的人。这是蒙东地区特有的农牧结合的院子,既有农家的菜园子,又有草原特色的牲口棚子。因为这个村子自古以来就是汉蒙满人杂居的地方,蒙古人满人和汉人的生活方式早已经水乳交融,无论是从表面上还是生活习惯和语言上根本就分辨不出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所标注的民族身份。
“这家的女人叫啥?多大岁数?她男人叫啥?”
陈村长又好奇又生气地问结巴。
结巴组长立刻回答:“这是烂板凳的家。”
陈村长皱了一下眉:“什么叫烂板凳?哪有烂这个姓?”
结巴组长立刻解释:“嘿嘿……我……我说顺口了,烂……烂板凳是蒿子村的人对白琴琴的称呼,意思是……是白琴琴这个女人像……像一条烂板凳一样,谁都可以坐。”
陈村长问:“她多大年龄?”
结巴说:“都六十七八岁——岁了。”
陈村长冷笑一声:“六十多岁的老婆子还有人坐?你们这村没女人了?”
结巴立刻解释:“这烂板凳的名是……是从她年轻的时候叫……叫起来的,再说……说了,你别……别看她六十多岁了,脸上还像桃……桃花一样粉……粉呢,想……想当年是这个村最漂亮的媳……媳妇,和演员刘晓庆一样好看呢。”
陈村长听结巴一说,立刻对这个老女人有了兴趣,他又扫射了一遍院子,希望那个快七十岁还粉面如桃的女人忽然出现在院子里,但他等了半天院里还是静悄悄的,于是他又转头问结巴:“她的男人怎么样?”
结巴说:“她男人是这个村最帅气……最好看,个子最……最大的男人,但也是这个村最窝囊,最没能力,一分钱也挣不来的囊货,窝囊到……到啥程度你知道不?”
陈村长说:“我不知道!”
结巴说:“嗯,不知道我告诉你,她男人窝囊到能和另外的一个男人与自己的女人睡在一铺炕上,怕打扰老婆和别人亲热还得转过身去脸贴在墙上大气不敢出。”
啊,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人?
陈村长一声惊叹,结巴看看陈村长那一脸的惊愕,撇了一下嘴巴,心里冷笑:哼,世界上的事你不知道的多着呢,别以为你这小白脸比我多读几年书,农村的事你知道个屁。甘文能耐吧?在城里跑了十年挣了点钱跑回来说什么治理家乡,竞选村长,刚当了一年,还没等施展他的那些宏伟计划就被刘三拉下马了,没进监狱就算便宜他了。就你这只读过几本法律书的小白脸,还来给我们当村长!嘿嘿,等着瞧好戏吧。
这个时候,一群羊咩咩叫着从马路的南侧走了过来,大概有三十多只,那羊全是黑脑袋白身子,这种羊叫杜蒙羊,是内蒙古本地的羊和澳大利亚引进的种羊繁殖的后代,这种羊不但耐寒性强繁殖能力也特别快,非常适合蒙东地区冬长夏短的寒冷气候。
羊群的后边跟着一个看起来像五十多岁的女人,女人穿着一件白底粉花的上衣,褐色的褲子,梳着齐耳短发,整个人给人一种干净整洁的印象。
羊群走近了陈村长又从陈村长的身边绕过去走进了陈村长刚才端详的大院子,陈村长看见羊走进院子才回过神来:哦,这个人一定是那条烂板凳……不,是那个白琴琴。
陈村长将目光飞速地定格在白琴琴的脸上:只见那脸虽然在眼角处有几条皱纹,但那皮肤还真的是白里透红,粉面如桃,两只黑黑的眼睛虽然很小,但天生就夹带着微笑,且黑白分明,看不出这个年龄本该拥有的浑浊,脸部轮廓也像年轻人一般清秀,一点多余的赘肉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