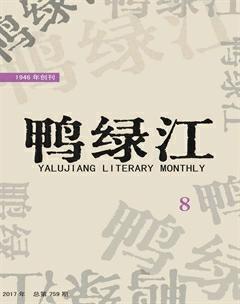骚动
安宁
1
明光村不是一个村。不过或许很多年前,是一个村的。反正北京这地方,随便一处,都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明光村在成为一个小区以前,是不是世外桃源一样的山村,似乎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老旧的几乎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楼房的小区,在十年以前,房屋均价就已经高得让我不做任何留在北京的念想了。
在海淀区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大楼面前,明光村跟北京土著大妈有一样的气质,苍老,却不服老;小钢炮一样炸响的京味普通话里,全是当家做主人的豪迈。在北师大没有买下明光村废弃的小学做女博士宿舍楼之前,每天黄昏,太阳将柳树的影子,拉长到小操场正中的时候,一群天真的孩子便从中飞奔而出,冲进腔调高昂的爷爷奶奶怀里,尔后一老一少沿着小区安静的石子路,说说笑笑地走回家去。但在更高档的小学相继建成之后,这所明显设施落伍的学校,便被人嫌弃,最终沦落为第三类人——北师大女博士们的“流放”地。
不过住在这里,却有世外桃源之美。一进圆拱形的小院门,明光村外的喧哗,和明光村小区的琐碎日常,就被锈迹斑斑的吱呀声给关在了门外。毫无疑问,被一圈柳树环绕的小操场,是这方天地里最让人喜欢的安静所在。女博士们喜欢运动的不多,大多数深居简出,即便出门,也是看电影,赏话剧,听讲座。游魂一样在小操场上散步的,看不到几个。但这反而让宿舍楼前的角落显得愈发静谧了。
雨后,周围斑驳的墙壁上,会看到许多奇迹般冒出的蜗牛,一个一个争先恐后地朝天空上爬行,也不知之前干旱的时候,它们都躲在哪儿。如果弯下腰去,会看到蜗牛不停屈伸向前的身体上,闪烁着湿漉漉的光泽,好像它们裹在柔滑的绸缎里。这总让人想起夜晚站在路灯下,与某个男人温柔絮语的女博士,学术的冷硬与枯燥,像蜗牛的外壳,经过雨水的冲刷,现出柔软的色泽。一切都是静谧的,柳树的枝条被风吹拂着,发出细密的私语。旗杆在夜色中叮当作响,大约陷入了昔日被小学生日日仰望的回忆之中。沿墙根的小舞台上,一株槐树落下鬼魅的剪影,那影子在风里飘荡,偶尔,会飘出一个长发的女生来,也不知是在想高深的物理,还是抽象的哲学。
如果每天不用去听讲座,或者被导师召见,住在这里,跟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们同进同出,很有些养老的意思。明光村周围全是纵横交错的高架桥,喧嚣自半空重重砸下,行至小区门口,就慢下来,及至博士楼下,更是缥缈遥远起来。人与蜗牛一起,被这种静寂缓慢的时光缠绕住,只看得到树叶间隙里,漏下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天空,蓝得晃人眼睛。
对,十年前北京的天空,还很少与雾霾这个词语联系在一起。只有风,很大的风,在春天浩浩荡荡地穿越整个城市。大风将天空吹得格外干净,清澈,以至于连云朵都彻底地消失。就连平日里拥挤的高楼大厦,也似乎后退了几千米。世界在明光村空旷起来。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生活简化为一粥一饭,一书一室。我几乎有些感谢这猎猎的大风,将内心的一切杂念扫荡一空。整个博士楼安安静静的,连小操场上麻雀的叫声,也都歇了。楼道里偶尔闪过一两个人影,幽魂一样鬼魅。如果不出门,很难见几个精致打扮的面容,几乎清一色的肥大的睡衣,人裹在其中,好像蚕茧里小小的蛹,晃来荡去的,听得见窸窸窣窣的声音,却寻不见丝毫的踪迹。
当然会互相串门,交换彼此专业的信息,导师的最新指示,或者学术报告的消息。女人们热衷的校园内外的八卦,或者爱情、化妆首饰服装,当然也在谈论之列。相比起黄蓉与李莫愁们,我们这些“灭绝师太”,还多了一项关于丈夫、孩子与婚姻的探讨。同样处于与爱人或者男友的“分居”状态之中,共同话题里便有了惺惺相惜。性也不是难以启齿的事情,同为“过来人”,就连婚姻里的情感波动,心思游移,都可以与亲密的同学倾诉,反正,早晚我们都要回到各自的城市,互不打扰地继续生活,这一场持续三年的相遇,因为没有任何的竞争与功利,便可以彼此坦诚地交换内心的烦恼。
常来我们宿舍的阿路,是双胞胎母亲。她来北京的那年,两个女儿才一岁半,所以她的这一场读博,便被家人定义为自私的出逃。逃避的当然是养育两个女儿的责任。但事实上,虽然她很少提及,从楼道里总是以争吵为主的电话中,我和舍友橙子知道她逃避的还有岌岌可危的婚姻。所以每次阿路推门进来,都裹挟着一股怨气和躁动。她说话的语速飞快,当然大部分的女博士,都有着非凡的足以吸引导师并清晰阐释自己学术观点的口才。电视台记者出身的阿路尤其如此;但凡她来,我和橙子都只能支起双耳耐心倾听。她的机关枪会突突突地从两个没人照管的可怜的女儿,转到单位里的奇葩同事,再到学界的某个霸主。但不管谈及什么话题,她带来的负面消息居多。我因此不喜欢听她絮叨,并庆幸博士开学时,她临时调换宿舍到对面房间,离开了我和橙子。
但即便关了房门,也还是会听到走廊上阿路歇斯底里的叫骂声,当然是跟她正在闹离婚的老公。她那么焦灼地在电话里诉说着自己的不幸,总让我想起祥林嫂,只是没有人,包括我在内,能够切身地体会到她的痛苦。她的老公,当然更不能。他们像一对仇人,站在悬崖边缘,进行着一场殊死较量。至于两个尚未学会喊爸爸妈妈的女儿,则被阿路寄养在姐姐家里。我只见过一次她与女儿的照片,在她的電脑里。照片上的阿路一家,拥挤在一起,表情幸福。我想阿路一定更希望活在这张照片里,而不是鸡飞狗跳的现实之中。
最初,阿路还会每隔十天,乘坐高铁回家一次。后来,她办理了停薪留职,就很少回去了。那个时候,她在楼道里讲电话的声音,开始变得温柔,语速也慢了下来,不再是急吼吼的样子。从她的身边走过的人,会下意识地放轻脚步,似乎怕打扰了这样甜蜜的絮语。她当然不是给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电话,她们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能让她的心安静下来,她们的哭闹和吵嚷,只会加重她的烦恼,和对世俗人生的厌倦。唯一能够让她快速行走的双脚,闲庭信步的,唯有爱情。
夏天的北京城,被热浪裹挟着,人稍微转一下身,便会汗流浃背。明光村里的狗,趴在阴凉地里,伸着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似乎它们不是趴在地上,而是被架在巨大无边的蒸笼上。夜晚,闷热让它们连狗的职责也忘记了,有人走近,一点声息也懒得发出。树上的知了也被晒得快要熟了,只偶尔在周围的车水马龙声中,发出一声慵懒的叫声。明光村里修鞋的,配钥匙的,卖米线的,开小卖铺的,也惰怠了,躺在树下的竹椅上,不耐烦地摇着蒲扇。鼻尖上的汗水,细密地堆聚着,而额头上的一串,早就滴答滴答地滑落在水泥地上,随即又被毒辣的太阳蒸发掉了。
这样的酷暑里,人人都躲进空调房不肯出来。博士楼里当然是没有空调的,但吱呀作响的风扇,也多少给人一些安慰。我抱着冰镇的西瓜,试图获得一丝清凉。就在我抱怨着这密不透风的北京城的时候,阿路的声音,却溪水一样叮咚流淌过来。那声音好像一只鸟在绿荫里歌唱,而且永不厌倦地唱,一直唱到死那样地唱。
一个少妇恋爱了。我将勺子插在吃了一半的西瓜上,笑嘻嘻地对橙子说。
橙子拉开门,装作去洗手间,在楼道里走了一圈,回来便笑道:作家的想象力果然能逾墙钻隙,窥到秘密。
几天后的傍晚,我趿拉着拖鞋,在小操场上散步,刚刚不留情地拍死一只落在大腿上的蚊子,鲜血还没有揩干,就见阿路捧了一大束玫瑰,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雀跃着走了进来。那玫瑰红得如此鲜艳,以至于我觉得很像我手上的蚊子血。我有些嫉妒,朝阿路挥挥手,却吝惜口中的赞美。况且,我说什么好呢,夸耀玫瑰漂亮,爱情中的阿路也美艳动人吗?还是祝贺她寻到真爱?我觉得对于一个已婚的女人来说,似乎,都不合适,或许语气稍微有些波动,被她当成讽刺也不一定。所以我还是聪明地闭上嘴巴,什么也没说。
但阿路却捧着那一大束耀眼的玫瑰,到我们宿舍里来,要借橙子的花瓶一用。她脸上的笑意,比小贩脸上的汗水还要浓密,只那溪水一样汩汩流淌的微笑,也足以浇灌玫瑰。
我和橙子正不知如何应对阿路的幸福,她却埋头深深地嗅了一下玫瑰,尔后笑道:以前真不知道玫瑰这么香气袭人,简直让人迷恋。
橙子笑嘻嘻道:那也得看谁送的哦!
第一次见眼角已经有了皱纹的阿路,羞涩地一低头,随即又骄傲道:当然是我的追求者。
女人即便到了六十,即便读到了博士后,怕也逃不掉这一点点有人爱慕追求的虚荣。而对于刚刚从奶粉尿布中逃离出来的博士少妇,这一束玫瑰,几乎像是小孩子贪恋的糖块一样甜蜜诱人,以至于在我们面前,阿路忍不住晾晒这一旦曝光,可能会带来离婚事件的婚外恋情。
阿路显然已经将婚姻置之度外了。她只想要爱情,就连她的女儿,还有即将开题的博士论文,也暂时不在考虑之列。她要闪光的糖果,她要危险的爱情,她要挽救她于歇斯底里边缘的男人的手。她有深邃的欲望,在本应步入平静河流的中年。
明光村,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村。我在声声的蝉鸣中,这样想。
2
明光村的北门口,天长地久似的住着一对卖杭州小笼包的老夫妇。在我尚未入住博士楼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北京待了许多年。据说,他们用卖小笼包的钱,给儿子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子,又娶了媳妇。除了过年,他们一年到头都待在北京,好像這里才是他们的家。但又明显,他们从未眷恋过明光村。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随时都可以离开另起炉灶的漂泊感,跟所有来吃小笼包的顾客都是陌生过客的疏离。他们的小笼包非常正宗,我吃过一次,就上了瘾,隔一天不吃,便很是想念。他们的米线和馄饨也无比美味,就是桌上的一小碟咸菜,不知为何,也比别家的更清香一些。
我每次吃小笼包,都要几瓣大蒜,给老板娘说,她从来不会像别家那样,响亮地来一句“来喽”,她只装作没听见一样,转身进屋,也不知在小而拥挤的店铺的哪个角落,寻到了一头大蒜,皮早就干透了,轻轻一搓,就窸窸窣窣地掉下来。女人将蒜放到我的面前,依然一句话都没有,便去忙碌。
有手艺的人,总是牛逼的。橙子如此总结这一对不讨好任何顾客的小笼包夫妇。
有时候,忍不住会对他们的冷淡生气,对橙子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吃了,就连附近枫蓝国际地下一层拥挤的美食城,都比这里服务态度更好。
可是没过两天,我又忍不住,被路过时小笼包鲜美的味道撩拨着,挪不动腿。即便是绕着他们简陋的店铺走,女人将长而柔韧的米线,弯腰从夏天的铁桶里捞出来时,那水滴滴答答落在沸腾的热锅里的声音,总在我的耳畔回响,我因此被诱惑着,恍恍惚惚地又迈开腿,朝明光村门口走去。
况且,哪个美食城,是开在一株茂盛的大槐树下的呢,这跟“明光村”三个字,如此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想想,初夏的傍晚,坐在大槐树下,被清凉的风吹着,蘸醋吃着一小笼蒸包,这跟乡下的人,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呼噜呼噜地吃一碗面条,有什么区别?不外乎一个是蹲着,看地上的蚂蚁抢剩饭吃,一个则悠闲地坐在板凳上,看风中来来往往的路人。这比挤在地下小吃城里,看人脑壳和屁股,不知要好多少倍!
所以我跟自己置气没两天,便放下颜面,又灰溜溜地走到他们的小吃摊上,自己抽出廉价的餐巾纸,擦擦落了一泡麻雀屎的板凳,假装从未发生过什么似的,叫一声:老板,来一碗米线,外加半份小笼包。
女人依然是淡淡的,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连一个“哦”字也没有。但我知道不用催促,不过是五分钟,她或她的男人,自会将我所需,准确无误地放到我的面前。
在吃到额头上浸出细密汗珠的时候,对女人的埋怨,便随着汗水从体内全部蒸发,又被餐巾纸擦过后,丢进了大树下的垃圾桶里。就像他们从未记得我是谁一样,我也因这样家常朴质的美味,而在那一刻,原谅了他们的冷淡。
每天出出进进,我从未见过老夫妇的儿子来过。据说儿子儿媳也在北京打工,因租住的地方太小,又每天忙碌不休,他们平日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有。在北京,有多少一年都不会见面的夫妇或者家庭呢?他们所有的打拼,都是为了年底的那一场狂欢。但像小笼包夫妇这样的,其实狂欢也没有多少吧?他们如此沉默寡言,好像每日奔波的蚂蚁,在这个世间所有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忙碌。
不过这样的人生状态,对于高学历的博士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阿路跟老公的见面次数,如果没有孩子作为连接,几乎可以缩减为零。橙子呢,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学期,未曾回家团聚。但我时常羡慕这一对老夫妇,北京城那么喧哗,每天都有各式明星演唱会,讲座,演出,策展,但对于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根本就对北京的一切热闹,漠不关心。而这些,恰恰是女博士们,来到北京,日日追求的。
秋子应该算是我们所有女博士中,活得最为贵族的一个吧。她买来随便戴戴的丝巾,也都是上千元。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在青岛的阳光百货,据说是大使夫人们光顾的贵族商场里,我在上万元的衣服面前,很刘姥姥地一声尖叫,并换来服务生一脸的鄙夷。不过既然来到首都北京,也便长了见识,不会这样毫无修养地一惊一乍。所以看到秋子的名牌衣服,也只是礼貌地给予赞美,并不会因为嫉妒而脸红脖子粗,落人笑柄。
当然,秋子的贵族,不只是徒有其衣。她人长得也好看,是个古典美人,所有衣服,都走杨丽萍似的优雅民族风。见过她的人,很难将女博士三个字,跟她联系起来。而且作为一班之长,她几乎是整个学院博士圈的文化宣传中心,最近有什么娱乐活动,哪个名家大腕来做了讲座,哪个电影好评如潮,甚至包括哪个饭馆里新上了好吃的饭菜,她都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她还是老师的宠儿,链接国内国外专家的桥梁。关于出国关于学术关于电影关于美食关于华衣,只有你不懂的,没有她不知道的。
但是,因为电影学专业,而见过无数明星,也与知名主持人做过搭档的秋子,并未流露出一丝的张扬。与她在一起,只觉得有一种走遍世界、遍览江河的娴静与优雅。她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却是最为纯净的一粒宝石。她的身上,没有阿路那样浓郁的烟火气,和急匆匆行走的戾气。事实上,她从未沾染上婚姻这样的俗气。她只活在爱情之中,并因此有一生不事养育的修女的静寂之美。
很多年以后,秋子果然在我们所有女博士们中,以一种炮制论文的焦虑,匆忙炮制二胎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换掉了男友,与一个高大的美国男人开始热恋,并依然坚持不婚不育的路线。
我想秋子其实是所有女博士们,最想达到的人生至境,活在舞台的焦点,却如小巷里的风,从容不迫,穿梭来去,了无挂碍。她与小笼包夫妇,一个高在云端,一个低在尘埃,却有同样不被喧嚣打扰的宁静灵魂。
秋子不忙的时候,便来我们宿舍里聊天。她会冲两杯咖啡端过来,于是两个人坐在窗前,一边慢慢啜饮着咖啡,一边闲闲说着日常琐碎。哦,我第一次跟秋子学会了如何正确地使用咖啡匙,我原本以为用来优雅搅拌的咖啡匙,是可以像我们乡下人一样,拿来舀咖啡喝的。秋子并没有因为我对高雅礼仪的无知,而流露出嘲笑的表情。她一出生就有优越的家境,出国旅行像我去乡下的亲戚家一样随意自由。但她天生有着接纳并尊重不同文化的修养,所以在我很乡巴佬地像喝茶一样,吹着咖啡热气的时候,她很委婉地向我讲述她第一次喝咖啡的经历,又用学术的思维,分析了西方人喝咖啡的历史及礼仪文化的发展。秋子在说这些的时候,还温柔地将落在我肩头的一根头发掸落下来。阳光穿过窗前风中拂動的垂柳,散落在热气氤氲的咖啡上,我用小勺按九点钟方向搅拌着咖啡,那一小片一小片的阳光,便在其中跳跃起来,连同空气中飘漾的香气,也在这细微的动荡中,摇晃了一下。
那是秋天,小操场上铺了薄薄的一层落叶,叶子是从院墙外飘进来的。夏天的蜗牛已经不知去向,只留下干枯的外壳,跟知了一起,挂在粗糙的石灰墙上。如果不是远远的明光村周围汽车鸣笛的声音,这样闲坐在窗前,看树叶飘落的时光,与古寺闲听钟声的静寂,没有什么区别。
我于是冲秋子笑道:等我老了,就搬去尼姑庵住,每天都是月落乌啼霜满天的美好自然,比做学术好多了。
秋子也笑:不过我倒觉得,真正的隐士,都是在闹市里能够心中有静的人。比如……
比如明光村门口,那一对卖小笼包的夫妇,或者坐在我对面的秋子吧。我抢先一步脱口而出。
说完了,两个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咖啡有些凉了。我知道喝完这一杯,秋子便会跟男友前往高雅的西餐厅,或许欣赏永远会让我昏昏欲睡的交响乐。我则直奔小区门口,要一份能够暖胃的米线,满头大汗地吃完,尔后回来躲进被窝,翻阅诡异的《搜神记》。
至于双胞胎妈妈阿路鸡飞狗跳的人生与婚外爱情,跟我和秋子,或者忙碌一天的小笼包夫妇,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片落叶,永远也惊不醒一只朝冬天走去的蜗牛。
3
开学典礼,博士乐山坐在小马扎上,世外仙人一样,边啜饮着一小瓶娃哈哈AD钙奶,边视线飘忽地仰头看操场上空云朵的画面,大概过去三十年,也不会从我的记忆里消失。对了,他还穿着公园里练习太极拳的大爷们常穿的白色对襟大褂,那衣服肥肥大大的,也或许是他太瘦太仙了,于是整个人便在衣服里四处飘荡着,好像一朵飘荡在天空的无着无落的云;那云还很好奇,时不时地就停下来,探头到烟火味道浓郁的人间张望一会儿,看人类怎样蝇营狗苟地忙碌。
乐山是书法专业的博士,也是某个流派创始人的关门弟子。我不懂书法,有时见乐山写的字,在学院大厅里展览,过去看上一会儿,瞅半天也认不出几个。但是却觉得练书法的,非得是乐山这样不声不响游来荡去的闲人才可。否则人都飘逸不起来,赖在人间拼命地四处跑场子挣钱,这里一笔,那里一勾,怕书法也跟着俗了,拖着一袋子黄金珠宝一样,灵动不得,也飞升不得,活活累死在人间。
乐山是学院的元老级学生,本硕博都在同一个校园里晃来荡去。我怀疑他是学院门口一株盘根错节的梧桐,谁也赶不走他,更别想将他拔掉。他的根系足够发达,已与那些古老建筑、知名雕塑一起,成为校园的一个部分。我那时还猜想他会毕业后留在这个大学教书,后来这一伟大猜想,果真得以实现。于是,一辈子长在同一个校园的乐山,便成了我们奔赴北京时的根据地,只要北京城还在,乐山也便不会离开。如果北京城不在了呢?乐山也还是在,他要跟这里的泥土啊、尘埃啊、大地啊,化为一体。
学院的顶楼是书法系的教室,两张很大的木桌拼在一起,上面只有一支笔,一个砚台,和一沓厚厚的宣纸。书架上的书,也是很仙的颜体柳体或者王羲之之类。空荡荡的桌子上摆着一盆飘逸的文竹,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我怀疑在这样的教室里,长久地待着画画或者研磨写字,人会成为《搜神记》里的神仙,或者化身一只知了,趴在书桌上,悄无声息地就蜕了壳,尔后一展翼翅,冲上云霄。
乐山有一颗童心,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这样认为。他一心沉浸在书法和绘画中,好像沉浸在游戏中的孩子,乐此不疲;外面的天光是怎样的,人群如何喧哗,似乎都与他无关。他只是明光村墙壁上的蜗牛,慢慢地朝着树叶漏下的天蓝色爬去,至于何时可以抵达,一起赛跑的兔子又怎样超越了他,于他,根本无关紧要。
那时大家除了学术论文,都在利用博士身份和人际资源,去校外代课,写剧本,做策展,当主持,挣取外快。乐山出身优越,不用为了谋生东奔西跑,但他却因写字绘画的天赋,和流派传人的声誉,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外快可挣。单凭这一点,就足以羡煞我们这些急功近利的俗人。于是每次我急匆匆从教室出来,赶着去见某个出版社的编辑,总会碰到乐山慢悠悠从学院对面的小花园里走过来,那气定神闲的样子,让我怀疑他刚刚在旁边假山上打完一场黄昏的太极。
我于是冲乐山打招呼,问他最近在忙什么?
乐山则孩子似的咧嘴笑道:练字呗!
我问橙子:乐山十年如一日地在校园里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他就没有烦过吗?
橙子与乐山是研究生时的同学,常常有看着他长大的错觉。不,在她眼里,乐山根本就没有长大过,母校像一个安全结实的蚕茧,他隐匿在其中,安静地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雨声,挥毫泼墨,写下一行行潇洒俊逸的诗句。有一类人,生下来就不再长大,即便读到了博士,再留校做了大学老师,他还是有一颗远离喧哗成人世界的心。他拒绝长大,也被时间善意地挽留下来。
学院每个专业的老师,都能认出乐山那张孩子气的脸。新来的学生,对学校规章制度有什么不明白,去找乐山,也总会得到满意的答复。他说话的时候,慢腾腾的,有些让听的人着急。大多数博士的语速,都是飞快的,好像说话也是一场论文答辩,怕人听不懂“内容摘要”和“关键词”。女博士的语速,比男博士们更胜一筹。以至于每次跟一个女同学聊天,我总是插不上话,心里憋着一肚子火,却发泄不出来。乐山就从不憋着,如果人家话多,他就微笑着不发一言,等人家说完了,他只点点头,回一个“好”,或者“行”。大家提议去聚餐,他也很少表态,我怀疑吃饭这件事,对他来说,也可有可无。乐山究竟在想什么呢,走在或许连蚂蚁都是十年前那一只的校园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乐山也从来不说。好像,他即便做校园里的一只飞虫,一株小草,一朵流云,一片叶子,都无关紧要。他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是闲云野鹤般的存在。他跟谁都不争不抢,却也因这样的态度,在毕业后,得到了我们所孜孜以求的一切世俗荣耀。
跟乐山住在同一宿舍的赵飞,用了三年的时间,也没有学会乐山的一丁点境界。乐山如果是静若处子,赵飞则是动若脱兔。每次从学院出来,总能碰到他骑着一辆快要散架的破旧自行车,从东门心急火燎地闯进来。因为人胖,他浑身上下便蒸腾着热气,好像刚刚从热锅里铲出来的大白馒头。红色背心当然也都湿透了,大裤衩上更是很不文明地现出一片湿地来。这多半是他刚刚从小吃巷里钻出来。吃的什么呢,大抵不是米线、土豆粉,就是鸭血粉丝或麻辣串。他的舍友乐山当然也吃这些东西,但乐山是打坐一样吃上好半天,饭吃完了,汗水也被蒸发走了。赵飞不同,小饭馆做饭的厨师,花了十分钟将炸酱面盛上来,他呼噜呼噜三分钟就能吃个底朝天,而且还会将饭碗边缘也舔得一干二净。
赵飞要将节约下来的时间,去操场上跑步健身,或者去给附近某个培训班代课,幫人做项目枪手。反正只要能挣钱,赵飞是丝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的。他认同时间就是金钱这个真理,每次我们商量去哪儿请导师吃饭,他总是将包袱一巴掌甩给我们,说自己最近忙得很,我们全权代理就可以了,他什么意见也没有。乐山也没意见,但乐山是随遇而安,自在逍遥。赵飞不是,他要忙着将全北京城的钱,都搂到自己兜里来。
于是橙子说:赵飞一没老婆,二没生病爹娘拖累,三不想留在北京受买房买车的罪,他那么忙不迭地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拖家带口的,也没他这样迫切地奔命。
倒是跟他有些相似的阿路,一语道破天机:还不是被一条贱命在后面追赶着!命好的人,这里看看,那里瞅瞅,有的是闲情逸致赏花看月,谁他妈不想慢下来!
阿路这样一说,没有人再敢嘲笑赵飞。包括我自己在内,谁不想做乐山和秋子那样的贵族博士呢?我们这样一路努力考博,拼打到北京城里来,为的不就是能有一份在大学里安稳清闲可以风花雪月的体面工作么?当然,两年后我们流落各省大学,为发表论文、申请课题和晋升职称,而四处卑微求人,自然是后话。
不知道哲学专业的博士,是否研究永恒是什么,或者这个世上究竟有没有永恒。我很想明白一只蜗牛永无休止地在夏日向着天空攀爬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多人,比如小笼包夫妇,蜗居在北京城的地下室里,多年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又是为了什么?离了婚的女博士阿路,因无法将婚外情变成名正言顺的婚姻,反而比过去更为焦灼,她拖着双胞胎女儿的负累,左冲右突地活着,有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她获得一丝宁静?混到三十岁还没有女朋友的赵飞呢,他忙忙碌碌地奔波在这个世上,在与甜蜜情侣擦肩而过的时候,有没有过厌倦?我们想象中有着完美人生的秋子与乐山,他们在独处的时候,又会不会露出身后不为人知的阴影?学术研究与人生幸福的关系又是什么,如果关系不大,我们从四面八方奔赴到北京城来,又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谋生吗?可是谋生是多么喧哗枯燥的一件事啊!
后来有一天,我在校园的假山上读书。假山旁边的篮球场,曾是徐静蕾拍摄某部电影的外景地。那里的确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闪烁的光华。当然,这种洋溢的激情,与我们博士已经没有太多关系。更多的时候,我是在欣赏这种有距离的美,并暂时地忘记自己的年龄。而捧一本书在假山上读,当然有冒充青春年少的嫌疑。但我实在喜欢这一小片树林,这里植满了槐树、柳树、竹子等所有容易让人有鬼魅联想的树木,人沿着不规则的山路,朝幽深僻静的高处攀登,会有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的错觉。
我在那个清幽的世界里,遇到过什么呢?大多数时候,是耳鬓厮磨的情侣。有时也会碰到学霸,旁若无人地朗诵英语。老年人是很少的,他们自觉地退出了这一片浪漫的天地。除此之外,便很难想象,这里会发生任何破坏如此湿润氛围的故事。
那天黄昏,我看到一对情侣借着昏暗树荫的遮掩,发出婴儿吸吮乳汁一样心满意足的亲吻。我几乎带着偷窥的欲望,用余光注视着他们的双手,怎样在对方的身体上试探游移。我期待他们继续下去,不要停止,我的身体里,甚至燃烧起一种隐秘的快乐。我在心里说,不要停下,继续……
可是,忽然从树的背后,冲出一个瘦弱的男孩来。他在情侣包括我还没有注意到的瞬间,以闪电般的速度,亲吻了女孩微微扬起的闪烁着美好光泽的脸颊。尔后,又在所有人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冲下山路去。
我出了一身冷汗。那对情侣,也被惊吓在了原地。许久,女孩才嘤嘤哭了起来。而男孩则勇敢地拥抱住女孩,我看见他的后背,在轻微地颤抖。
我被惊恐驱赶下山。那个偷袭女孩的男孩,早已不知去向。不过也或许,他正隐匿在附近的某个角落,窥视着暗夜中发生的一切。
我在夏日的风里走了许久,最后忍不住笑了起来。我想那个偷袭女孩的男孩,在他的身体里,一定有一种东西,在骚动、酝酿,直到某一天,以这样的方式爆炸。或许,这只是他的一个恶作剧;或许,他暗恋了女孩很久,也跟踪了她很久,却始终不能找到机会。对于他,这一个瞬间结束的亲吻,不亚于一次原子弹爆炸,也必将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无法祛除核辐射的侵害。
可是,一切都发生了。
我目睹了一场青春的爆炸,在与青春完全无关的博士“高龄”,在与充满烟火气息的明光村,相距不过百米的校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