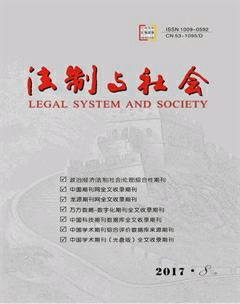辱骂型寻衅滋事对罪刑均衡原则的破坏
摘 要 辱骂型寻衅滋事罪重于侮辱罪的法定刑与其本应轻于侮辱罪的社会危害性相矛盾,违背了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则。这是因为寻衅滋事罪具有“补充性”和“随意性”特征,“辱骂他人”的行为方式亦为侮辱罪所包容。刑法所称“破坏社会秩序”在本类型寻衅滋事罪中体现为对个人名誉的侵犯,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扩大解读的可能性,产生处罚“不当罚”行为的风险,亦是对罪刑均衡原则的破坏。
关键词 辱骂型 寻衅滋事 侮辱罪 罪刑均衡原则
作者简介:杨申,四川警察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法理学、法制史。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8.268
我國《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以其行为模式类型的多样性著名。根据条文表述一般可将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分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和“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四大类型。其中第二项所称“追逐、拦截、辱骂、恐吓”四种行为,由于“无需具备所有行为即可成立本罪”的“选择性”特征,亦可划分为不同行为类型的寻衅滋事罪。如“两高”在2013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1款称:“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该条款排除在网络领域不可能实现的“追逐、拦截”,单独列举“辱骂、恐吓”,事实上等同于认可了将“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作为并列关系的法律解释方法,肯定了“辱骂型”寻衅滋事的存在。由于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纠集他人多次实施”情节可达“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与辱骂型寻衅滋事具有竞合关系的侮辱罪,在《刑法》第246条的规定中法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据此辱骂型寻衅滋事在实践中常常作为侮辱罪的“升格”罪名而存在。
然而辱骂型寻衅滋事的社会危害性是否真的大于侮辱罪,显然不能仅仅因法定刑的高低得出结论。事实上,如果按照刑法所描述的犯罪构成对其进行体系化的解读,只能得出辱骂型寻衅滋事的社会危害性轻于侮辱罪的结论。因而,由辱骂型寻衅滋事所引起的,法定刑轻重与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不一致,是对刑法整体罪刑结构即罪刑均衡原则造成的破坏。传统观点从“破坏社会秩序”角度对辱骂型寻衅滋事畸重的法定刑进行的解释,不仅在寻衅滋事罪保护法益方面存在矛盾,而且可能引发处罚“不当罚”情形的风险,亦是对罪刑均衡原则的破坏。
一、辱骂型寻衅滋事与侮辱罪罪刑轻重关系的错位
辱骂型寻衅滋事的社会危害性轻于侮辱罪,是由寻衅滋事罪名的补充性决定的。就犯罪构成而言,“辱骂”作为一种言辞侮辱行为,亦没有社会危害性明显高于其他侮辱方式的可靠根据。而寻衅滋事本身具备的“随意性”特征,则进一步证明了辱骂型寻衅滋事的社会危害性往往小于侮辱罪的事实。
当今学者一般将寻衅滋事定位为补充性罪名,作为其他几种具体犯罪形式的补充。进而有学者指出,由于一些行为在表面上虽然并不符合故意伤害罪、侮辱罪、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其反复性往往导致法益的严重侵犯,“倘若不以犯罪论处,则既不利于保护法益,也导致处罚的不均衡。” 进而有学者提出了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相关罪名的竞合处理模式,即“凡是符合特别条款规定之罪的犯罪构成的,就按特别条款规定之罪定罪处罚;只有在既达不到特别条款规定之罪的犯罪构成标准但是又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才按照堵截性罪名或堵截性条款定罪处罚。” 学界亦称其为“兜底性”罪名。据此,殴打和追逐、拦截行为是故意伤害罪的补充,恐吓行为是敲诈勒索罪的补充,强拿硬要是抢劫罪的补充等。寻衅滋事罪的设立初衷就是将某些游离于重点罪名边缘的危险行为纳入刑法评价范围,并使之与邻近重罪呈梯级衔接关系,以形成罪刑均衡体系。因此,辱骂型寻衅滋事亦应作为侮辱罪的补充,并不得高于侮辱罪的法定刑。补充性罪名的法定刑不应当高于被补充的罪名,否则以重罪为轻罪“兜底”,被“补充”的罪名反而失去存在的意义,也就破坏了刑法的罪刑轻重体系。
根据刑法对犯罪构成的描述,辱骂型寻衅滋事显然是轻于侮辱罪的犯罪形式。具体而言,“辱骂”属于一种非常具体的行为方式,而“侮辱”则可能包含多种旨在降低被害人社会评价的行为。《刑法》第246条规定,侮辱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一般认为,“暴力方法”是指“为使他人人格尊严遭受损害而采取的强制手段,而非直接对被害人人身实施殴打、伤害”;而“其他方法”则通常主要是“以文字或语言的方式损害他人人格、名誉。” 据此,侮辱行为实际上包含了“暴力侮辱”和“其他方法侮辱”两种行为模式,而其中的“其他方法侮辱”又可以包括“文字侮辱”和“语言侮辱”两个类型。“辱骂”指的是“用粗野或带恶意的话侮辱他人”,应当属于“语言侮辱”中表达方式相对激烈的一种。一般而言,具有实害暴力倾向的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往往重于非暴力行为;形成书面文字的侮辱手段也应当比单纯口头侮辱行为表现出犯罪者更强的犯罪意志。因此,辱骂行为在多种侮辱行为方式中并不突出,也没有为其专门设置“升格”法定刑的必要性。
最后,辱骂型寻衅滋事与侮辱罪最大的区别应属寻衅滋事行为的“随意性”,这正是辱骂型寻衅滋事的社会危害性轻于侮辱罪的最好证明。所谓“随意性”,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通过实行行为的“无因性”和选择行为对象时的“非特定性”两个方面予以认定。其中“无因性”是指寻衅滋事行为一般都是“事出无因”的,而对“事出有因”的侵犯身体权行为则将按故意伤害、抢劫、敲诈勒索等特定罪名论处。同时,“事出有因”的“因”应缩小解释为“一般人认为合理的理由”,否则任何故意犯罪行为都一定是有原因的。 “两高”在2013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称之为“无事生非”,并描述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情形,同时指出“无事生非”应当包括“借故生非”,但不包括“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的相关行为定性为寻衅滋事。另一方面,判断“随意性”往往还要求行为对象的“非特定性”。也就是“把被害人置换为另一个社会正常人,在同样的环境里该人实施同样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仍会殴打则是随意,如果不会则不是。” 鉴于寻衅滋事罪源于旧刑法中的“流氓罪”,因而仍有观点将“流氓动机”作为该罪名的主观特征。但由于所谓“流氓动机”或“寻求精神刺激”含义模糊,难以为司法实践所把握,继而遭到了学界的批判。 事实上新的罪行表述之中既无“流氓”之类的语词,也找不到任何“寻求精神刺激”的文本依据,过分强调寻衅滋事罪对流氓罪的继承,进而为该罪名强加所谓的“流氓动机”,已不存在现行有效的条文依据。“随意性”特征表明寻衅滋事类犯罪在实施目标、手段选择、被害人特定等方面,缺乏明确的犯罪预谋和实施方案,也就是其主观有责性方面往往欠缺坚定的犯罪意志,因而其客观社会危害性也相应的有所减轻。
罪行均衡原则在立法层面上要求罪名对应法定刑的轻重应当与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应,所谓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应当根据犯罪构成具体判断,而“轻重”、“大小”之别则是相对的。作为“寻衅滋事”的“辱骂他人”行为,因为并不具有明显高于侮辱罪的社会危害性,其相对过高的法定刑显然是对罪刑均衡原则的破坏。
二、“破坏社会秩序”存在引发处罚“不当罚”行为风险的错误解读方法
根据《刑法》第293条规定,寻衅滋事是“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但对“社会秩序”的理解必须与行为类型所侵犯的具體法益相结合。特别是作为言论类犯罪的辱骂型寻衅滋事,如果抽象理解“破坏社会秩序”,极易造成超越罪刑法定处罚“不当罚”行为的风险,破坏实质上的罪刑均衡。
坚持认为辱骂型寻衅滋事的社会危害性大于侮辱罪的观点,主要着眼于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然而“社会秩序”属于抽象法益,刑法分则所要保护的法益应当是具体法益,否则“保护法益的抽象程度越高,所包含的内容就越宽泛,刑罚处罚的范围就越广,而具有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解释为犯罪的危险。”因此,就辱骂型寻衅滋事而言,其保护法益就是“他人的名誉”。 由于自然人的名誉权作为“社会对个人的评价”,其本身属于社会秩序或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认为社会秩序是寻衅滋事的一般犯罪客体,而自然人的名誉,或称“人格权”就是辱骂行为具体所侵犯的特殊客体。 辱骂型寻衅滋事正是通过侵犯自然人的名誉权,进而破坏社会秩序的。由于刑法所称“辱骂他人”其行为对象只能是自然人,鉴于“追逐、拦截”均不属于能够对“法人”、“单位”、“其他组织”或“特定社会群体”实施的行为,因而辱骂型寻衅滋事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就只能通过侵犯自然人的名誉体现出来。
据此,辱骂型寻衅滋事所保护的法益和“公然侮辱他人”本质上是一致的。前者强调了侮辱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后者则不以实行行为的社会环境为限,强调结果上造成了受害人名誉的贬损,即达到相对“公然”的程度。实际上,很难想象单纯的辱骂行为如何造成相当程度的公共秩序损害。言论型侮辱罪与辱骂型寻衅滋事都发生在公共空间,都有引发围观的属性;但将前者的公共秩序问题忽略不计,转而特别强调后者的“破坏社会秩序”,显然仅仅是因为辱骂型寻衅滋事主观上出于无事生非,客观上随意的针对不特定人,因而其行为由相对的个人关系转入公共关系,从而构成对公共秩序的侵害。而这里的“公共秩序”不在于“围观”及其后果,仅在于辱骂因对象“不特定”可能导致的“多人”指向。针对“多人”的损害,其核心还是名誉权。在针对“公共”的犯罪中,多人名誉权的叠加是否能比之于多个生命权的叠加?以破坏交通工具罪为例,其实行行为威胁多人安全可能变为现实性;辱骂行为却很难同时对多人发力,其实行行为威胁多人名誉权的可能性很难变为现实性。生命、健康、财产损失可以叠加计量;名誉损害大小则不能以人数计算。因此,若果辱骂型寻衅滋事因危及“不特定多人”、“破坏社会秩序”而入罪,其对“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破坏——多人的名誉——与侮辱罪的“情节严重”在损害程度上实难相比。
然而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忽视辱骂性寻衅滋事侵犯个人名誉权的前提,机械理解“破坏社会秩序”,造成该类型犯罪打击范围的不当扩大。因为“辱骂他人”属于一种言论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该言论的解读。而“破坏社会秩序”的说法范围过于宽泛,可以说任何一种不文明的言论,如果上纲上线的理解,都可能解读出“破坏社会秩序”的内容。据此,《刑法》第246条将侮辱罪和诽谤罪规定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公民人身及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维护的微妙平衡。法律将言论犯罪危害程度的判断交由受害人把握,如果受害人认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就不应当认为是犯罪。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仍能够通过对“破坏社会秩序”的解读,以该行为侵犯个人名誉之外的其他法益为由,按辱骂型寻衅滋事追究其刑事责任。姑且不论其他法益受侵害的程度如何判断,犯罪构成中客体的含混性本身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仍可依《刑法》第13条但书否定行为人的犯罪事实,但这种全凭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出罪方式并不可靠。况且对言论行为实施刑事追诉的过程,本身就足以造成行为人人身自由受到侵害、司法资源遭到浪费以及社会公众对“因言获刑”事件的恐慌。而这种司法追诉方式如果被某些地方部门加以利用,很容易成为打压公众舆论的手段,进而损害司法权威和民主氛围。
质言之,对“破坏社会秩序”的错误理解,会产生将道德上的不文明行为作犯罪处理的可能性,破坏罪与非罪的界限,导致罪刑均衡原则的失衡。
注释:
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上篇).政治与法律.2008(1).
杜启新.论寻衅滋事罪的合理定位.政治与法律.2004(2).
王作富.刑法分则事务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980.
关振海:规范与政策: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二重区分.国家检察官学院报.2012(1).
何庆仁.寻衅滋事罪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4).
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下篇).政治与法律.2008(2).
陈兴良.寻衅滋事罪的法教义学形象:以起哄闹事为中心展开.中国法学.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