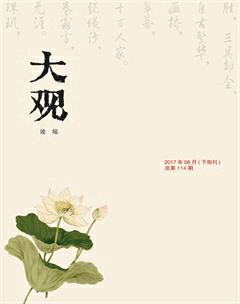《史记》与《汉书》人物评价异同个案分析
王晓晖
摘要:《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者各有侧重,均在文学史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记》与《汉书》均以写人艺术见长,人物传记中都表现出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但是,受司马迁、班固二人治史的时代环境、个人经历和史观笔法等因素的制约,二书在人物评价方面迥然不同。本文从《史记》与《汉书》中五十五篇重叠篇目中选取《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以汉高祖刘邦为个例,通过比较研究二者对刘邦人物评价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而从一定程度上窥探《史记》与《汉书》人物评价的整体异同。
关键词:《史记》;《汉书》;人物评价;汉高祖刘邦;史汉异同
自《史记》《汉书》问世以来,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为其注解、补充、研究、探索,至今仍然经久不衰。与此同时,从《汉书》诞生之日起,史汉异同的问题就应运而生。由于两部著作地位特殊,两位作者也贡献卓著,对《史记》与《汉书》、司马迁与班固优劣伯仲的诸多问题的对比研究就一直备受瞩目,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千百年来百家争鸣,热议不断。
一、选题依据
从现存的历代各类文献中,人们不难发现,《史记》是公认的纪传体史书的鼻祖,《汉书》则是开断代体史书之先河,如此看来,史汉二书,可以被视为古今史书之首。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一般认为,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最杰出的作品,前四史中,《史记》和《汉书》又是最杰出的作品。《史记》被近代作家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南朝宋范晔在《后汉书》中提到《汉书》是这样描述:“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但是,在对《史记》和《汉书》的对比研究中,孰优孰劣就难分伯仲,不能统一了。
自古以来,研究史汉异同的学者,多数是从二书的整体出发,站在宏观的角度,通过异同之处的对比、考证,再结合司马迁和班固二人时代背景、生活经历、写作宗旨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差异,探究文学、史学的发展变化和其反映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主要影响。这种整体性的对比研究著作颇多,成果丰硕,但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针对性。笔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研究重点放在《史记》和《汉书》的重要篇章和重点人物,把关键语句并列呈现,逐一对照,考证异同,探究原因,力求在全面的、客观的研究背景下为日后的研究提供更加具体而详实的依据。
本文选取《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两篇文章,以汉高祖刘邦这一典型人物为切入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比较研究。原因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因为两篇文章都是史汉二书中的经典篇目,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学史和史学史研究价值,二是因为汉高祖刘邦作为历史上具有极大争议的重要人物,从司马迁开始,时至今日仍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無论是他的个性特征还是治国方略,前人都有着广泛的涉猎。本文以刘邦为核心人物,从《高祖本纪》和《高帝纪》中发掘关键语句进行对比研究,以期发现问题,求证史实,分析原因,补缺拾遗。
二、异同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对刘邦人物评价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刘邦个人本纪在二书目录中的位次
1.《高祖本纪》在《史记》目录中的位次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其中,十二卷本纪依次为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秦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太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孝武本纪第十二。由此可见,刘邦的个人本纪位列所有本纪的第八位,更值得深思的是,司马迁将本朝的开国皇帝排在了项羽之后。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时候更崇尚秉笔直书,遵照事实就事论事。他认为项羽领导各路诸侯与秦军作战,是灭秦的最大功臣,即便是秦国灭亡以后,项羽也掌握了多数的天下军政大权,所以将项羽列入本纪,地位等同于帝王,且按照时间顺序,排在汉高祖刘邦之前。然而,由于司马迁是汉家臣子,编写《史记》时定会有所顾忌,所以将项羽本纪区别于其他帝王,用本名来命名,内容也以汉代年号来纪年,在笔者看来,这不失为一种隐晦的手法,向汉朝王室妥协。
2.《高帝纪》在《汉书》目录中的位次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其中,纪共分为十二卷,分别是卷一 上 高帝纪 第一上(汉高祖刘邦)、卷一 下 高帝纪 第一下(汉高祖刘邦)、卷二 惠帝纪 第二(汉惠帝刘盈)、卷三 高后纪 第三(汉高后吕雉,汉少帝刘恭,汉少帝刘弘)、卷四 文帝纪 第四(汉文帝刘恒)、卷五 景帝纪 第五(汉景帝刘启)、卷六 武帝纪 第六(汉武帝刘彻)、卷七 昭帝纪 第七(汉昭帝刘弗陵)、卷八 宣帝纪 第八(汉宣帝刘询)、卷九 元帝纪 第九(汉元帝刘奭)、卷十 成帝纪 第十(汉成帝刘骜)、卷十一 哀帝纪 第十一(汉哀帝刘欣)、卷十二 平帝纪 第十二(汉平帝刘衎)。由此可见,刘邦的个人本纪位列所有本纪第一位,且因篇幅过长,分上下两部分著述。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因为《汉书》本身就是一部断代史,不同于《史记》的编年体记事,更重要的原因是,班固认为,汉代的历史,应以汉高帝刘邦为开端,所以要把他列于首席的位置。至于上文笔者提到的项羽,班固仅仅把他置于列传之中,书中也多次强调先入关者称王这一概念,从而把刘邦视为灭秦的最大功臣。
(二)关于诸侯入关的相关问题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当是时,秦兵彊,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彊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彊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成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魏)[秦]二军。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史记·高祖本纪》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
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羽怨秦破项梁,奋势,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悍祸贼,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秦宽大长者。”卒不许羽,而遣沛公西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城阳与杠里,攻秦军壁,破其二军。”——《汉书·高帝纪》
以上两段文字是马班二人对诸侯入关这一相同事件的不同表述,可以看到有几处明显的区别。一是《高帝纪》将《高祖本纪》中的“令沛公西略地入关”几个字全部删去,仅以一个“初”字代替。二是在谈到战果时,将“楚军出兵击王离”一句删去,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淡化楚军作用的做法。当时,楚怀王仅仅是楚国的国家元首,而不是各路诸侯的统帅,地位上不能和起兵造反的陈胜相提并论,因此,由怀王与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威性,其次,令沛公一人“西入关”,对于同时相约伐秦的其他诸侯来说,是不是有失公允?说到战果,竟有意将楚军的作用忽视,是不是有些刻意?
《汉书》中的这两处删改,看似轻微,实际上是对诸侯入关后秦国最终被谁灭亡这一问题的一种掩饰。对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就表述地更为公正客观,他在《项羽本纪》提到:“项羽由是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这里的诸侯,应该是包括当时的沛公刘邦的。也就是说,诸侯入关,是项羽带领诸侯,最终消灭了秦国。
(三)垓下之战的相关问题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谷城。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 ——《史记·高祖本纪》
“十二月,围羽垓下。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 ——《汉书·高帝纪》
以上两段文字是马班二人对垓下之战这一事件的不同描写,比起在诸侯入关问题上个别语句的差异,二人对垓下之战的描写在篇幅上就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在《史记》中,楚汉垓下之战,是一个重大事件,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将其描写的详尽而宏大,在《高祖本纪》中,也有着两百多字的详细记载。消灭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为最终称帝奠定最总要基础的一次战争,在《汉书》中却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不得不让人深思。笔者看来,班固在此处这样安排的愿意无非是因为曾企图谋反的韩信。细读司马迁笔下的垓下之战,从“将三十万自当之”,到“侯复乘之,大败垓下”,明明白白地指出,垓下之战得以取胜的最大功臣正是淮阴侯,也就是韩信。对于这次战争,司马迁还写道:“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说明韩信“四面楚歌”的计策,使项羽产生了“汉尽得楚地”的错觉,所以说是“以为”,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如此,以凸显张良杰出的军事才能。到了《漢书》,班固直接把“以为汉尽得楚地”改为“知尽得楚地”,把项羽的一种错觉改写成了一个事实,不能不说是对这段历史的有意掩盖。
(四)其他篇目中与刘邦相关的问题
1.立楚怀王的相关问题
“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史记·项羽本纪》
“六月,沛公如薛,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 ——《汉书·高帝纪》
以上两段文字是马班对立楚怀王这一问题的不同表述。司马迁通过详细讲述前因后果,清楚地告诉读者,楚怀王孙心是项梁所立,当时的沛公只是项梁召集计事的诸侯之一。同一件事,到了班固笔下,就无视其原有,变为沛公“与项王共立”,而且把沛公排到项梁之前,从一个应召参会的诸侯,上升到与项梁平起平坐的地位。
2.鸿门宴的相关问题
在《史记》中,《项羽本纪》是写的极为精彩的篇章之一,其中,鸿门宴的座次历来为人称道。“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和分析,这样的座次,对于刘邦来说,显示出了他当时地位和身份的卑微。把《汉书》中的相关情节与之对比后,不难发现,班固改写的较为简单,如樊哙事语在《汉书·樊哙传》中就写得比较详细。班固更是将鸿门宴的过程极尽简化,将司马迁原文一千余字缩为四百余字,显得十分寡淡无味,人物对话也未能保留,使得人物失去了原本的生动性,很难表现出当时在座的人物之间内心暗潮汹涌的角力。关于鸿门宴的座次,班固更是将其直接删除,在笔者看来,也许是试图刘邦当时地位的卑微。
三、结语
在对史汉二书中关于刘邦的人物评价的对比研究后,笔者认为,班固在编写《汉书》的时候,以《史记》为蓝本,着力对司马迁对于刘邦这一人物的直面描写进行了不少后期加工,包括删除了大量涉及其负面形象的语句,提升其在各种重大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以至于替代他人的重要性,对于人物评价来说,不仅不够鲜活生动,更是不够严谨客观。由此可见,司马迁和班固二人对待汉高祖刘邦这一人物是有不同的评价的。对于刘邦的最大竞争对手——项羽,司马迁在《项羽本纪》及其他传记中进行了全面而不失公允的刻画,故在《高祖本纪》中相对减少。班固对此进行了补充,把《史记·项羽本纪》中诸如鸿门宴、彭城之战、陈平间楚、垓下之战等,移入《汉书·高帝纪》中,为的是在人物评价上,将汉高祖刘邦塑造成一个居功至伟,丰满鲜活的开国皇帝的形象。与司马迁相比,班固这样进行人物评价固然有失公允,特别是对于项羽、韩信等人物。但是,作为一部官方断代史书,班固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个中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深究。
总而言之,《史记》和《汉书》都是伟大的历史巨著,司马迁和班固对文学和史学的贡献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笔者仅以此文表达一点拙见,希望见微知著,拾遗补缺,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冯鑫.《史记·高祖本纪》与《汉书·高帝纪》比较研究——马班异同个案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0.
[2]冯家鸿.论司马迁和班固之孰优——《史记》、《汉书》同篇目比较评述[J].金陵职业大学学报,2000(04):26-32.
[3]刘德杰.《史记》《汉书》人物个性比较[J].河南社会科学,2007(02):114-116.
[4]赵东栓.班固的人格审美意识与《汉书》人物形象[J].绥化师专学报,1992(01):1- 6.
[5]尉永兵.《汉书》写人艺术研究[D].山东大学,2014:3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