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人类
D. T. 马克斯


人类特征的演变这些符号(上)连缀全篇,分别描绘了人类进化历程中文化、生物学意义上的里程碑。
我在巴塞罗那见到“赛博格”——半人半机械的科幻混合体——尼尔 ·哈比森的时候,他看起来跟当地的其他另类潮男没什么不同,只除了一样:从脑后翘起、绕过他的金色锅盖头发型伸到前面的黑色天线。
这是在去年12月,34岁的哈比森穿一件灰色拉链衬衫,外面是厚呢短大衣加灰色窄腿裤。他生于英国贝尔法斯特,长于西班牙,患有一种名为全色盲的罕见病症,完全感知不到颜色。但这条终止于眉间、末端带着光纤传感器的天线,打破了他的感官局限。
哈比森以前从未觉得生活在黑白世界里算是一种残疾。“我的视力能看到比常人更远的地方。而且我能更轻易地记住图形,因为不会被色彩分散注意力。”他用一口平和的英伦腔告诉我。
但他仍满怀好奇地想知道彩色的事物是什么样。他是学音乐的,十八九岁的时候曾有过一个点子,想通过声音来发现色彩。经历过数次技术不达标的失败尝试后,他在二十来岁时找到一位外科医生(至今拒绝透露姓名),后者愿意为他植入一个电脑装置,“升级”他的肉身。
光纤传感器采集他眼前的色彩信号,再由植入头骨的一块微芯片把信号频率转化成脑后的震动。震动产生了音频,在某种程度上把他的头骨变成了第三只耳朵。他准确地认出我的外套是蓝色,然后把天线对准旁边的赛博格艺术家、舞蹈家朋友穆恩·里瓦斯,说她的夹克是黄色——严格说其实是芥末黄,但他解释说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长大,“我们打小就没见过芥末”。
我问哈比森,医生是怎么把这个装置安到他头上的,他爽快地扒开脑后的头发,给我看天线的接入口。一块带有两个锚点的长方形盖板压在粉红的皮肉上,与天线相连的植入体装载着震动微芯片,还有一个植入体是蓝牙通讯集线器,这样朋友们就能通过手机发送色彩给他。
这根天线对哈比森产生了天启般的意义,使他感受到的世界更加激动人心。他说,随着时间推移,传感器的输入开始变得既不像视觉也不像听觉,而是近似一种第六感。
但最诱人的地方在于,天线赋予他一种我们这些常人不具备的能力。他看看屋顶平台上的灯具,能察觉到控制感应开关的红外光的明灭;他扫一眼盆栽中的植物,能“看到”显示花蜜在花朵中位置的紫外线标记。他不仅仅补上了常人的感受能力,还超越了它们。
所以,他就成了人类迈向未来主义者一直以来的远大目标的第一步,即畅销书《奇点已近》的作者雷·库日韦尔所说“人类潜力之广大扩展”的一个早期实例。哈比森本人并无意为库日韦尔的梦想打头阵——他热爱自然多过醉心科技。但既然他已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官方承认的赛博格(办护照时,他说服英国政府人员让他戴着天线照相,辩称它不是一件电子设施而是他大脑的附属物),也就同时成了一把召唤变革的火炬。朋友里瓦斯很快跟上了他的脚步,成为所谓“跨人类主义”流派的一员:她在上臂内植入了一个震动磁体,与手机上的地震波监测软件相连。她通过手机获得实时地震报告时,就能切身感受到与大地运动的连接,并通过舞蹈将之诠释出来。“大概是因为我看到他之后觉得眼红吧。”她说。

12500年前
进化出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体质
直到不久前,科学家还认为我们这个物种早在远古已经停止进化。然而当我们有了深入窥探人类基因组的能力,就发现人们的生物学特征其实一直在改变,以适应特殊环境。大多数人登上高山后都觉得喘不过气,因为我们的肺必須奋力运作才能吸纳变得稀薄的氧气。但安第斯人拥有一种基因决定的体质,使他们的血红蛋白能够结合更多的氧。藏族人、埃塞俄比亚人也各自适应了所处的高海拔环境,说明自然选择机制能带领我们从不同路线获得同样的结果:生存。

8000年前
适应沙漠气候
沙漠对于萨赫尔(曾把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塔斯马尼亚连为一体的史前大陆)居民而言构成了进化上的挑战。现代澳洲土著的祖先约于5万年前进入萨赫尔,之后他们便发展出了适应性,得以在夜间降至冰点以下、白昼常高过37℃的气候中生存。这一生存优势(尤其是对于婴幼儿)源于一种代谢调节激素的基因编码中发生的突变,能调节体温上升时产生的多余热量。
“我们将超越自身的全部生物学局限。”库日韦尔断言,“这就是身为人类的意义所在——扩展我们的存在形式。”
哈比森的天线显然只是一个开始。但我们真的即将重新定义自身的进化方式吗?“进化”从今以后将不仅意味着散播优势基因的磨磨蹭蹭的自然选择,还意味着我们扩展自身能力以及产品能力——结合基因、文化、科技——的一切手段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将去向何处呢?

直立行走我们的远祖之所以适应了用两腿行走,可能是为了高效地远足,以发现新的食物种类。

制造工具这是人类最早产生的文化适应性之一,使我们的食物构成得以扩展。营养改善之后,我们就能发展出更大、更复杂的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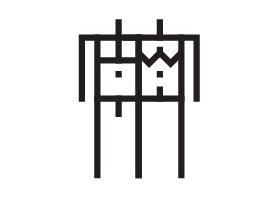
毛发消减早期人类发展出没有厚实毛发的皮肤,可能是为了在热带草原保持清凉,并使得体表寄生虫更容易暴露。
常规进化机制在我们这个物种中仍是活跃而健全的。人类细胞中为蛋白质合成提供编码的基因约有2万个,不久前我们还只知道其中极少数的构造,如今已经知晓约1.2万个基因的功能。但基因还只占我们全部DNA的一小部分,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突破性的发现——而且来得很快。在这遗传信息的宝库中,研究者已找出几十个发生于相对晚近时期的进化实例。从解剖学特征来看,现代人类于5万~8万年前的某时走出非洲,向外迁徙。我们最初的基因遗产适用于温暖气候——从类人远祖到人类,从指节拄地行走的猿类到狩猎-采集部落,进化过程就是在这样的气候中完成的。但在那以后发生了许多事,随着人类向全世界扩张,面对新挑战需要有新的能力,我们的基因构成因此而改变。
这一过程不乏晚近的真实案例。在沙漠气候中生活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拥有一个基因变异,是过去1万年间发展出来的,使他们更容易适应极端高温。史前时代,大多数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只在幼年期能消化乳汁——有些基因负责在我们断奶时停止有关消化酶的产生。但大约9000年前,有些人类开始畜牧动物而不再单纯依靠狩猎,于是这些牧人的基因发生改变,使身体能够终生合成奶类消化酶,如此可以方便地摄取家畜生产的高营养饮品。
在近期发表于《科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古人类学家约翰·霍克斯写道,这个消化类基因在世上散播的速度令他赞叹:“每经过一代人可扩增多达10%。它带来了巨大优势,可能是晚近出现的人类特征中最强大的一个。”
肤色的演变与之相似。如今非裔人种之外的一切族群,其祖先当初也都是带着黑皮肤走出非洲的。研究者说,即便是区区1万年前,欧洲人和非洲人的肤色看起来也差不多。但又过了些年,在光照较弱的北方气候区,人类演变出较浅的肤色,这样有助于吸收阳光中的紫外线,在体内更高效地合成维生素D。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拥有一种适应性,对鱼肉中Ω-3脂肪酸的消化能力远高于我们其他人。阿根廷城市圣安东尼奥-德洛斯科夫雷斯附近的一支原住民,已进化到能饮用天然含有高浓度砷的地下水而安然无恙。
进化是不会终止的,只要可以增加主体的生存机会,它就会千方百计做出改变——有时还会采用几个不用版本。比如,有些中东族群消化牛奶的基因变异就与欧洲人的不同。在非洲人中,有五六个差异明确的抗疟疾基因型并存,其中一个具有明显的短处:如果孩子从父母双方都继承了这个变异,就会患上镰刀细胞贫血症。过去50年中,研究者在安第斯人、埃塞俄比亚人、藏族人中发现了多种多样的基因型,都能帮助各自的族群在高海拔地区高效呼吸:安第斯人群保持着较高的血氧浓度,而藏族人中有证据表明他们经过与丹尼索瓦人(人类世系中一个神秘的分支,数万年前已灭绝)通婚而引入了一个基因。这些适应性,使得居于高海拔地带的土著获得了相对于因缺氧而头晕气喘的外来者的优势。

面红耳赤伴随尴尬、局促感的脸红可以流露悔悟心理,在社会群体中有助于取得同辈的谅解。

动情落泪哭泣表达内心的脆弱,增加获得帮助的机会,并进而强化群体中的社会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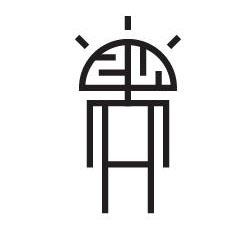
腦量增大随着人类结成更大的社群,趋于复杂的交流、办事行为促使人脑发育得更大。
查尔斯·达尔文早年在《物种起源》中大张旗鼓地叫阵:“自然选择,如我们将在本书中所见,是一种永无止境、随时起用的力量,无限优于人类的微薄努力,正如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于人类的艺术创作。”这本书出版于1859年。当时成立的论断今日还站得住脚么?甚至,即便是在达尔文在世的时代,这说法就一定成立么?生物进化固然不可取代,事实上也确实比人类利用动植物杂交所催生的进化更为巧妙,但它与我们用自己的大脑设计出的适应方案相比还是那么重要么?借用古人类学家米尔福德·沃尔波夫的说法:如果你能骑马,你自己跑得快不快还重要吗?
在我们如今的世界,繁殖成功——以及由此发生的进化改变——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以及它的“武器化表亲”,科技。这是因为,进化的速度和丰富性实在赶不上现代生活。无论自然进化在近代以前有过多大的成就,想想我们对电脑屏幕、全天无规律作息、高盐薯片和去除病原体的环境适应得有多差就明白了。我们体内的生物钟干嘛那么严格呢?看似一无用处、远古可能曾帮助我们消化草类的阑尾,怎么不能改为分解糖类呢?如果人类遗传机制是一家技术公司的话,蒸汽机出现之后就该破产了。它的“商业计划”是让新特征随机出现,然后通过有性繁殖推广出去。

当今
科技 v.s. 自然选择
我们这些大脑袋人类做了许多事来抵消自然选择的力量。凭借我们的工具、药品和其他文化革新,我们已展开一场有着致命隐患的竞赛——而且可能会输给一种高度进化的超级病菌。考虑到如今的疾病借人类长途旅行之便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速度,“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疫病流行时代,必须采取行动来终止它。”非营利机构“生态健康联盟”的疾病生态学家凯文·奥利瓦尔说。栖息地毁坏、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转变,也正使得更多人接触到以往与人类宿主隔离的病原体。
当今以及不久的将来
自己动手搞进化
结合体外受精与另一技术流程,我们便能检测出人类胚胎中可导致严重疾病的基因突变。当前我们正在开发强大的“基因编辑”新工具,下一步也许就能实现人为导向的进化。迄今此类研究大多是以其他生物为对象——例如尝试修改一种蚊子的基因组,使其无法传播寨卡病毒或疟疾。我们可以利用同样的技术来“设计”人类婴儿——也许只是简单地选择合意的头发或眼睛颜色。但我们该不该这样做呢?“肯定是有黑暗面的,”生物伦理学家琳达·麦克唐纳·格伦说,“但我确实认为‘升级版人类的出现不可避免。我们从本性来说就是喜欢改造的动物。”

这在老鼠的世界里还运作得挺利索,因为它们隔三个礼拜就能新产一窝崽,可人类造人要慢得多,差不多每25~30年才产生一代新人。照这个速度,一个优势特征传遍族群人口说不定要花上几千年。考虑到遗传进化如此磨蹭的程序,被科技超前也就没什么出奇了。科技如今承担了进化机制的大部分工作,而且速度快得多;它提高我们的身体能力,加深我们的知识范围,并使我们得以向更有挑战性的新环境挺进。

掌握用火用火可以燒熟食物、改变饮食结构、抵御猛兽,增加了社交机会——并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对语言的打磨。

艺术起源艺术表达以及象征符号的运用为社会关系网的扩展打下基础,后来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文明。

安葬仪式伴随死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不断进化,标志着自我意识的出现以及生命可能拥有来世的观念。
“人们还在对达尔文和DNA眷恋不舍。”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联合任职的分子工程师乔治·丘奇说,“但今天大部分的选择过程发生在文化和语言、电脑和服装领域。想当年,在DNA主导进化的日子,你要是有个精彩的基因突变,可能过上10万年才能传给全人类。如今你要是推出一部新手机或者一种革新性的制造流程,可能一个星期就传开了。”
毫无疑问,现实局面没有这么简单。擅写高科技题材的作家威廉·吉布森指出:“所谓未来已经在这里了。它只是还没有均匀分布。”有些人活在丘奇版本的世界中,有喷气式航空旅行和跨社会婚姻,分子药物和基因疗法,再向前一步,我们原本的基因构成似乎就只是一份有待改正的草稿了。但在世界的最发达地区之外,DNA往往仍是命运的代名词。
而且也并非所有的“大势”都无法逆转。有些情况下,自然选择即便在这些发达地区也可能回到中央舞台。比如,一场类似1918年大流感的全球性疫病爆发。那些对病原体有抵抗力的人(因为其免疫系统强健或体内有保护性的细菌使病原体失活)就会拥有巨大的进化优势,他们的基因能传给后代,而其他人会死绝。
今天我们对许多传染性疾病都有药可治,但近期已有恶性细菌进化到不畏抗生素的地步。喷气式航空能在一两天内把传染源带到世界各地,气候变暖可能导致携带病菌的动物不会像以前一样死于低温,例如曾被寒冬杀死的包藏瘟疫祸种的跳蚤。
纽约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埃洛迪·盖丁和我探讨了艾滋病的例子。全世界死于这一绝症的人已累计达3500万人,大致与1918年大流感的受害者人数相当。研究发现,一小部分人——不超过1%——拥有的某个基因突变可以改变一种细胞蛋白质的行为,而制造艾滋病的HIV病毒必须挂在这种蛋白质上才能感染细胞,所以这些人几乎不可能染病。如果一个人住在纽约市格林威治村,有条件买到最好的抗病毒药,那么有没有这个基因突变也许不是攸关生死的因素。但如果在非洲农村地区遭遇HIV病毒,基因很可能就是唯一管用的救星。
人类处境中还有许多其他状况可以让基因回到中央舞台。亚利桑那大学天文学教授、太空旅行专家克里斯·英庇预言,在我们孙子辈的有生之年,人类可以在火星上建成永久居住地,住进100~150个人以组成具有遗传活力的社群。他认为距我们更近的目标是一支规模更小的定居先遣队:“伊隆·马斯克(SpaceX公司首脑)嗨大了的时候,可能会说10到15年实现。但还是30到40年听起来现实一点。”他又补充说,这种定居点一旦建成,“就会加速自然进化过程。那里将是人造程度很高、身体舒适度很低的环境,对旅行者或殖民者的生理塑造作用颇为强烈。”他认为由地球人转化的火星人最佳体型是瘦长型,因为这颗红色星球上的重力大约只有地球上的三分之一。代代繁衍下去,人的睫毛和体毛可能渐次消退,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直接接触到尘土。英庇又预言,假设火星人类不再与地球人通婚,几十代人之内体质就会发生重大生化改变,几百代后连形貌都将与我们迥异。

淀粉代谢日常饮食含有大量淀粉的人类,比如以稻米为主食的族群,已进化出特定的基因来帮助他们消化此类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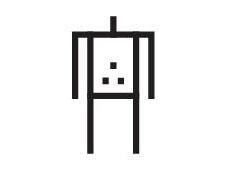
存留盐分某些热带人群拥有能防止身体在高温环境下损失太多汗水盐分的基因。

五短身材俾格米人的小体型可能源于低龄生育,而后者是为了应对热带疾病和人丁早夭。
有一项遗传比重很大的人类特征在持续增值,随着科技的主导地位上升反而有增无减——人类最普遍的野心始终是提高智慧。其他人类特征中没有哪个像智慧这般诱人追逐、用途巨大、用武之地丰富,在地球乃至我们能想象的其他世界都是如此。它对于我们在非洲的先辈来说不可或缺,对于我们在人马座比邻星外围行星殖民的后裔(如果有朝一日能到达那里的话)来说一样能派上用场。数十万年里,我们的基因通过进化,将越来越多的营养资源交给大脑使用,而事实上,我们永远不会嫌智慧太多。
与先辈不同,我们大概很快就不必再等待自然进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了。2013年,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尼克·博斯特罗姆、卡尔·舒尔曼着手调研强化智能的社会影响,论文发表在《全球政策》期刊中。他们集中审视了通过体外受精来进行的胚胎选择行为——由父母挑选合适的体外受精胚胎来植入受孕。据他们计算,从任意给定的10个备选中挑出“最聪明的胚胎”,如此生下的子女智商就比随机受孕约高出11.5分。如果女性愿意接受更高程度的激素治疗以加快排卵——论文轻描淡写地将这一做法描述为“昂贵而增加身体负担”——收效可能更为明显。
但真正的回报是体现在当事人后代的综合收益上:舒尔曼称,经过10代人的生育选择,后裔的智商就有望比初代产妇高出115分之多。如他所说,这样的收益估值是建立在极端乐观的假定之上,但进行这项遗传筛选的一般当事人至少能获得相当于今日之天才的高智后裔。论文又说,如果采用能在六个月内转化为精子或卵子胚胎干细胞,有望大大加快上述过程:谁愿意等上两个世纪来培育一支天才血统呢?舒尔曼还提到,论文遗漏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繁衍10代人的时间里,很可能已出现了连获得最高级强化的人类也完全不是对手的电脑智能程序。”
除了可能会输给人工智能,这套做法还面临一个更为直接的不利因素:我们对于智力的遗传学基础还不够了解,筛选高智力胚胎便无从谈起。说不定这个胚胎不会解高级微积分,而另一个连整数运算都过不了关。该项研究的作者们承认有这个问题,但声称可能再过5~10年就有能力从“认知轻度强化”的导向筛选人类胚胎。

不久的將来
科幻故事变成现实
五十多年前,两位科学家自造了“赛博格”一词,用来指代想象出来的生物——人与机器的混合体。当时看来是科幻,但时至今日,已有大约2万人身上带着能遥控开门的植入装置。尼尔·哈比森没有彩色视觉,只有通过植入头部的天线把视频信号转化成声音才能“听”到色彩;他相信未来人类会因为感官被此类科技拓展,而拥有广阔得多的天地。他说:“比如夜视能力,可以帮助我们适应环境——我们可以设计自身而不必设计这个星球。设计地球等于是害了它。”

节约基因有些发现于热带岛民体内的基因能帮助人在食物匮乏的条件下存活,但在食物热量高的环境下可导致肥胖。

毛发粗重东亚人在3.5万年前进化出了粗毛干,可能是性选择的结果或者调节体表热量的辅助机制。

消化海藻日本的饮食以海产居多,当地人群肠道内细菌的基因能帮助他们吸收海藻的营养。
猛一看这似乎可能性不高。智能的遗传学基础非常复杂。智能本身拥有多个组成部分,而且即便是单一的方面——计算能力、空间知觉、分析推理,更不必说同理心——也显然涉及多个基因,还全部会受到环境因素影响。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主持研究工作的副校长、中国华大基因公司认知基因组学实验室联合创始人斯蒂芬·徐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估计,可能对人的智力有影响的基因变异约有1万个。听起来挺吓人,但他认为处理这许多基因变异的技术能力已快到位——“今后十年内吧。”他写道。还有些研究者认为,并非需要了解全部有关基因才能开始筛选高智力胚胎。“问题不在于我们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丘奇说,“而在于我们需要知道多少才能有效行动。前人做出天花疫苗的时候又对天花病毒有多少了解呢?”
如果二人所言不虚,那么很快这条路上的唯一阻力就是我们自己了。也许我们并不想拿自己的天然基因组搞优生学。但我们会停下脚步么?如果会,能停多久?一项名为CRISPR-Cas9的新技术已经出现,丘奇的实验室参与了开发。它将考验人类好奇心的界限。这项技术于2013年初试锋芒,它能迅速而精确地切掉DNA序列中的一段,并用另一段取而代之。原本需要研究者花费几年的操作,现在只要一小部分时间就能完成。(本刊2016年8月号曾以《DNA革命》一文介绍该技术。)
以前出现过的其他人类基因组操纵技术与CRISPR相比望尘莫及。比如体外受精,是从随机生成的胚胎中挑选合意的那个,但如果给定的一组胚胎全都不具备超常智力优势怎么办?繁殖是个高风险过程。有个故事(真实性存疑)能阐明这种风险: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向剧作家萧伯纳提议,他们一起生个孩子,使之兼具她的美貌和他的智力,据说萧伯纳反驳道:“万一搭配成你的脑筋和我这张丑脸怎么办?”CRISPR能去除这种风险。如果说体外受精是从一份给定的菜单上点菜,CRISPR就是自己动手烹饪。事实上,有了这项技术,研究人员可以直接向精子或卵子中插入新的遗传特征,因此不止可以造出一个兼具才华和美貌的孩子,還能无止尽地制造这样的个体,形成鼎盛的大族。
迄今许多用到CRISPR的实验都是在动物身上做的。丘奇的实验室用它改造猪的胚胎,提高其器官用于人体移植的安全性。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凯文·埃斯韦尔特正致力于修改小鼠基因组,使之不再做莱姆病致病菌的宿主。另一研究者,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安东尼·詹姆斯,通过在按蚊体内插入基因防止其携带疟疾寄生虫。
但大致与此同时,中国科研人员做出了惊人之举——宣布他们利用CRISPR在无活性的人类胚胎中尝试修复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症(一种具有潜在致死性的血液病)的基因缺陷。这次尝试虽失败了,却使他们距离修复这一缺陷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于在人类基因中加入可遗传改动的疗法持暂未解禁,等待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充分证实,CRISPR也不例外。

脂肪代谢因纽特人的一个基因变异使他们能够消化油脂丰富的地区性食材,例如鲸肉和海豹肉。

耐受毒性有些阿根廷族群已发展出了对所在地区地下水中常有的高浓度砷的耐受能力。

驯化行为驯化家畜和驯化作物的做法很可能是挂钩扩散的,导致了永久性聚居地的出现,后来发展出城市和文明。
这个禁区会维持下去吗?我访问过的科学家无一这样认为。有的人提到体外受精技术发展的先例:它最初是作为一种帮助不育夫妇的医疗手段来宣传的,但其清除恶性遗传病的潜力很快显露出来。携带亨廷顿病、Tay-Sachs病等致病突变的家庭利用这种技术,可以选取无病胚胎来让产妇孕育。这样不仅让孩子将来免受许多痛苦,他(她)的潜在后代也同样受益于此。即便这有在产房内扮演上帝之嫌,对许多人来说仍显得合情合理。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生物伦理学家琳达·麦克唐纳·格伦指出:“如果禁止或避用这种技术,背后的法理是:自然进化机制一直是良性的、以某种方式起着正面作用。老天,真的不是这样!想想我们因为进化过程中出的错而吃了多少苦头,简直心惊胆战。”
随着人们对体外受精技术日渐熟知,它的主流用途也从防止遗传病扩展到了性别选择——多数应用于重视生子传宗的亚洲地区,但欧美的人也在用,以达到理想的家庭性别平衡。在官方说法中,该技术的非医疗用途倾向到此为止,但我们这个物种从来不懂适时收手。“有不止一个体外受精专家告诉我,他们可以筛选其他合意的生理特征,比如瞳孔和头发的颜色。”格伦跟我说,“对外不会宣扬,只在口头上告诉你这个选项。”换句话说,只要你喜欢,可能已有条件要求选取金发碧眼的胚胎受孕。
CRISPR又比体外受精技术强大得多,被滥用的风险也大得多,比如会带来通过修改基因制造某种完美种族的诱惑。该技术的发现者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分子生物学教授珍妮弗·杜德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讲述她做过的一个梦:人身猪脸的希特勒来找她学习这项技术。最近她在给我的电邮中说,她仍希望禁令持续,这会“让我们的社会有时间进行研究、了解,探讨在改变我们自身基因组时有意无意造成的各种后果”。
另一方面,对人类使用的潜在利益是不可否认的。格伦希望人们至少先对这种技术今后的应用方式做到深思熟虑。“什么会成为我们改进自身的新常规手段?谁来设定标准,‘改进又意味着什么呢?你可以把人改进得更聪明,但更聪明等同于更好、更幸福吗?CRISPR我们要不要改进道德呢?谁知道该怎么做?”

遥远的未来
人类能适应红色星球吗?
脱离人类常规形态的大规模进化分歧需要把一个人群隔离数千年才会发生——在地球上不大可能。但我们有望在今后半个世纪内到火星上建立小型定居点。然后再送去一个较大的社群——100到150人,并含有育龄成员以维持、扩增人口。我们能进化成理想的火星人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天文学教授、太空旅行专家克里斯·英庇预见到了火星殖民地,科学家们的作为可以令天然进化过程加速。对应于重力不及地球40%的大气,人的体型会变得高而瘦;人工控制的环境里没有尘土,所以会渐渐脱去毛发。

城区免疫随着人类结成更加紧密的社区而定居,他们强化了对传染病的天然抵抗力。

耐受乳糖早期驯化动物的人群,如欧洲、中东、非洲的牧民,进化出了脱离婴儿期之后也能消化奶类的能力。

文字读写最初只是作为贸易、记账的符号系统,后来随着城市和文化的扩张,发展到能够完全表达复杂的语言。
其他许多科学家不认为大家应该等到这些问题有答案;CRISPR一旦被证明安全,伦理问题就会退居二线,就和体外受精技术的情况一样。丘奇认为这类讨论仍然只算枝节:基因改造的闸门已然敞开,CRISPR只不过是大河里的一滴水罢了。他指出,时下已有2300项基因疗法试验在运作。去年,BioViva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宣称,自己已通过注射该公司开发的基因治疗药物,成功逆转了身体的部分老化现象。丘奇说:“显而易见,逆转老化与我们谈论的其他技术同样具有改进身体的潜力。”几种针对老年痴呆的基因疗法试验也在推进,它们不太可能遭遇多少阻力,因为其目的在于治疗一种损害巨大的疾病,但正如丘奇所言,“任何能防止老年痴呆的药物很可能也有增进认知能力的效果,并且几乎毫无疑问能对成年人生效。”2016年2月,英国主管生育事务的独立法规部门向一支研究团队颁发许可,准其使用CRISPR技术和人类胚胎(实验中用到的所有胚胎最后都会销毁,不涉及孕产)研究流产机制,此事使得抵制基因改造的防线又多松动了一点。丘奇对于下一阶段的发展已迫不及待。“DNA以前面对文化的进化速度望尘莫及,现在它又赶上来了。”
我们的身体、大脑乃至身边的机器,有朝一日也许会像库日韦尔预言的那样融合,成为一体化的大型共用智能装置。但自然进化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最鲜明的主题:通向同一目标的可以是许多条路径。我们本来就是一個不停折腾、瓦解自身局限的物种。进化之路的本身也会进化,分成多条平行路线。无论CRISPR在今后十年内能发展出怎样神奇的能力,都会有许多人等不及,现在就有迫切的欲求或需要。他们选择追随尼尔·哈比森的榜样——不是出发征服科技前沿,而是把前沿科技纳入自己的身体。
医疗领域永远是这类应用的先锋,因为科技在这里的用途是疗救危困,可以令复杂的道德问题简化。全世界有10万名帕金森患者接受了植入装置——所谓的“大脑起搏器”——来控制病情。此外还有针对某些类盲症的人工视网膜、为聋人设计的耳蜗植入体也较常见。美国国防部通过军方科研分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为这一前沿注入了大量资金。依靠这份助力,南加州大学神经工程中心的一座实验室正在测试脑植入芯片对恢复记忆的效果,这项技术也许有一天能用于治疗老年痴呆和中风、脑损伤患者。去年,匹兹堡大学一名实验者成功地用计算机转换大脑发出的电脉冲,控制一条机械臂的动作,甚至还能接收到其指端的触感。DARPA从未丢掉把人脑和机器连接、造就无敌战士的想法。“那里的每件事物都具有双重目的。”在《五角大楼的大脑》一书中记录此类研究的安妮·雅各布森说,“你应该记住DARPA的职责不是帮助患者,而是打造庞大的未来武器系统。”

皮肤色泽浅色皮肤(高海拔地区)增加对紫外线的吸收,促进维生素D产生;深色皮肤(低海拔地区)提供对紫外线的防护。

血液突变不同族群展示出多样化的血液突变;在热带气候中,镰刀型血细胞能对疟疾产生抵抗力。

魁梧西人北欧人的大块头可能是另一个性选择特征,被异性的青睐代代强化。
改进人体不见得要赋予人超能力才算。有数百人体内植入了电波频率识别装置,能用它隔空打开自家的门锁或登录电脑。一家名为“危险事物”的公司声称已卖出1.05万个波频识别芯片,以及用来将它们植入皮下的DIY工具箱。购买这类装置的人自称为“身体黑客”。
英国雷丁大学的工程学名誉教授凯文·沃里克是世上第一个接受波频识别装置植入的人(1998年)。他对我说,这是他在一栋以电脑控制门锁、自动感应温度和光线的大楼里上班时,自然做出的决定:他想和容纳他的这栋建筑一样智能。“做一个人类感觉也还行,”沃里克2002年接受一家英国报纸采访时说,“有些方面我甚至还挺喜欢。但成为一个赛博格的乐趣要大得多。”另一个同道中人在一只耳朵里植入了耳机。他还想在耻骨下植入一个振动器,并通过网络与拥有类似植入装置的人互联。
要讽刺这些事是很容易的。他们让我想起早期尝试飞行的那些人:胳膊套上板子、黏上羽毛就在那里拍拍打打。但我在请求哈比森展示天线入口的时候意识到此事并不那么简单。我不确定这个要求是否失礼。在科幻小说《仿真机器人会不会梦见电子羊》(后来被拍成电影《银翼杀手》)中,向一个机器人打听它的运转模式被视为无礼之举,“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礼貌的事了”。但哈比森热切地向我展示了他的天线如何运作,这让我想起人们在炫示自己的新手机和健身追踪装置时的那份快乐。我开始怀疑哈比森与我——乃至与我们任何人——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
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2015年报告称,当代18岁以上成年人平均每天约有10个小时盯着屏幕。(相比之下,每天的平均锻炼时间只有17分钟。)我至今仍记得童年好友家里的座机号码,却现在好友的电话却一个也记不得。(英国专门做过一项调查,发现10个人里有7个是这样。)美国人有十分之七在服用处方药,其中40~59岁的女性有四分之一服用抗抑郁药——尽管研究表明有些人随便做做心理治疗或者去小树林走走都能起到和吃药一样的效果。虚拟现实头盔在游戏产品市场上炙手可热。汽车是我们的脚,计算器是我们的脑,谷歌是我们的记忆。我们现在的生活只有一部分是生物性的,血肉与科技、碳(有机)与硅(电子)之间并无清晰的分野。我们也许还不知道会去往何处,但我们肯定已离开了原来的位置。

